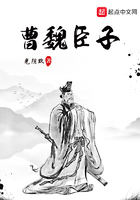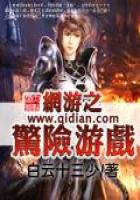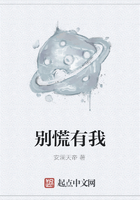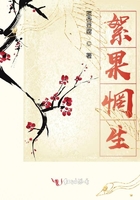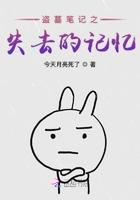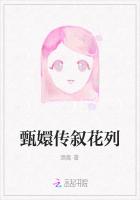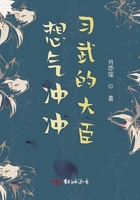那个被一群商贾簇拥,正笑得老脸开花的,正是李重进的使者孙成。
赵文扬让赵德昭等人继续在粮店等他,他则快步走了上去。
“哎呦,这不是孙老先生吗,想不到在这遇到了。”
赵文扬人还未到,已经扯开嗓子吆喝开了。
孙成抬头见是他,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沃日,这厮怎么在此?
赵文扬故意抬头看了眼“满园春色”的招牌,不怀好意地笑道:“孙先生原来也好这口啊,那日在风月楼何故离开呀?”
老东西,还跟我装?
孙成被他当场揭穿,登时老脸通红,心中暗骂:我跟你犯克咋地?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你小子就跟我过不去,我跟你没仇啊。
他支支吾吾道:“老夫,老夫……偶遇几个老友,人家邀请我一块,我也是盛情难却……”
赵文扬故作惊讶道:“你的意思是,你们几个,一块……咳咳,那啥?”
孙成气得瞪他一眼道:“话可不能乱说,你可别瞎想。”
他赶紧转移话题,问道:“赵少爷,怎会在此啊?”
赵文扬道:“我来这的目的,不是跟孙先生一样嘛。”
又将话题扯了回来。
孙成发现这厮就是块滚刀肉,揣着明白装糊涂。
一旁的几个商贾纷纷问道:“孙先生,这位公子是?”
孙成无奈只得介绍道:“这位是扬州大户赵家的少爷,也是……咳咳,李节度使未来的女婿。”
赵文扬忙摆手道:“我可没答应啊。”
孙成老脸拉了下啦,怎么感觉好像是节度使府在上杆子求着你啊?你特么什么东西!
于是冷冷说道:“前两日老夫去赵府,你不在,我与你父亲已经将亲事定下来了,自古婚姻大事都是父母做主。”
赵文扬突然明白老爹为何会来盐城了,我靠,老爹这个巨坑!
后院失火啊!
那几个商贾登时大惊,忙不迭地一一见礼。
赵文扬全程高冷,任凭他们卑躬屈膝。
“几位都是来这买粮食的?”赵文扬突然问了一句。
既然这些人跟孙成待在一起,那幕后买家就很明确了,就是李重进无疑。
那几个粮商登时警觉,齐齐看向孙成。
孙成暗骂:买粮的事本来是安排你做的,若不是你烂泥扶不上墙,用得着我亲自出马吗?老夫来此,可是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的。
“你也知道淮南地区遭了水灾,淮南西路受灾尤其严重,当地的粮食不够了,节度使大人为了赈灾,特意派遣他们外出购粮。”
几个商贾纷纷点头,不住地称赞李重进爱惜百姓。
赵文扬冷笑,我信你才怪。
淮南东路的灾情比西路的还重,你跑到这里来买粮食?
李重进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切断扬州城周围的粮食供应,为他兵围扬州做准备!
看来李重进起兵在即了。
孙成见他不说话,又道:“说起来赵少爷也算半个李家人了,你又对这里比较熟悉,也应该帮着节度使大人分担一些啊,买粮的事,不如就交由你来负责吧。”
赵文扬两手一摊,很干脆地拒绝道:“没钱!”
孙成冷笑,看来非逼我揭穿你啊。
“前两日我去赵府,赵老爷子可说了,十一万两银子都被你带走了,你没钱?”
赵文扬一阵后怕,得亏把银子都带上了啊,否则肯定被老爹都借出去了。
“银子都花了。”
“全花了?”
“全花了。”
孙成不信地看着他,十一万两银子,才几日的功夫就花完了,你蒙谁呢?
赵文扬一脸无辜道:“都用于赈灾了,我在小盐湖附近施粥呢,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八方流民齐聚小盐湖的事,孙成是知道的,想不到那幕后大傻笔竟是赵文扬,这厮无愧败家子之称啊!
赵文扬又道:“要我帮忙买粮也可以,要先预付三成的银子。”
孙成气恼道:“堂堂节度使大人,又是你未来岳父,会差你那点银子吗?”
“那可说不准。”
孙成瞪着他,心道:之前低估了淮南东路的粮食储备,虽然这几日不停地四处收购,但还是未能买空这里的粮食,而大人又起兵在即,且应了他,等粮食到了手再说,到时你还想要剩下那七成银子?做梦去吧!
“好好,我给你银子,但是你必须要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粮食采购完,然后安排运往淮南西路。”
“我尽量吧。”
目送孙成等人离开,赵文扬回到粮铺,将赵德昭拉到一旁,屏退了左右,郑重其事道:“大哥,我有一个重大消息要告诉你。”
赵德昭很少见他如此严肃,忙道:“兄弟,你说。”
“李重进,要谋反了。”
“什么?!”
“你小点声。”赵文扬忙警惕地四下看了看。
赵德昭瞪着牛眼,使劲咽了口唾沫道:“兄弟,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啊。”
“我靠,我哪敢开玩笑啊,大哥你要赶紧通知朝廷,早作防范。”
这等消息无益于晴天霹雳,赵德昭一时半会很难接受。
“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哎呀,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要是信得过兄弟,就赶紧吧,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赵德昭咬了牙,一跺脚道:“好!”
东京汴梁城,皇城文德殿。
赵匡胤坐在龙椅之上,看着手中的折子,眉头紧皱。
朝廷分派了皇长子赵德昭、晋王赵光义,赴淮南东西二路赈灾,这几日关于两地赈灾的消息不断传回。
淮南西路的赈灾工作已经陆续展开,而且已经颇见成效,节度使李重进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晋王赵光义大加赞赏。
奏折中说,晋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亲自去周边的路、州借钱借粮,帮助淮南西路赈灾,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淮南西路的灾情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
群臣对晋王的赈灾的功绩称赞有加,于是纷纷又开始询问淮南东路的情况。
毕竟晋王和皇长子是一同去的,从一开始,所有人都会不自觉地把两人进行比较。
一些与赵匡胤亲近的大臣,从皇帝阴沉的脸上,已经猜到了淮南东路的情况。
现在赵匡胤手中拿着的,就是淮南东路节度使刘守忠的奏折。
奏折中说灾情愈发严重,请求朝廷调拨粮食和银子……也捎带提了一句皇长子,说是将五万流民都聚集到了一个什么工业园,据说要晒制湖盐……
我的傻儿子,湖盐那是有毒的啊!
赵匡胤心中那叫一个气啊,临走时的殷殷嘱咐,算是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