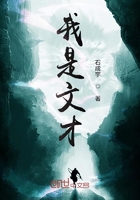覃夕月,是经济管理学院的高材生,院系系花。
姜蕊,高考第一志愿填的是南开大学历史专业,不料提档了,又不愿调剂,不得已转投别校的汉语言文学。
李子瑜,则是规矩的广播电视学的学生。
三个专业迥异,性格亦趋截然不同的女生,囿于大学报道当天迟到,鬼使神差地分配至一间宿舍,成了交情过硬的朋友。
覃夕月与姜蕊,分别拥有各自典型而极端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前者是崇尚金钱与权势的现实主义者,而后者,则是时刻幻想月下柳梢人的浪漫主义者,彳亍于两人之间的,就是李子瑜,既不悲也不喜,尽管大伙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间断中存在着意见与分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一起逛街,一起扫货,一起吃饭,和一起逗趣。
姜蕊是个好姑娘,骨子里秉性深埋的纯真,天可怜见。
她自己都照顾不住,一个不留神,还会让一个佯装凄凉的人讨走几十元不等的钱财,也许情况远比她们想的糟糕,别人认为她是遭骗了,但欺诈对她而言,无异于宇宙万物回归奇点,于是,一个扎着马尾辫,长相伶俐乖巧的女子,就这么执拗地杵在街头,劳碌地等那所谓‘一定会回来把钱还上’的承诺久久成空后,她这才扁着嘴,双目噙泪,手攥空拳,言之凿凿地指天发誓:再要上当我姜蕊便叫猪啃喽!
可宁愿信姜蕊是失心疯掉,她俩若较了这份真,把这看作是一份郑重的誓言,姜蕊怕是须为公猪下一辈子的崽,再踏出圈外一步,那是不大可能了。
李子瑜的意思是指,蕊儿还是那个不谙世事、无法承受别人乞怜目光的小女孩。
覃夕月是个十分自命清高的女人,傲气得让人几近窒息,虽说如此,她的麻辣嘴舌,也向来都会让人难免介怀,一件即将清季的名牌大衣,能够被她数落得毫无是处,服务生在她的唾沫碎星下,自惭形秽得简直不是个东西了,李子瑜感觉她的红脸是在攒着劲,亦然,站在一旁局促的子瑜与蕊儿也是。
她曾问过自己,子榆,你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感恩的,冷漠的,活泼的,文静的,或许都不是,在平平碌碌的大学时光里,某一天如同童话般,碰怀邂逅了陈潇,蕊儿以她的纯真与夕月作了个赌,并且赢了,可在最后一次分手,两人同样也是打了个赌,夕月,赢得了李子瑜的结局。
以至于她时常会这般认为,自己那所谓的爱情,不过是在美轮美奂中开始,在悲催的残酷中,又匆匆地结束......
那天似乎是下起了朦朦细雨,天边的云如铅锤倒灌,结成一块块,李子瑜无法接受这般的压抑,付之一笑,陈潇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潇洒地背过他那浑厚高大的身影,推开玻璃门,不遗丝毫的恋想便离去了,她如鲠在喉,咽不下又呕不出,梗阻于心窝,是如此的沉甸,那一霎,清晰地听到了琉璃盏狠心被掷在地上的声音,那不像话的爱情溅得支离破碎,拢在一起的瓷片即便拼凑得歪歪扭扭,李子瑜看那裂缝,丑得就好像一张咧开嘴哭的笑脸。
她是喉颤眼涩,也许真的想哭了,但伏在蕊儿肩膀上良久,却只是微微睁着无神的双目,望着那曾最为熟悉的男人坐过的位置。
义愤填膺的夕月差点就要从座位里跳出来揪住离去的陈潇,却让出奇冷静的子瑜给按住了,这或许会被她编纂成日记里闲散的一段笑话,正因为那么的讽刺,那么的不可置信。
就连她自己,都该开始怨恨这份倔强了吧。
在平静无波的数日过后,夕月忽然在大街上停住了脚步,转头面向子瑜,并伸出了两只手,一边紧握成拳,一边平摊舒展,严肃地丢出一道选择题,左手,是追回他、抓住他,追得你心乏疲累,追得你遍体鳞伤,追得你即使二十岁的脸容,也将憔悴得四十余几,右手,则是放开他、放生自己,让那个负心汉像崩个响屁一样,滚离我们五百公里远,也让你自己回归自我,重获排出那道浊气后舒适的笑容。
这对于失恋者来说,大概会是个异常悲壮的抉择,可李子瑜却首露了浅浅的笑容,轻轻地抓住了她的右手,三人相互望了两眼,均是扑哧一笑。
生活依然是这么过,工作仍旧如此繁琐。
覃夕月与姜蕊向来不吝于朝李子瑜抱怨工作压力如何的大,上司是如何的哓呶不休,李子瑜会有一些共鸣,但她并不是一个爱说唠叨话的人。
公司本就是社会的缩影。
谁都要习惯,里面所有的人,包括拖地的阿姨,包括送外卖的小伙子,交流中多少都会装有伪装的善意,这并没有多大的问题,也无法说明这种浅显到不能再普通的社会交际方法就是错的,即便是她自己,也乐不疲此。
这是一个一望无垠、使人迷茫踌躇的城市洋流,它卷起澎湃的波涛,海水冷得发怵,李子瑜攥紧了帆船的角隅,徘徊中彷徨。
‘媞莎’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跨多元产业集团公司,载誉四十余年,广州分部主营营销策划业务,业界内罕有的超新星,策划部划分A、B、C三组,李子瑜在B组,任策划助理,组内成员,舍去李子瑜,还有黄德权、徐涛,以及不久刚结束孕假的胡敏,主管王成宇是个胖子,讲他是个大男人,可浑身这细皮嫩肉的白皙,寸缕寻不见一根毛,光的折射一旦大于45°,轻易能晃瞎人眼。
黄德权与徐涛两个糙汉子不提,李子瑜好歹是有点姿色,反倒是胡敏,生产后妊娠纹褪不去,本就黑不溜秋,体毛又盛,经风一吹,一肘子的鬃毛摇曳,老远一瞅,好似捞月的长臂狒狒。
被男人比下去的女人,该有多臊。
胡敏一吼:自己唯一能与之媲美的,只有体重。
于是她常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诫李子瑜,女人呐,千万别惦记着早婚早育,二十至三十岁,是女人能否永葆青春尤为关键的一环,防晒,锁水,补充胶原蛋白,甭信男人‘怎样都爱你’那一套胡话,他体恤的只是你不该花的,真要是油尽灯枯,你瞧他嫌不嫌弃你,想一想,皮筋松了还能保持紧致吗,大约是不行的。
胡敏讲得这样露骨,像极了覃夕月的口吻。
不提‘矮’和‘胖’的关联词汇,王成宇可以文质彬彬与你温婉地聊上一晌午的生活前景,若是揭了他的短,出门不挨他一顿吵是万不可能,脏字不带叠的。
一次即将上马的电商项目,所有细则均谈拢了,只剩签约,王成宇把人送到门口,惯例握手致意,那爱尔兰人是个不拐弯的直肠子,伸出胳膊勾过王成宇,飞快地在他那大肚腩上拍了两巴掌,说:Hey,bro,you're so fat!
不是顾忌旁人和那一纸千万的合约,王成宇便要口灿莲花,祝他一路平安了。
策划总监是Ella,扮相淑女,行径却十分鲁莽,嗜好甜食,啤酒节营销的那一次,她以为避开了人群,囫囵咽下一块碗口粗的蛋糕,吮手指的间歇,转身与李子瑜四目相对。
那一刻,李子瑜真想剜去双目,拄一拐杖,告诉她:我什么也没看见。
李子瑜上周被委任为南沙一个小项目的负责人,全无拒绝的机会,这是大公司一贯的狼性做派,既以最低的工钱差人把事给办了,又美其名曰锻炼基层员工,作技术储备,给你画一张大饼。
总经理位极人臣,英文名叫Neal,中文直译为尼尔,她们管他叫阿T,尼尔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高学历海归华侨,光是他那枚不胜举的高级头衔,以及那剑眉星眸的年少皮囊,就足以让办公室内那群趋之若鹜的性感女郎,好似劈头盖脸浇了一身黑驴血的母鸡们,纷纷微睁迷离的眼睫,侧肩撩起她们长翅下的绒毛。
李子瑜想,真该学一学人家,至少捶胸顿足,也得为因自己没加入到爱慕他的行列而感到惋惜、懊恼。
尼尔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他常会给组内下达一大摞的工作,放荡不羁的黄德权偶尔会趴在李子瑜的文案上,笑嘻嘻地调侃我这般那般的,末了,询问是否愿意应他的约,出去吃顿饭,她自是委婉拒绝,但多数不用她出口,尼尔会像个幽灵一般飘到他身后——真不是假,也许‘飘’字还不足以形容尼尔的鬼魅,他冷冰冰地扫了小黄一眼,只说一句‘看样子,年终奖是可以省下一笔了’,后者便会落荒而逃。
李子瑜也会幻想,并且是那样地喜欢白日做梦,王子与童话,是一样不差,差的只是这谢幕的舞台,王子蔑视地扫过一眼,儒雅地抬起他那尊贵的骑士之手,给他那兼差影印的腌臜女仆,扔下一沓文件与一句‘尽快完成’的话语,便扬长而去了。
这适逢也是她的性子,言简意赅,李子榆和尼尔,再简单不过是两块笨重地传递机械工序而铰轧出刺耳金属音的齿轮,两人的交流,三句以上都势必恬燥。
尽管他袒胸露乳,如同神情肃穆的阿佛洛狄忒矗立在维多利亚广场上,那般的毋容亵渎,也就那精致的五官,揩净了,依稀还能裱画出人类的轮廓,否则,真就算泯灭了。
他仍然会使李子瑜产生好奇感。
但凡有人细细斟酌过他那丹凤眼的双目,未必不会有同样臊热的诱魅感,细而狭长的睫毛簇拥住那眸子,扑朔的光亮忽然水漾银光,仿佛明灭可扑了,迷迭在惊鸿一瞥的悸动里,捣出水花,晕成片片涟漪,既像波澜江海里剔透的墨绿珍珠,又如泥泞小道上幽暗的萤火虫光,使人禁不住恍惚,无以复加。
李子瑜几番斗胆想上前去掐灭它。
这双锃亮眼睛的主人,他如不是会施法的恶魔,那就应该是一只生性顽劣、自负傲慢的小精灵。
不知何时起,李子瑜就爱缩紧脖子,藏匿在桌子那料峭的文件堆后,偷眼打量着这位总是从她面前匆匆而过的绅士男子。
李子瑜嗅到过他身上的味道,一股浅淡的葵花籽的味,那是她所喜爱的,如同当阳里绿柳窜挠过脸颊上那丝丝缕缕的酥麻,清沁肺腑,在她租住的那不过十平米的拮据单间内,硬生生地让她挪出了一点空隙,用以接纳一位刚从邻居家中扫荡出门的可怜家伙,一颗连根险些都无法扎下的向日葵。
几乎是第一眼,她便从它那枯朽的黄叶里倒映出了自己的影子,异乎寻常的吻合。
李子瑜为它添置了新盆,浇了水,培了土,它面朝朝阳,佝偻的背破出了绿芽,颤巍巍的,好似涅槃后有厘不清的慨想,她倚住窗边枕着手臂,会神神叨叨地跟它讲个不停,或天南地北,或情难杂事。
原本茕茕孑立,现在它俨然成了李子瑜少有可倾述的舍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