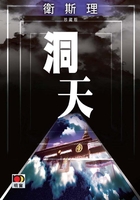先前京城没有张贴天师禁蝎符咒的习俗,只是随着青词宰相赵丹坪在京城的得势,以及民间的传颂,尤其是在天子的表率以后,满城都有了朱砂书符禁蝎的习俗,寻常人家就去道观花上几十文钱买符,破财讨心安。富贵门第自然有门路去让道教真人亲笔画符,而高门大宅,都是京城大观里心眼伶俐的老神仙派遣道童主动将一叠叠朱红符咒送上门,这与清明谷雨之间的热络赠茶并无两样。此时,离五更破晓还有小一段光景,一名身穿大红蟒衣的男子走在深宫大内,手持几张与寻常禁蝎符截然不同的黄底朱丹符箓,另外一只手下垂在袖,提了一把普通的油纸伞。
缓缓穿廊过道,往皇宫玄武北门走去,男子无眉没须,一头雪白头发,两缕如雪长发垂在鲜红蟒袍前,持符探袖的那只手,粗看只是修剪干净,如女子般白皙修长,细看袖口竟然有无线红丝如纤细小蛇扭躯飘摇。虽然才是谷雨,约莫是近湖的缘故,骤雨过后,附近蛙声一片。北门玄武有一座更鼓房以及计时的一间刻漏房,各挑选有勤恳太监当值,这名虽白发如霜,面容却保养得体瞧着才中年模样的蟒衣太监脚步竟然无声无息,如同一只行走在夜幕中的捕鼠红猫。宫内有资格身穿红蟒衣的宦官屈指可数,就官衔而言,以正四品司礼掌印太监和从四品司礼秉笔太监几位大宦官为首,太安城皇宫号称浩浩荡荡十万宦官,虽是夸大其词的虚数,却也侧面说明这个坐拥天下的赵姓家族宦官之多。这位近看装束就已经足够被称作貂寺的宦官来到玄武门,贴上了画有雄鸡啄蝎的朱丹符箓。他不识字,自然认不得那些精妙符咒到底写了什么,年幼入宫前是没钱进入教塾或者私学,入宫以后,跟了主子,忙碌得顾不上学文识字,再后来,主子成了九五至尊,大概是为了避嫌,他也就没了去读几本书的心思。
站在门下,看着那张由龙虎山赵丹坪提笔亲写的符咒,这位大宦官嘴唇微动,说了无人可闻的三个字,“鬼画符。”
他抬头看了眼天色,还要下一场暴雨,可惜了那些新透红的桃花新抽绿的嫩芽,不由轻叹一口气,默默提伞返身走回。四更将至,临近刻漏房,一名值殿监老宦官匆匆拿着青底金字的时辰牌往更鼓房跑去,一路上大小太监们见着了,不管身份,都要侧身站立,以示尊崇,便是未曾掩门的房内太监见着了,也应该起身。太监这个世人眼中云遮雾罩的行当,实在是有太多的规矩和讲究,曾经有一名圣恩正隆的大太监撞到了值殿监宦官,误了敲更,那名大太监曾经的班头已经成为御马监的掌印,私下父子相称,当值宦官被反咬一口,被活活打死,之后被韩貂寺获知,不仅这名正值炙手可热的太监,连同御马监掌印太监一并被私刑剥皮,而这等连朝廷大臣都悚然的大事,对家事国事习惯事必躬亲的皇帝陛下,也只是一笑置之,对于御史言官雪片一般的弹劾,以“寡人家事”四字驳回。此时,前往更鼓房递送时辰牌的老宦官原本沉浸在所到之处所有太监的恭敬礼让之中,见着了拐角转来的那一袭大红蟒衣那一头白发,瞬间头发炸开,不敢停留,只是弯腰低头,大步变小步,但加快步伐,使得速度不增反减。白发红蟒太监微微侧肩,两名身份天壤之别的宦官就此擦肩而过,老宦官始终连大气都不敢喘。乖乖,他如何不怕,当年那位遗落民间的新皇子入宫,身后这位,可是一气杀了四百多名胆敢私下议论皇子身份的太监,其中就有本是心腹的二十四衙门之一兵仗局的首领太监。
这位手腕血腥的红蟒太监,自然就是十万宦官之首,与人屠徐骁和黄三甲并称王朝三害之一的人猫韩貂寺。
五更鼓响,也就是破晓了。
刻漏房九刻水滴出第一声,就有腿脚灵活的小太监赶往宫门禀告拂晓已至。千万盏大红灯笼几乎是在同一瞬间高高挂起,照耀得一座皇宫灯火通明,充满生气。韩貂寺轻轻走在其中,等到九刻水第二声来临,他刚好一步不差来到皇帝御前,进屋以后,始终低头,只能看到一双出自尚衣监的黄紫相间的靴子,除去寓意勋贵的颜色,也就与寻常家庭的棉鞋无异。房内有奉御净人侍奉那名男子穿上正黄龙袍,男子听着窗外雨声,笑声温和,“谷雨降雨,万物清净明洁,是个好兆头。”
弯腰的韩貂寺,两缕下垂头发几乎触及沁着凉意的青石板地面,轻声道:“启禀陛下,六皇子昨天托人送了些雨前香椿入宫。”
男子没有作声,房内气氛凝滞,只听得窗外雨声隆隆,许久,他才笑道:“虽说雨前香椿嫩如丝,不过他显然是送你这个大师父的,与朕无关,你就不要画蛇添足了。”
韩貂寺弯腰更低。
男子脱下一只黄紫棉鞋,砸在这名大太监身上,大笑一声,略显无奈道:“拿三斤过来便是。”
红蟒衣韩貂寺点了点头,白雪发梢随之在地板上弯曲,他捡起棉鞋,小跑几步,交给御前净人手中,然后后撤几步,站在原地,用太监特有的轻柔腔调,只不过比起一些太监的阴柔瘆人,多了几分醇正,小声说道:“陛下恕罪,六皇子只送了两斤香椿。”
才拿过棉鞋准备自行穿上的男人又丢了过来,笑骂道:“那就两斤都拿来,你这当大师父的,没这口福了。”
掌宝玺大太监和几名俱是红蟒巨宦都已经在门外安静候着,站在廊道中线,风吹雨斜,大雨拍栏杆,溅入走廊,鞋面很快就浸透。这些大太监都是宦官极致的四品从四品,等着跟随皇帝陛下向南而行,其间要先走过一条象征大内界线的龙道,再绕过两座宫殿,才算到民间所谓的金銮殿参加今日的早朝。
临朝之前,就会有几位新提拔而起的起居郎在中途汇入这支队伍,都是一些年轻的新面孔,却连大太监们都要笑脸相向,与以往一等达官显贵在宫内遇上他们主动下马下轿截然相反。
本朝早朝遵循旧例,皇帝亲临,除去天灾,严寒酷暑一日不间断。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品秩不高的京官而言,还算不上如何劳累,只需要参加五日一次的大朝以及朔望朝;那些个住在临近皇城几条权贵扎堆的大街上的官员,大概是四更起床;其余官员每逢大朝,若是买不起越是离皇城近越是寸土寸金的豪宅大院,恐怕就要三更半夜就要动身,穿过小半座京城才能不耽误朝会。今日大雨,文武百官出门就都带了雨衣,此时披雨衣等候大门开启,因为是大朝,不光是公侯驸马和近千京官,许多世袭勋官散官也都按例前来早朝,足有一千四五百人,密密麻麻地站在皇城大门以外的雨中,黄豆大小的雨点敲打在伞面上,砰然作响。
这是一幅太平盛世独有的候朝待漏画面。
这个前无古人的庞大帝国,无数政令就交由他们下达到版图每一个角落。
钟响以后,这些大权在握的朝参官京朝官就要弃伞前行。过城门以后,不得喧哗不许吐唾,近侍御前有病咳嗽者即许退朝,前者往往也因人而异,低品小官一经发现,自然会被监察侍卫和宦官驱逐出去,以往许多祖辈建功的勋官子弟也都对此不搭理,踏阶入殿以前的一路前行,都会与世交官员窃窃私语,说些不甚恭敬的言语,直到张首辅掌权以后,这种陋习才得以涤荡,每次朝会因此越发肃穆庄严。大黄门晋兰亭撑伞而立,依然孤单伶仃,对此人相当不喜的大部分京官们都私下取笑“并非鹤立鸡群,而是鸡立鹤群”,尤其是这位鲤鱼跳龙门的小士族黄门郎一次早朝,竟然拉肚子,差点憋死,所幸黄门郎不像四品以下官员只在殿外跪地无法入殿面圣,被皇帝陛下看出异样,特准他退班离去,才算没有闹出天大笑话,于是这个好不容易靠卖熟宣与几位大人物拉上关系的黄门郎,彻底成了京城显贵们茶前饭后的取笑谈资,尤其是桓温遥领国子监左祭酒去广陵道担任经略使后,一偌大座京城,四品以上官员中唯一一位愿意让晋黄门入府门的庙堂重臣也没了,谁让这小子好死不死偏偏与北凉走得近?
以递补大黄门身份踌躇满志步入京城的晋兰亭,早已没了起初的书生意气,磨光了棱角,对于铺天盖地的冷嘲热讽也不再在意上心,他清楚地记得当自己被桓祭酒邀请上门的第二天朝会,那些嫉妒羡慕的眼神。晋兰亭伸出一只手到伞外,雨点敲打掌心,一阵生疼。一直以油纸伞遮掩面容的他微微撑起伞面,看着那些每一个熟人扎堆便意味一座小山头的百态官员,听着他们的谈笑风生,这位被京官集体排斥在外的熟宣郎轻轻踮了踮脚跟,因为他的身份清贵,大朝要严格按品秩依次鱼贯入门,得以靠近皇城正门,于是晋兰亭看到了几个显眼伞面,其中一柄是身材高大故而超出常人伞面好几寸的首辅张巨鹿,伞下除了这位“三百年独出砥柱”的大人物,还有可以不上朝却执意上朝的门下省左仆射孙希济,大概是首辅大人担心孙老仆射的身体,就帮着撑伞挡雨,这是一份莫大的殊荣,比较皇帝陛下准许老仆射临朝坐椅,丝毫不差。
晋兰亭缩回冰凉的手,低敛眼皮子,握紧拳头。
他悄悄望向不远处同是北凉出身的一名大臣,贵为皇亲国戚的礼部侍郎严杰溪。本是北凉陵州州牧的后者恰好也向他望来,双方视线一触即弹开。
晋兰亭不露痕迹地收回视线,重重深呼吸一口,眼神坚毅。他要做一名诤臣。
而今日即将被他弹劾的误国奸臣,正是提携他入京为官的北凉王徐骁!
他知道早朝以后,不管大雨是否停歇,自己都会震动朝野,清誉满天下。
而此时,徐凤年转入了橘子州。
徐凤年想通了一个道理,所谓的拔剑四顾心茫然,除了忧国忧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迷路了。因为修改了既定路线,只能循着大致方向如无头苍蝇一般乱窜,所幸路途上遇上了一队正被马贼剪径的读书人,算是没拔刀就给相助了一次,然后一同折向龙腰州和橘子州边境。之所以出手,是看出了这些人的春秋遗民身份,而且马贼也不陌生,其中两名就是上次要抢人回去给女当家压寨暖床的家伙。这群年龄参差不齐的书生士子应该家境不俗,不知是家族聘请护院教头还是临时雇佣了五六名精壮武人,对上三十几名来去如风的马贼也称不上毫无还手之力,几名佩剑士子也表现得颇为出彩,剑术花哨归花哨,吓唬马贼倒也绰绰有余,几名装扮男装的年轻女子看得两眼放光,反倒是出力最多一锤定音的徐凤年,让她们兴致缺缺。
这大概是他戴了一张平庸相貌生根面皮的缘故,世间情爱大多文绉绉讲求一见钟情的感觉,可说到底,才子佳人小说里的主角,男子怎能不玉树临风或者满身书卷气浓得呛鼻才好?女子怎能不必须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徐凤年对此倒谈不上有什么失落,反倒是跟队伍里的几名老儒生谈得来,才知道一行人都是姑塞州几个同气连枝世交家族的子弟,圣人教诲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队伍里有几人同时及冠,恰巧一名老学究和橘子州大族有联姻,也想着遍览边塞风光,就一起出行,年轻人趁着风华正茂去游学,年迈的趁着一只脚还在棺材外就赶紧游历,至于三名女子,都是爱慕及冠士子,虽然也是北逃的遗民后代,但感染北莽风气后,就壮起胆子来了一出私奔好戏。徐凤年略作琢磨,也知道她们所在家族多半比起几位青年俊彦要稍逊半筹,希望能够借机在游历途中生米煮成熟饭,攀上高枝,这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徐凤年在与老儒生天南地北地闲谈套话中,也得到了佐证,北莽分四等人,春秋遗民都在第二等,后来北莽女帝净九流清朝轨,排姓定品,除了朝野上下心知肚明在为慕容氏铺路以外,也并非一无是处,南朝除了高踞甲字的“高华”三姓,接下来一线所谓的高门大族大多是丙丁二字居多,和徐凤年关系亲近的老儒生,便因为族兄曾经担任南朝吏部正员郎,得以跻身丁字家族,而队伍里为首的世家子,虽然士子北逃时只是中原三流士族,但扎根北莽,约莫是水土适宜,家族先后有两人位列南朝九卿高位,一跃成为丙字大姓,三名家族不在丙丁之列的女子,有两位思慕对象都是一个姓骆的潇洒公子哥。
路途上她们得悉姓徐名奇的年轻人只是姑塞州流外姓氏的庶出子弟,连给个笑脸的表面功夫都不乐意做了,好似生怕与这人说一句话,就要被骆公子当成水性杨花的轻佻肤浅女子。
离橘子州边境城池还有一天脚力,暮色中一行二十来人开始扎营休憩,徐凤年手脚利索地帮着几名老儒生搭建羊皮帐篷,在有心人势利眼看来就越发没有结交的兴趣,只有那几名差点丧命在马贼手上的扈从,偶尔和这名武力不错据说是半士半商子孙搭腔几句。北莽中南部偏北容易水草肥美,靠近离阳王朝的锦西州还有连绵山脉,不过他们不敢跨境幅度太大,遇上了北朝的权贵,不管是草原上的悉惕,还是军伍的将校,别说碰一鼻子灰,能否活着回姑塞州都要两说。粗略安营扎寨,就开始燃起篝火烤肉,顺便温酒煮茶,昨日一名箭术精湛的扈从射杀了一头落单离群的野马和几只天鹅,还未吃完,徐凤年沾了几位老儒生的光,才尝到几口烤得半生不熟的马肉。坐在篝火前,年轻士子们高谈阔论,好像一个吐气就是经国济民一个吸气就是山河锦绣,老书生们则缅怀一些年轻时候在中原的光景岁月,不知为何话题就集中到了两朝军力,再推衍到弓弩臂力。丁字家族的罗姓老者见徐凤年好像听得入神,就笑着解释道:“这弓弩强度,即所谓的弓力,就是用悬垂重物的法子,将一张弓倒挂,拉满为止,重物几斤,这张弓便有几斤,也有相对少见的杆秤挂钩,后者精准一些,一般用在军营里,老夫那名拉弓射落天鹅的扈从,就有接近两石的臂力,百步穿杨不敢说,八十步左右,透皮甲一二还是可以的。弓弩用的是冬天津液下流的上好柘木,水牛角和麋鹿筋也都是制弓美材,可惜鱼胶和缠丝差了些,否则他背的那张弓少说能卖出三百两银子。”
徐凤年笑道:“罗先生,如此说来,那张上好弓弩起码能挽出三百斤弓力吧?”
罗姓老儒生抚须笑道:“不错,不过三百斤弓力,怎么说都要战阵上的骁勇健将才拉得出来。他若是拉得开,就不会给老夫当扈从了。徐奇,你可猜得到此人年轻时候是一名北凉军中的擘张弩手?”
徐凤年瞥了一眼那名沉默寡言的擦弓汉子,摇头道:“还真猜不出。”
兴许是隔壁篝火堆的俊男美人听到了“北凉军”三字,顿时谈兴大涨,就将北凉军里的武将排坐了一番,有说陈芝豹枪术天下无敌,也有说袁左宗是真正的战力第一,更有说那人屠怎么都该有一品境界,否则十岁从军如何活着拿到北凉王的藩王蟒袍,大家对此争论不休,大部分俊彦公子都比较偏向徐骁城府深沉,一直在战场上隐藏实力,不可能是二三品武夫境界,二品小宗师境界,的确很出彩了,可搁在一名几乎要功高震主的大将军身上就难免有些拿不出手。老儒生见徐凤年默不作声,笑问道:“徐奇,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