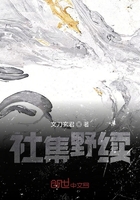1959年9月16日下午即将收工时,喜讯从天而降,而率先为众战犯送来喜讯的,居然是独自被派回场部去挑开水的徐远举!田野上陡然响起了他那早为大家所熟悉的湖北口音:“好消息!好消息!”
大家抬头寻声望去,只见徐远举手舞一张报纸,满面赤红,气喘吁吁地连跑带叫。
众人赶紧围了上去。徐远举双手展开当天的《人民日报》,用湖北话在人丛中大声念了起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犯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所有的战犯都犹如骤然间遭到了雷击,人人目光呆滞,喜泪纵横,那一句宣布实行特赦,在心中立即卷起了滔天巨浪,一股暖流霎时涌遍全身,脑袋里嗡嗡作响,思维也好像凝固了。
有人在拼命欢呼,有人在号啕痛哭,有人彼此拥抱,有人在田野上狂奔大叫……
当人们从极度的惊喜中清醒过来,回到宿舍,再将报纸认真地细读了一遍。虽然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大提出的建议中并未说将所有的战犯全都特赦,但毕竟,所有的战犯都从中看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希望,因为党中央的建议中明明白白地写到:“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这一天恰好是中秋节的前一夜,月亮已经圆了,月华像明亮的天灯照亮了农场;离散多年的家庭要圆了,每一个战犯的心中一片光明。范汉杰、郑庭笈几名战犯受不了这骤然而至的喜讯的冲击,兴奋过度,血压升高,被送进了医院。其他的战犯也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
两天后,即9月1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便登出了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和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特赦令的第一句便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十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这还能指谁?这不清清楚楚地就是指他们这帮人吗?他们喜极而泣、感激涕零,找不到一句能准确地表达他们此时心情的语言。
一切雷厉风行,就在特赦令颁布的第二天,功德林的孙处长陪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和不少记者来了,理发师沈醉忙得不亦乐乎,每个战犯都希望自己的形象能够光彩一点。
徐远举对沈醉的陈年积怨早已烟消云散,趁理发时悄悄对他说:“咱们如果能够一起出去就好了,我还有一大笔钱,可以分一半给你。”
原来,他在解放前寄存了几千美金在重庆银行的一个朋友那里,这个朋友很讲信用,解放后将这笔美金换成人民币,交到了徐远举手中。
沈醉感谢他的好意,但他表示,现在不考虑钱的问题,如果能出去,他马上要求到香港去与雪雪见面。
徐远举长叹了一声,悲苦地说道:“还是你聪明,把老婆孩子弄到了香港,我这次就算能出去,也依然是孤家寡人一个,耿静雯和孩子在台湾,我怎么过得去?”
沈醉:“我算什么聪明?真正聪明的,还是那些把家眷留在了大陆上的人。我们过去的确跟着蒋介石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就是受点苦,抵抵罪,我也是想得通的。可就是每次管理员叫领家信,看到他们那副高兴的劲儿的时候,我马上就会伤心起来。你姓徐的,我姓沈的,过去都是少年得志、心比天高的人物,如今连封家书也没有……”
徐远举眼也潮了,长叹一声:“现在才知道杜甫的诗写得好,家书抵万金呐!他这诗,不就是专门为我们写的么?……”
面对摄影师的镜头,管理人员叫大家不要激动,照往常一样,该干啥就干啥。摄影师拍了战犯们除草劳动、讨论学习等镜头。
具有职业敏感的徐远举最善于察言观色、小中见大,并据此作出判断。当他发现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的镜头,老对准少数几个人,似乎把他冷落在一旁时,他突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拍我?我流汗水,写材料,哪一件落在后头?到今天连配角也轮不上,连跑龙套的资格都没有,我是真心实意接受改造,改恶从善的呀!”
文强赶紧上前一把拉住徐远举,把他带到墙角去好言开导:“共产党明明公布的是特赦,而不是大赦,更何况在反右斗争结束后不久,政府采取谨慎的措施是可以想见的。对于我们这种生死场中过来的人来说,有一句俚俗之言叫做将军额上能行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凡事不要抱太大希望,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失望。”
徐远举红着眼,气呼呼地说:“你的分析是有道理,我有些不服气是真的。唉,谁叫我们过去呆在军统那黑窝子里,把自己的名声弄臭了呢?好吧,我听你的劝告,牢骚就暂时发到这里吧。”
每一个战犯都在猜测,从政治影响出发,特赦名单肯定会在建国十年大庆之前公布。获释的战犯肯定会在10月1日之前跨出牢门。
在兴奋而焦急的盼望中,国庆节来了,过去了,不少战犯的心里由晴转阴,对特赦的失望一天比一天加重。
就在这样的时候,孙处长又来到了秦城农场,在会上对大家讲:“你们都学了《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可是,你们的注意力都落到了关押已满十年这一点,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当获得特赦,而对改恶从善这一条认识得不深,这四个字包含的意义很深刻啊,过去做的恶是否交待彻底,成为战犯后是否真正从内心服罪认罪,这难道不也是你们应当重点考虑的吗?”
孙处长的这番讲话,让所有战犯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之中。过去做的恶是否交待彻底?这是能否获得特赦的关键,可是,交恶彻底的标准,在战犯们的心中,却显然是不太一致的……
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那是1959年的12月4日,功德林的大礼堂里呈现出一种极微妙的气氛,喜悦与激动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们并不是所有战犯脸上的主色调,因为,这种喜悦和激动里掺和上了担忧、焦虑、紧张、期盼、妒忌,甚而还有恐惧。
战犯们静静地走进了大礼堂,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大红绸缎做的横幅,“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几个白色的仿宋体大字整齐地剪贴在上面。
大会开始了,很快便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陈长捷……”随着法官那时起时落的声音,所有战犯的心都像闪电一样交替闪现着两种感情,一是喜,一是悲。
全场死寂,落针可闻。
当法官念到邱行湘、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卢俊泉等名字后,突然停了一下,紧跟着又说道:“以上人员,改造十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那一刻,除了已被念到名字的10人,其余的战犯仿佛头上遭到了重重的一击,立时觉得眼前发黑,美丽的海市蜃楼消失了,有人失声啜泣,有人丧魂落魄,有人几乎站立不住……特赦人员代表杜聿明向政府致谢词,郑庭笈的女儿和杨伯涛的儿子代表家属发言,他们根本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是,代表政府的姚局长的讲话让每一个刚刚陷入绝望的人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我们祝贺第一批获释人员,希望你们以人民为榜样,我们期待第二批特赦人员,希望你们以新生者为榜样。过去常对你们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现在应该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最后,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代表未获释人员们发了言。他说:“感谢党的宽大政策,10名同学特赦了,我们也感同身受。今后,我们一定要努力地改造自己,争取第二批得到特赦。”
这是所有未获释人员共同的心声。
首批特赦,全国共33名,功德林10名,军统人员无一人上榜。
组织上为作好续留战犯的思想工作,邀请了一批民主人士去探监,担任国务院参事的张志和也去了,他的安抚对象是王陵基和徐远举。
1948年,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王由南昌回成都赴任后,曾到陕西街72号告知张志和夫妇一项机密情况,王说他回川就职前,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他时曾向他亲授密令,要他一到成都即将张志和秘密处决。
张志和与李琏芳闻此言不禁惊出一身大汗,猜不透王陵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谁知王陵基却对张志和说:“志和兄,你想我两个这么多年的交情,我对你哥下得了这种毒手么?这种不够朋友的事,我姓王的是不会做的。”
他又对李琏芳拍着胸口说:“大嫂,你放心,我和志和是生死之交,情同手足。只要我在四川一天,天王老子也不敢动他一根汗毛的!”
三位昔日的老朋友相见于功德林狱中,忆及往事,自是感慨万分,也煞是亲热。
徐远举告诉张志和,那时张每次去重庆,他其实完全知道他是来此与共产党接洽,但是,出于私人情谊,他却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做法。
1960年,沈醉、董益三获得特赦。徐远举被安排代表未赦人员发言。
在大多数人眼中,徐远举这批落榜,显然下批肯定有份。然而,延至1964年底,已经特赦了5批。郭旭、康泽、沈醉等均已获赦,徐远举仍然榜上无名。
1964年,沈醉读了《红岩》小说后,特地去功德林探望张严佛、徐远举、周养浩等一批朋友。
见面后,大家都很高兴。沈醉向他们介绍了特赦出去后,受到了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的两次接见,以及担任政协文史专员后的种种情况。然后,沈醉取出《红岩》递到徐远举手中,希望他对照《红岩》小说,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徐远举表示:“一定好好反省,争取早日出去。”
这年10月,徐远举以《血手染红岩》为题,自破坏《挺进报》起,至“11·27”大屠杀止,系统地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在这份长达4万字材料的结语中,徐远举写道:
“我血手染红岩的罪行,是震骇中外、令人发指的。我以美帝国主义的金钱,以美帝国主义的刑具,以美帝国主义的武器和炸药,来屠杀人民,破坏城市,使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数以千计万计的遭到屠杀牺牲,这完全是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行为。在西南全境,可以说没有一块土地,不留下军统特务和我个人的血腥罪行……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宽大政策,将我这个危害人民、作恶多端、怙恶不悛的大刽子手,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机会,使我逐渐地恢复了人性,分清了是非善恶,认识到谁恩谁仇。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
言之切切,情之殷殷,谁会想到,这是发自于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的内心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