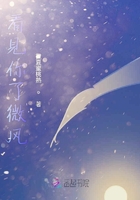新的生活开始了,一切都很陌生,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里是现成的监狱,有高墙、有铁窗,墙上还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勿怨勿悔”等等攻心标语,但是,这一切都是过去徐远举大权在握时他的部下们搞的,共产党只不过又拿来对付他们了。
不同的是,共产党的管教人员不仅不打骂犯人,也不要学员们向他们立正、敬礼,拉屎撒尿也不要他们在门边喊报告。有时他们蹲在院坝上抽烟或吃饭,见学员走过,他们还会喊着你蹲下闲拉一阵,问学员的经历,或是家庭情况,向学员介绍共产党的政策,谈思想改造。学习,没有设专门的教员,也不发课本,主要任务是各人写反省自传。此外就是选读报刊社论,学习时事,讨论座谈,讲认识体会。有时也听管教干部上大课,讲一些改造的道理。生活上,犯人们自己到厨房抬饭菜,回小组分吃,自己打扫室内外以及院坝、厕所里的卫生。每天晚饭后自由活动,有的打百分,或围在一块摆龙门阵,有时也到坝子上集合唱歌。尽管如此,犯人们大都还是怀着无可奈何的暗淡情绪,内心里暗自抱屈,埋怨共产党对垮台的国民党人处理太严。
王陵基就在晚上摆龙门阵时对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说:“过去改朝换代,垮台的官员可以当平民,作寓公。今天我们求作一个平民而不可得,连个搞勤务的副官也不能带在身边,整天就是关起来改造学习,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处置我们哩?”
每个星期六的上午,要例行召开一次生活检讨会,让每人自己检查近段时间说了哪些错话,做了哪些错事,包括自己头脑里有哪些错误思想、看法,自己批判认识,保证今后改正。如果自己不老实交待,别人则可以检举。检举者有功,隐瞒者加罪。在这样的会上,犯人们都说自己通过近期的学习,自己又懂得了什么道理,找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检讨,但心里真实的抗拒情绪却深藏不露。
犯人们私下称这样的检讨会叫做倒脏水。
在1951年2月23日的检讨会记录上,记载着徐远举的发言:“来到白公馆后一开始吃大桶饭菜,我很不习惯,既不好意思,又怕不卫生,通过学习,我才认识到这种思想还是过去当反动派头子时爱讲排场的习惯未改,我保证今后一定改正。”
1951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纪念日,狱方号召犯人写诗撰文,在墙报上出纪念专刊,善写旧诗的沈醉偏偏写了一首题为《我的忏悔》的新体散文诗,其中有这么几句:“我们,有的明明是贪得无厌、凶残狠毒的豺狼,却偏偏给自己披上民意代表的外衣,我们,有的在人前装着善良无害,尽说悦耳的好话,却天天在干吃人血肉,卖国求荣的勾当!看今天,太阳升起,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革命烈火,要烧尽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魉!”
徐远举仰着头边看,边用左手揉着下巴,脸上挂满了轻蔑的神色,突然他轻声而愤然地说道:“我看沈麻子现在还想吃人血肉,还在继续干卖国求荣的事情嘛。”
此话一出,犯人们大惊!
在检讨会上,有人将此事揭发了出来,徐远举马上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可是,他表面上认错,背地里却在犯人们面前做出一副党国忠臣的样子,连王陵基也不得不劝他人在矮檐下,不要自找苦头吃。
来到白公馆后最初一段时间里,犯人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写反省自传。对这批国民党的大人物来说,反省自己的历史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过去,人和人的道德准则是隐恶扬善、不揭人之所短,而今天则要完全反过来,要自己揭自己的短,自己不揭,别人知道的也可以揭。开始大家都非常反感,觉得共产党这种做法太没有人情味。
徐远举甚至说:“共产党是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来整我们。”
一次,预审员找徐远举核对审讯笔录,徐远举自作聪明,认定是公审处决的日子临头了,整日茶饭不进,等待公审处决。当天晚上,他两次从噩梦中惊醒,一次梦见自己五花大绑在群众大会上被宣布死刑,在被押出会场时,一大群共产党的犯人举起拳头直朝他头顶打来;一次梦见背插斩标,被押往五灵观阅兵场,解放军对准他的脑袋叭的就是一枪。惊醒后他一身冷汗,呆坐在铺上。
第二天,白公馆一切生活照旧。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十天过去,徐远举暗地里咒骂自己是个庸人。
谁也不会想到,34年后,沈醉居然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重返山城重庆。
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计划拍摄一部资料片,其中之一是沈醉的《旧地重游》,而重庆,自然成为这次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部资料片由曾执导过故事片《创业》等片的著名导演华克同志担任编导工作。
这年中秋前后,一个消息传遍了福州新闻界,两个宿仇深怨的新闻人物将在榕城见面,一位是曾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中,当时任中共贵州省顾部委员会委员的韩子栋,一位是曾经专门捕杀革命者的大特务、国统局戴老板跟前的大红人、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沈醉。可是事不凑巧,就在启程前几天,沈醉突患感冒,身体不适,未能如愿。沈写信对韩老说:“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一定要去贵州当面谢罪。”
沈醉此次风尘仆仆到达重庆,下榻烈士陵园附近的外语学院外国专家招待所。到达的第一天就拍加急电报给韩老,告诉他自己准备赴贵阳拜访,不料几天后韩老却从广州发来了回电:“我来重庆看你……”原来韩老正在广州,决定乘飞机到重庆与沈醉见面。
韩子栋就是小说《红岩》中的人物华子良。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九·一八”事变后,韩子栋进入中国大学经济系读书,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各种抗日活动,并在地下党领导的《春秋书店》工作。1933年,他加入了地下党组织,由于他在秘密活动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矿区有过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党组织要他打入到国民党蓝衣社(即复兴社,军统的前身)内部做情报工作,并建立发展情报网。韩子栋在极其复杂和十分艰难危险的环境里,出色地完成了地下党交给他的任务。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韩子栋不幸被捕。他面对特务的严刑拷打拒不承认对他的一切指控。经过几次与特务的交锋后,韩子栋知道特务机关并没有抓到他的任何现行证据,这更加坚定了他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心。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的14年牢狱生活中,韩子栋的罪名一直是军统严重违纪人员。
狱中的韩子栋,更加沉默寡言,老是在不停地做清洁和一个人来回地走动。这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了敌人对他的看管。在贵州息烽监狱,他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关押在一室,他利用自己相对自由的身份,秘密地担任起与狱外党组织联系的任务。在狱中他也多次为越狱的问题与罗世文发生争执。韩子栋坚持创造条件集体越狱,狱中支部则要求能够出去一个就是减少一分损失。虽然韩子栋希望有更多的同志与自己一起逃出去,转到重庆关押以后,韩子栋在狱中做杂务,比其他的政治犯有在监狱范围内活动的条件。由于白公馆的看守加强以及被关押人员变动性大等原因,集体越狱的机会几乎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韩子栋接受了狱中党支部的要求,抓住机会跑出去!
为了作好越狱的准备,他加大了每天的运动量,为了能够更好地麻痹特务,他显得愈发地疯疯癫癫,为了越狱的成功,他利用每天跟随看守外出买菜、挑货的机会仔细地观察路道和辨认方向。
机会终于来了!1947年8月18日上午,看守卢兆春带着韩子栋到磁器口去买菜,韩子栋照常担着挑子走出了白公馆看守所的大门。因卢兆春经常去采购,在磁器口街上有许多熟人,每次去了少不了要被邀去喝茶、打麻将。这一天,卢兆春很快地把菜、货买好后就去货主家喝茶,稍后,又围桌打起了麻将。与往常一样,韩子栋照样坐在门口石梯坎边等候。当卢兆春刚刚自摸了一把满贯,乐得鼻子眼睛全错了位的时候,韩子栋走到卢兆春身边说要去方便一下,卢兆春毫不经意地挥挥手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