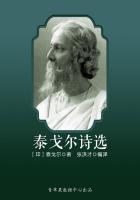“哦!二位就是C区过来支援的该隐先生和白奕先生吧!”艾维斯刚推开办公室的门,一个地中海男子便从一大堆档案里面探出了脑袋,对二人露出了一个和蔼的笑容,“快请坐快请坐,我已经等候多时了!”
该隐喃喃道:“这就是以后的尹泽吗……希望秃头不会传染,否则我现在就得和他保持距离了……”
白奕白了他一眼,和艾维斯一起坐在了地中海男子的对面。
“喂,我呢?”该隐指了指自己。
艾维斯耸肩,“由于这个案子,最近报案的人越来越多了,椅子不太够用,你就站着呗。”
“混蛋,治安署的椅子都不够,你们还是来接待客人的吗?信不信我撒手不干了?”
艾维斯干脆懒得理会这家伙。
白奕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这时候的他倒是表现得有几分人样,“别耍宝了,站着就站着吧,我还想早点结束公务回家养老啊!”
地中海男子清了清嗓子,说道:“先做个自我介绍,由于我和尹泽不一样,他曾经担任过治安官一职,所以有一个霜逝的称号,但我没有当过治安官,没有称号,你们可以直接叫我韦兹署长。
“关于这次的案子,我们初步怀疑是妖魔所为,毕竟人类中可以使用灵能的基本都担任了治安官,少数作为自由人干着一些非法的交易。
“这个案件最开始是由一名少女在街边巷内昏迷,然后被路人发现并报警获救。少女本身没有收到什么伤害,但各种生命体征变得极其虚弱,甚至有两三位年龄尚小的女孩子陷入了植物人状态。”
该隐提问道:“医院有给出什么解释吗?”
韦兹道:“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她们的灵魂有了一部分的缺损,应该是被犯人给劫走了。”
“劫走灵魂?”白奕似是有了些门道,“我见过这种犯案手段,大多数都是为了执行一些黑魔法的仪式,来召唤魔鬼为自己所用。”
一说到魔鬼,该隐的表情明显抽搐了一下。
“我们最开始也有这样的设想,但是我们已经调查过了D区的所有女巫和巫师,他们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该隐自是一下就判断出来了其中的异样之处,“首先,会使用仪式的绝对不止女巫和巫师,炼金术师也会干这种事情,我们血族这种事也没少干过。”
白奕接了下半句,很明显思维列车是跟上了该隐的节奏,“其次,全部都拥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这本来就是一件很违和的事情。你不可能知道某一天治安官会查到自己头上,对每天的细节不会有那么多的记忆,那么又怎么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据?”
韦兹问道:“哦?你们的意思是……怀疑这群家伙是早就串通好的?知道我们一定会怀疑到他们的头上?”
“哼,”艾维斯双手抱胸,“这种事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不可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去抓捕别人,我们只能把他们当做嫌疑人对待。可是那么多的巫师女巫,难不成全部都当做嫌疑人?”
“用私刑。”白奕冷不丁地冒了一句。
艾维斯和韦兹当即就惊了,后者拿出一张手帕擦了擦自己头上的汗,“那个……白奕先生,你能再说一遍吗?我好像因为某些不可预知的量子力学原因而听错了你的话……”
“动用私刑。”白奕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
“你来捣乱的吧!”艾维斯猛地站了起来,完全没注意到这个瞬间该隐顺带抽走了他的椅子拉到了自己的屁股下,“动用私刑?这样你还能叫做治安官吗?!我们是为了社会的治安做出贡献,我们就代表正义!为什么要和罪恶同流合污?!”
白奕抬眉,似乎对他的这种言论表示不屑,“那么你觉得……在那些被害人的眼中看来,连凶手都抓不到,无法给她们一个交代的你……代表着什么?”
艾维斯语塞,这个问题,他无法回答白奕。
每当他前往医院探望那些受害者时,她们总会迫切地询问自己是否已经抓到了凶手。
而自己,能够回答的永远只有:“快了。”
最开始,被害者们还可以相信这种显而易见的谎言,但到了最后,每次得到这种敷衍式的回答,即使她们不说,眉眼只见也流露出了失望的情感。
艾维斯不甘,他心中有着十足的自责和愧疚,可是他无法抓到凶手,永远只能给出敷衍的回答。
那些被害人的眼神,像针一样狠狠地刺着他的心脏。
即使作为丧尸,心脏不复跳动,身体的每一处都无法感受到痛苦,每一次受伤都能够回复,但……这种心伤,他无法痊愈。
该隐和白奕与他的第一个照面就看出来了艾维斯已经被困扰已久,而他们给出的办法,也是最为简单粗暴的计划。
现在韦兹也基本可以推断出为什么白奕这种业绩极佳的治安官会被总部点名批评,甚至被调剂到C区,这个人的做法……真的是不拘泥于形式啊……
“回答不了么?”白奕摸出了一根香烟,自顾自地点燃,丝毫不顾及艾维斯和韦兹的脸色,“那就我来告诉你吧,在她们看来,现在的你只是一个心理安慰,你的出现代表治安署还有人在关心她们的遭遇,至于能不能带来线索,这已经不是她们所期望得了,因为她们能够预料到结局。
“你所谓的正义,带有着非常强烈的主观色彩。现在在她们的眼中,你已经不代表正义,因为正义不仅迟到了,还迟迟未来。这就是你的正义?”
“那你呢?!”艾维斯上前一步,自己的鼻子基本上要和白奕的鼻子触碰在一起,“你的做法,就算的上是正义?”
白奕哈哈一笑,对艾维斯的说法相当鄙夷,“正义?正义是什么?那是你自己为自己定下的行事准则!你只是被人道主义所约束,可我没有,在我心中,‘行动’不会带有任何的褒贬含义,它只是手段,能否达成最后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你口中的正义,在我看来,根本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