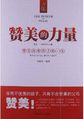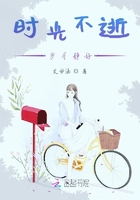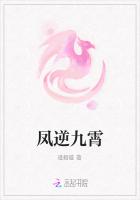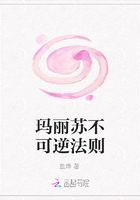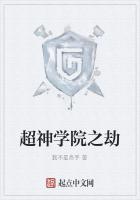与这些更热衷于寻求纸上谈兵快感的人相比,善于从本职工作中发掘快乐的人幸福感会更高,而且更容易留住手中的“饭碗”。比如我见过的一个快递员,在交给他一个快递时,他兴奋地说了一句:“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连着接了两个大单子。”那个快件跨了上海的三个区,算是单价比较高的一个吧,竟然让他这么快乐。他的表现让我想起一个报社副主编截然相反的态度。晚上在办公室签大样时,副主编对一个朋友说:“现在外面资金那么多,随便拉一个就好单干了,谁还在这里干这个?”当然了,那是好几年前经济形势大好满大街是钱来追人的光景。现在不同了,估计他在签大样的时候会有一些惶恐与珍惜相伴的情感,而不是往日的不屑。万一报社不再需要那么多副主编了呢?带着这份惶恐,他工作一定更积极,说不定还更快乐些。
想要的太多。
听一位刚结婚的上海男士说,如今身边好多适婚年龄的情侣之所以还未结婚,主要原因是婚房尚未解决。以目前北京、上海的房价,绝大多数30岁以下的情侣若想完全自食其力地付完首付,再支付每月按揭,就算勒紧裤带每天喝西北风过活,也不一定付得起。而看上去似乎大多数中国人又不愿意在租来的房子里成婚,于是就愁坏了一批人。对适婚女士来说,如果喜欢的人没有婚房,而有婚房的自己又不喜欢,那么是该嫁给喜欢的人还是喜欢的房子呢?
大概是被上两代人的贫穷经历吓怕了,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自己食宿无忧,具体物化为:小两口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除了每月付的按揭外,还能有供家庭吃喝玩乐的余款。这即使是在欧美发达国家,都算是高标准严要求了。而最让人担忧的是,“人格独立”这项应该算是基本的素质要求却被忽略了,父母为孩子准备婚房成了大势所趋。可见相比居者有其屋,一对年轻人的行为与意识独立不算什么,这应该是一种文明的耻辱吧。
在爱丁堡,我在一对年轻情侣的家里借宿过。男士是剑桥天文学硕士毕业,在一家公司当技术人员;女士还在读硕士,在一家甜品店打零工。他们用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租了一间一房一厅的房子,午餐常常吃女士从店里带回来的工作福利——免费甜点。虽然没什么存款,女孩一年还是能有一两次跟随男士出差的旅行。我对比着中国相似人群的经济状况算过一笔账,发现如果选择租房的话,中国大城市同样教育水平的情侣的生活水平一点儿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因为人工便宜,中国白领可以花很少的钱雇用钟点工。
买了房子的情侣也有问题。有对家底殷实的情侣在上海和南京分别买了房子,因为男方先是在上海工作,后又被派驻南京工作。而现在的矛盾是两人长期过着分居生活,女方说什么也不愿去南京生活,理由是不想辞去现在安逸稳定的工作,以致闹到分手边缘。比起这对小情侣,那些跟随着爱人经常跨国大搬家的人好像要求得少多了。
眼下的中国应该是矫枉必先过正的时期,从什么都没有,变成什么都想有,至少别人有的我都得有。由这种泛滥的欲望引发的烦恼实在很难让人同情,甚至令人生厌,就像讨厌那些纷纷登上富人榜还在说房价不高的房产开发商一样。
干一行,恨一行。
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闹离婚的时候,据说妮可的Fans实在气不过,只好这样排解:让他跟那狐狸精走吧,看他们能挺多久。
这大概是最有效的报复手段:你喜欢什么,就给你什么,然后悠悠地跷起二郎腿,欣赏一幕由仇人们主演的从悸动到习惯,由麻木到厌倦,由争吵而渐渐反目成仇,最后不得不离弃的悲情戏。
妮可与汤姆的最初,又何尝不是意乱情迷、天昏地暗?只是把激情当成事业经营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目的不同,收获不同,经营手法自然也不同。及彼不能顾此,只好一拍两散了。
出来做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喜欢了就想投入地去做,结果发现喜欢的部分不过是盲人摸到的象鼻子,剩下的庞大身躯面目可憎,却与那喜欢的部分浑然一体,躲都躲不过。
有个讨厌搞人际关系的人选读了理工科,在一家外资企业科研部门工作。本以为这里会太平点,没想到照样三六九等,等级森严,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于是恨恨地说:“当初不如去做公关,至少那里的人际关系是摆在桌面上搞的。”
有个酷爱艺术设计的人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家具设计师,可每每设计出的精品无人喝彩,而他眼中的俗物却在市场上大红大紫。一边顺应市场,出产俗物,赚得盆满钵满,一边痛斥这个行当无趣透顶。
于是化妆品公司的女孩会悄悄地说:其实我最讨厌化妆,而食品公司的人见到零食就反胃。
碰到一个音乐编辑和一个炒股票的。两人相互羡慕不已,都觉得对方的工作有趣。但音乐编辑说:这年头,音乐实在是没得做了。炒股票的说:这年头,股票实在是没得炒了。然后又说:不信,换换?
换了就好了吗?鬼才信。
突然失业。
我目睹过一个网络公司宣布裁员的场景。临收工前十分钟,老板宣布开全体会议,通报公司近况,然后让数十人留下来。五分钟后,这十几位同事木着脸从会议室出来,各自默默收拾办公桌上的物品,还有行政经理在一旁监督着,然后就永远地离开了公司。整个过程,从全体会议到被裁员者离开办公室,不超过二十分钟。偌大的办公室静悄悄的,连键盘声都很少,只听见收拾东西的琐碎声音,特别刺耳。
有个在国企工作的朋友,试用期将满时,在签正式合同时突然退却。只因那份合同上写明,如合约期未满提出辞职将赔偿薪金若干。朋友想了想,还是没有签,于是突然失业。比起上述失业者,他真的很幸运,至少还有机会选择。
相比起失业者,在业者过得也未必自在。一个在投资公司任副总裁的朋友已经三年没休过假了,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甚至董事会建议他休假时也被他婉言谢绝。他私下里对一帮朋友苦笑:“哪里是我高风亮节哦,只怕这一休,就连这个职位也一起被休掉了。”那时他们公司连他一共6位副总裁,缺了谁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
只要有一个被解雇的威胁悬在头上,坐在哪个位置上都是战战兢兢的。一个跨国公司的亚太区高级总监每次提到自己如何勤政爱民时总要缀上一句:“不然我怕被解雇。”虽然她的年龄和资历已经使得这个危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显然这个危机还是存在的。
不过在怪态百出的网络公司,又别有一番景致。由于公司强迫原来招进来做制作人或者编辑的员工去做销售或者赚钱的项目。许多人摆出一副“干不了”的架势,对老板怒目相向,潜台词就是:“有本事你炒我呀!”由于不愿支付遣散费,老板只好扮出一副可怜相挣得一点同情分,哪里敢提一个“炒”字?那时的员工别提有多神气了。
我们有机会做个愉快的打工仔吗?
对一些人来说,办公室意味着工资、事业、实现自我的价值;对另一些人来说,办公室意味着每天能和相熟的人一起吃午饭,有一张看上去还算体面的名片可以出去交换新鲜的面孔和话题,自己的座位上有一部公司的分机可以与外面的世界产生自然而然的联系。就像是加入到一个打工俱乐部一样,可以扩大社交圈,并且可以解闷。这样的人正是在“愉快打工”。
对“愉快打工”的人来说,工作成为一种需求,这好像和小时候学的共产主义劳动者对待工作的态度是相似的。
能有这样的觉悟,一是因为不缺钱,二是因为缺乏欲望,不想运用自己的金钱和人脉去改造世界或者维护世界和平。
有个女翻译因为厌倦了独自在家工作的日子,也想找一份能待在办公室里朝九晚五和同事相处的工作。薪金的多少、职位的高低她并不在意,唯一的条件是希望有三个月左右停薪留职的假期。她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家小规模的翻译公司。一共15个员工,却能搞定13个语种。公司考虑到资深女翻译质优价廉,破例应允了那三个月的条件,打的算盘是,在她不在的日子里,大不了找个大学生来实习呗。可怜这个有多本译作的人,在老板那里不过相当于英语系大四学生。但是女翻译工作得很愉快:一年当中九个月给老板打工,三个月给自己打工,如此交替,再也不会厌倦。
最近见到一个更神的人,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杂志社采用弹性坐班制度,每周只要去两三次即可,剩下的时间他用来打理自己的房产。由于热衷投资,他和自己开公司的太太在上海房产最低谷的时候买入五套房子,出租、出售、服务房客成了他的第二份工作。由于他开着丰田吉普,并持有文学杂志社编辑的身份,很容易赢得房客的信任与好感,就算房子的煤气灶、自来水管出了问题,而他未能及时赶到,房客也很少有怨言。毕竟,请得动一位文学编辑上门维修煤气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今和他同年进杂志社的同事已经成了他的领导,或者领导的领导,他依然和当初一样,做的还是最初的事——编辑。用他的话说:杂志社发的工资差不多刚刚够我养车的,就算当了最大的领导,又有什么意思呢?
活在当前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家再也不必在同一条路上挤死。你升你的职,我发我的小财,他睡他的懒觉。和谐社会,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