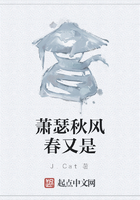夜,是深夜。
邓禹哲走在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他不知道该去哪儿,他无处可去。
谢老师技惊四座,在场之人无不倾心拜服。邓禹哲、武亦安、殷俊三人更是跪倒在地,央求道:“我们从此选择武科,请谢老师收我们为徒!”他们三人成绩一塌糊涂,文科考试本是伴人读书,今日见此神乎其技,更是大为心折,只觉凭武出头有望。
“我是教文科的,若要习武,还是另请高明。”谢老师转身便要离去,怎料陈若丹追了上来,哀求道:“老师,我想学武。还有,燕然他也想……”眼角偷偷瞟了一眼燕然。
“我方才已经说了,武学之道,在于扶危济困,与人为善。你们几人心中争斗之心太重,学不了我的功夫。况且,武科之路过于偏狭,录用之人极少,行业也日渐萧条,实非明择。你们还是安心读书吧。”
“谢老师,我闻圣人有云: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你本已是我们的老师,现在学生有心求学,您借故推脱,难道是有意藏私吗?学武功,和学作文有什么不一样吗?”张诗妍平日温婉文静,想不到此时出言,竟是如此犀利逼人。
谢老师回头看她,只见她眼波流转,余光也是暗指一旁伤痕累累的燕然,心中已是明白。叹了口气,又问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小杜:“你呢,也想学武吗?”
远处的居民楼里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不急也不亢,也算是一种助人安眠的白噪音。
但声音扎进邓禹哲的耳中时,却像尖针一般刺耳。他忍无可忍,随手抄起脚旁一只喝剩的酒瓶,朝着那一片居民楼扔去。
“我本自潇洒倜傥,为何如今犹如丧家之犬?”
“好吧。若要跟我学武,文学必先过关。你等平日个个自命不凡,语文课上哪个好好听过讲?今天我倒要考你们一考。如若答得上来,不妨传你们一点微末本领。”
邓禹哲等人心中大炽,直呼:“谢老师,您只管出题,我们一定全力作答!”
“你等平日有的恃武扬威,有的以文章夸示人前,今日便要你等七步成诗,若不能,则不必再说习武之事了!”
“七步成诗?好熟悉的剧情!”李败心想:“在场之人,只有我与张诗妍以文采闻名,谢老师这是有意偏袒于我!”
“谢老师,这……”邓禹哲面露难色,欲言又止。
“怎么,你不愿意?也不必勉强,还是好自读书吧。愿意者,在场人人可以参与,若有哪位可以七步成诗,我便传他一招半式。至于科考能否高中,全凭个人本事了。”
“请老师出题!”邓禹哲咬牙说道。
李败心想:“不知道武侠世界中,是否存在“陈王昔日宴平乐”的典故……我若是吟出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会不会被判作抄袭?”
正踌躇着,只听谢老师说道:“我们既然是师生,那便以“师生”为题吧。但是注意,诗中不得出现“师生”二字。七步之后,我即离去,如是一首不成,那也不必再多费口舌了。”
这些人平日读书一个个心不在焉,吊儿郎当,学武倒是心中赤忱。怎奈书到用时方恨少,莫言七步之间,就是给他们三天三夜,也恐难作出一首好诗来。
一声脆响,楼中顿时犬吠声大作,邓禹哲这才感到一丝快感。但这一丝丝破坏的快感,不时便随着时间一起消逝,黑夜又回到了一片沉寂之中。
“良辅自是有奇才,安得朽木与泥蒿。
苦心书牍不论功,悲欢人生各有时。
碧海丹心付流水,万语千言总关情。
惟曾指上茧成塔,不见浪子肯回头。”
邓禹哲刮肚搜肠,每走一步如履薄冰。短短的七步路,足足走了半个时辰,才终于憋出来这么一首大拍马屁却是穿凿附会、平仄不齐的七言律诗。
殷俊、武亦安更是急得满头大汗,支支吾吾,连首打油诗也吟不出来。张诗妍见陈若丹也是一脸难色,偷偷拉一下她的手,另一只手平平展开,在上面轻轻地吹了口气。陈若丹恍然大悟,立时吟道:“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惟见育材心,一世几人知?”
“好诗!好诗!”众人闻之啧啧称赞,谢老师也不由暗自点头,却将目光投向了燕然。
李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出言试探道:“这诗是依唐韵还是宋律?”
“唐韵?”张诗妍奇道:“宋朝是世间最为古老的朝代,在那之前人类还没有形成文明。虽然《尚书》、《山海经》等古籍中有过“有唐”、“大唐”之类的文字记载,但毕竟虚无缥缈,而且文字难辨,无人知是真有文明还是神话传说。”
“这我就放心了!”李败心想,虽然燕然颇有才名,但毕竟只是武侠世界中虚立的人设,写写散文、小说或许可以,吟诗作赋还是不能靠他的意识。如今此世不知有唐朝,就更没有成篇的唐诗留世,“我”此文一出,必定名盖当世,天下震动!
众人只见他片刻之间,走了不过三步,便一字一句慢慢吟道: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泪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诗刚念完,谢老师不知怎地,竟然暗自流下泪来,口中反复诉诵:“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泪光寒……”众人呆呆望着,也是默默无言。
开篇一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便把他全诗秒成灰烬。他恨,恨燕然文采绝世、武艺了得,他一生从未被如此全面碾压,如同脚下的渣屑。邓禹哲一边踽踽穿行于小巷中,一边寻找着可以破坏的物什。他看到了,街角处有一个破衣喽嗖的乞丐,正趴在地上写字。
夜这么深,路上早已没有行人了。一盏昏黄的路灯照得他的字迹更加殷红,好像是在写血书博人同情。他写了一会,又伸手去摸一摸腿,这时邓禹哲才发现,他双腿膝盖以下,竟是什么也没有!
邓禹哲不管这些,他走过去拿起那乞丐前面的瓷碗,朝那片居民楼扔去。犬吠声,汽车警报声一时交映响起。
“兄弟,你把我吃饭的东西摔坏了。”
“我便摔了,你又怎地?”
“嘻嘻!”那乞丐阴森森地一笑,突然站起身来,倏忽间一巴掌打到邓禹哲脸上。那一掌之快,实在不可思议。待邓禹哲反应过来,面前已是空空如也,那人像是凭空蒸发了一般!
邓禹哲哪还敢细想,拔腿转身边跑。康乐巷狭窄异常,他扶着墙壁跑出十来米,脸上突然又中一巴掌!那乞丐不知什么时候又闪现在他面前,右腿从膝上一瞬间长了出来。
邓禹哲吓得魂飞魄散,哪还分得清东南西北。他掉头就跑,可他无论往哪边跑,不出十来米,就被那乞丐堵住打上一巴掌。他飘然出现,单腿独立,时而是左腿,时而是右腿,却总能把邓禹哲拦下痛打,当真如鬼似魅一般。
邓禹哲脸上挨了十几个巴掌后,眼冒金星,再也走不动半步了。
他弯着腰,扶着膝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横竖是个死,老子和你拼了!”邓禹哲挺起身来正要拼命,那乞丐忽然之间又消失了。邓禹哲也不知道自己跑到了哪里。他抬头一看,只见面前一家酒吧,上面写着三个大字:“众仙会!”
邓禹哲生于石桥,长于石桥,也算是常年混迹娱乐场所,却从来不知镇上有家这样的酒吧。
“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先进去躲躲。”想着,邓禹哲走了进去。
他刚一进门,一支酒瓶便疾如闪电般地当面砸来。邓禹哲哪里躲避得及,当即头破血流。
“咄!现在这般身手的废物也能来参加众仙大会了吗?”那人轻蔑道。
邓禹哲手捂着头,鲜血却还是止不住地潸潸而下。他晃了晃脑袋,一个人模模糊糊,不停旋转着地正坐在吧台前,目如精光般看着自己。
即使他被头上流下的鲜血挡住了半边身子,邓禹哲还是认出了他!
魑魅山庄二公子孟毅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