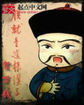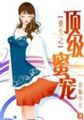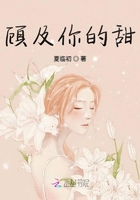七点还差二十分钟,李昊就安排李爽到玄都观去接孙思邈。
这是两天前李爽在终南山找到正在采药的孙思邈师徒时就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
李爽离开后不久,李昊和李世民也离开了餐厅,两人一起来到了书房。
李世民坐到沙发上,把坐姿调整到了最舒适的位置。
“五郞,八年前我就认识孙道长。”
“这个我知道,那时候二哥在晋南与刘武周手下骁将尉迟恭进行了一场决战,身负重伤,经过孙先生治疗后痊愈康复。”
“五郞,有时候跟你说话特没意思!你难道就不能假装不知道,让我表现一番?”
“干嘛要假装?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好吧,五郞说的有理。五郞为何想要道家一派加入长安医院?除了孙道长,二哥就没听说道家还有什么有名的医家。”
“二哥这话就不对了。被尊为‘医圣’的神农,与岐伯、雷公问对的黄帝,编纂《金匮药方》的葛洪,加上现在的孙先生不都是出自道家吗?”
“五郞说的这个我还真没有注意过。”
“道家盛产‘药神’不是偶然,而是道教文化思想潜移默化影响下的必然。”
“二兄愿闻其详。”
“首先,华夏上古时期没有医术,那时‘医师’也是‘巫医’。”
“在自然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巫医承担了救死扶伤的职责,在生活实践中也积累了大量的医疗经验。”
“在道教发展早期,巫医文化被纳入道教体系之中,因此,道教从诞生之初就把治病救人当作自己的本分,道教多出‘药神’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道教的一大核心思想和道士们的一大追求就是修道成仙。”
“要想长生,对于修道者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治病,只有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能够化解,才能活得更长久。”
“在追求长生,探索人体奥秘的修行过程中,道士们为医学积累提供了宝贵经验。”
“还有一点,道教祖师们在修道成仙的过程中,认识道想要长生成仙,单靠内修外养的道家方术是不够的,还需要积善立功,广修德行。”
“在这种思想的潜移默化之下,道教祖师们都心怀一颗‘道心’,行善事,立功德,凭借自己的医术,救死扶伤,切实的行道弘道。”
“二兄受教了。”
“不仅是医家,道教在化学、天文学、算学方面也有很深的底蕴,这些人才都能对大唐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两人正说到兴头上,传来了“呯呯呯”的敲门声。
李昊在说了一声“请进”之后,同李世民一同站了起来。
走进书房的孙思邈,在李爽的引领下,缓步来到李昊和李世民面前,抱拳齐眉,郞声说道:“草民孙思邈,拜见圣人。”
李世民上前一步扶住孙思邈的手臂:“孙道长,不必如此多礼,我们坐下说话。”
史籍中的孙思邈,此时应该是八十五了岁,而在李昊和李世民面前的孙思邈,乌发黑须,精神矍铄,一席麻衣道袍,虽然老旧,却干净整洁。
除了皮肤略显粗糙外,孙思邈看上去还不到五十岁的样子。
站在旁边的李昊向孙思邈行了一个抱拳礼,说道:“李昊拜见先生。”
孙思邈赶紧回了一礼:“贫道当不得殿下如此大礼,坊间关于殿下的种种传闻令贫道神往。今日得见,不胜荣幸。”
“先生请坐。”
三人坐下后,李爽端着茶盘,在三人面前摆上刚泡好的茶水。
“先生请用茶。”李昊指着孙思邈面前的茶杯示意道。
“贫道谢过殿下。”
“家人都叫我五郞,先生唤我五郞即可。”
孙思邈点了点头说道:“刚刚德棻小友还专门同贫道谈起五郞,特别是后世的医学科技,更是令贫道神往。贫道今日前来便有讨教之意,望五郞不吝赐教。”
孙思逊口中的德棻,即令狐德棻。
令狐德棻出身敦煌豪门,博涉文史,少有文名。
隋朝末年,授药城县令。
李渊入据长安后,先为丞相,奉代王杨侑为傀儡,德棻即任大丞相府记室。
李渊称帝后,令狐德棻即转为起居舍人,后迁秘书丞。
令狐德棻与孙思邈是同乡,交往甚为亲密,时常相聚谈古论今。
令狐德棻了解孙思邈的渊博学识,深知其思想早已超出医学范畴。在两人的谈论中,孙思邈把哲学思维和医学相结合,由哲理会通医理,阐发了“妙解阴阳”、“慎以畏为本”等一系列真知灼见,让令狐德棻非常折服。
孙思邈在同令狐德棻的交往中,也吸收了许多对自己有用的思想。
两个相差四十一岁的人,成了忘年之交。
“在先生等华夏医学前辈的成果基础上,经过一千六百年的发展,华夏医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五郞这次回到大唐,就是要把后世华夏医学的最新成果带到大唐,为大唐民众服务。”
“五郞有何差遣,贫道定当尽力。”孙思邈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我们在大唐设立长安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国立长安医院,招纳天下有志于医学的能人志士,一边学习,一边研究,一边治病救人。”
“五郞此举大善,现在的大唐,可以说是缺医少药,贫道虽然一生都致力于救死扶伤,但终究势单力薄,收效甚微。”
“先生在医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救死扶伤的善举,在华夏传颂一千六百年,是为我等后辈楷模。五郞想请先生主持长安医科大学和国立长安医院。”
“学习、研究、治病救人,贫道一定倾尽全力,但主持医科大学和医院,恐贫道力所不逮。”
“先生过谦了,纵观华夏数千年医学史,先生在医学一道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华夏医学的贡献,与黄帝、扁鹊、华佗、张仲景、沈括、李时珍等前辈并列。”
“五郞谬赞,贫道惶恐。”
“五郞先把长安医科大学和长安医院的规划告知先生,请先生先生教正。”
“五郞请讲。”孙思邈客气地说道。
“长安医科大学和长安医院完全按照后世的模式组建。”
“在后世,狭义的医学只是疾病的治疗和机体有效功能的恢复,广义的医学还包括华夏的养生学和由此衍生的西方营养学。”
“这与贫道的看法完全相同,疾病的预防、治疗,加上养生,才是医学的全部。”因为后世对医学的界定与自己的理念完全一致,孙思邈显得很激动。
“先生高见。”李昊对孙思邈的医学水平推崇备至。
“在后世,医学分为两大类: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
“现代医学也叫西医,通常是指华夏医学之外的医学体系。传统医学即指华夏的汉医医学体系,汉医也叫中医。”
“传统医学除了中医而外,还包括藏医、蒙医、维医、朝医、彝医、壮医、苗医、傣医等多种医学体系,也包括天竺的阿育吠陀医学。”
“五郞的意思是,我华夏民族的汉医,只是众多医学体系中的一种?”
“先生说的极是。”
“既然都是治病救人,难道不同的医学体系不能融合在一起?”孙思邈不愧是一代宗师,看问题的高度与常人完全不同。
“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如果只要一个结论,那就是不同的医学体系很难融合,只能是借鉴。”
“这是为何?五郞不是说了,医学是以治疗预防生理疾病和提高人体生理机体健康为目的吗?既然不同医学体系的目标一致,为何就无法融合呢?”孙思邈又提出一个极有深度的问题。
“不同医学体系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所使用的方法也完全不同。”
“我们以中医和西医为例来作简单的说明:西医理论的焦点内容就是找出致病源(病毒),然后研发能杀死这种病毒的药物杀死它,简单快捷而有效。”
“中医的理论焦点是阴阳均衡,失衡则病,治病则是调和阴阳,使人体阴阳均衡病即好。”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一间房子进了老鼠,用西医的方法就是放毒药毒死它;用中医的方法,可以封闭房子断水断粮饿死它。”
“两种方法均可以达到目标,但理论基础完全不同,很难融合。”
“贫道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华夏民族有了中医,还要学习西医呢?”
“五郞还是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中医西医有点像人的左右手,有的病以左手为主、右手为辅,有的病以右手为主、左手为辅。”
“没有中医能看病,没有西医也能看病。但是,如果一个人光有一只手,总不如两只手配合起来有效。”
“中医、西医各有侧重,各有所长,打法不一样,优势病种也不同。”
“二者的关系是互补,共存于人类战胜疾病的过程中。虽然不能融合,但可以相互借鉴。”
“五郞说的极是,贫道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