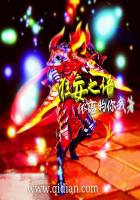梅朵上穿白色修身内衣,外面一条浅蓝色印白色小碎花的连体裤,穿着白色的平跟布鞋。她小腹微隆,在蛤蟆和阿珠的搀扶下,先来到了馥郁家。身后,跟着白子雄和伪娘,还有拎草药箱的两男人。
一进门,身穿浅米色休闲装的白子雄就说:“嗯,比前天好多了,那股子腐臭味淡了不少嘛!”
梅朵问馥郁:“你弟弟叫什么?”
“乃利,我弟弟叫乃利。”
梅朵跨进乃利的卧房就问:“乃利,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床榻上的乃利当即睁开眼睛,虚弱地回答:“不那么疼,好多了。”
梅朵让馥郁扶乃利侧靠在床板上,查看他背上的疮症。她说:“虽然还是很虚弱,但是病情已经有了控制。”
馥郁听了,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梅朵对馥郁说:“我说一遍,今天先让阿珠做给你看,明天你自己操作。”馥郁连连点头。“阿珠,你多拿些蒜瓣捣烂成膏做成饼,铺盖在多头的疮顶,单头的用蒜片,再用艾灸出毒浓拔白头。”
“哎!”阿珠有条不紊地按照梅朵说的在做,馥郁很仔细地在看。白子雄呵呵一乐,问梅朵:“没想到才两三天的时间,你就收徒啦?”梅朵只微笑,没理他。蛤蟆就说:“怎么切片,怎么用小药臼捣药成泥,还有怎么做艾灸、按压疮口出脓、清洗,我家总裁可都是事先手把手教的!对吧阿珠?”
“嗯!梅姐姐可细心了。她还说以后她出学费,供我去读护校呢!”
“阿珠你记住我对你说的,女人靠委身男人生活,是没有光明的,只会让自己遍体鳞伤。”梅朵当着白子雄和馥郁的面说:“女人要做到自力更生不依附男人,那才是最具魅力的!”
白子雄扯着嘴角淡笑不语,馥郁沉下了眼帘。阿珠一遍敷好,示范给馥郁看怎么做艾灸。梅朵说:“馥郁,敷蒜做艾灸是个慢活,你就这样给你弟弟做着,我们去看一下邱老伯再过来。”
“好的梅姐姐,那你们待会可一定过来啊?”
“放心吧,半途而废,不是我的性格!”
一行人来到阿珠家,邱老头的状况比前天好很多,他还主动伸出右手,向梅朵做了个请的手势。梅朵向他甜甜一笑:“邱老伯,你今天的心情不错哟,是不是因为知道阿珠要回来,所以特别开心啊?”梅朵让蛤蟆拿出准备好的一些营养品和消炎药放在了桌上,还放出了两沓钱:“老伯,今天敷过药后,我后天再来看你。西药要按时吃,每天多活动活动,开地种菜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另外……”梅朵拉近了一下椅子,把手握在他的手上说:“留给你的钱,慢慢花,可别再吸毒了。你自己克制戒了它,因为你是吸毒,才会长毒疮的。”邱老头一脸的疑惑,他开口轻问:“你……你是要买阿珠这女子吗?”老人摇了摇手说:“我……我不卖,不卖女儿!”
阿珠听了两眼含泪:“阿爸,梅姐姐不是要买我,她是想帮我!梅姐姐不是坏人,不是……”阿珠想说不是因为忌讳身后的白子雄,她才改了口:“梅姐姐要出钱供我去读护校,以后等毕业了,有了工作,就能养活你了!”
梅朵一阵感动,感动得有点鼻酸。一个染上毒瘾的父亲,居然还能很肯定地说,我不卖女儿!这样的人,这样的一对父女,确实该帮。“阿珠,你给你阿爸敷药做艾灸,别忘了清洗疮口,给他吃消炎药和神骏膏。我……我去外面走走。”梅朵说完,走到了外面。
蛤蟆追了出来,白子雄也跟了出来。梅朵顺手折了一根细树枝,转身就在白子雄的身上连抽了好几下:“白子雄,你就是个撒旦!你自己怎么不吸毒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住着诺大的庄园,左拥右抱的,每天晚上不做噩梦吗?”
白子雄任由她抽打,很平静地说:“缅甸,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你心里清楚。我不做,照样有人做。除了蛤蟆所知的那单货,我没沾过运毒的事。都是各国、各地纷涌而来,带货而去,通常都是货款两清,概不赊账。马克是个例外,因为他能帮我解决武器,我以货充款,给他便宜点儿,就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你还敢狡辩!还敢狡辩!你就继续作孽吧你!”梅朵用力地抽了十几下,最后扔掉树枝,气呼呼地坐在了一块长石头上。白子雄坐到梅朵边上,两眼含情地盯着她问:“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仅仅是因为同情那些瘾君子吗?还是因为你开始在意我了?”梅朵哼了一声,再白了他一眼:“你太自信!又太自恋!离我远点儿,让我休息会儿,吹吹风,晒晒太阳行吗?”白子雄嘴角一动,二话不说,直接把她的上半身一按,让她的头和后颈枕在了自己的腿上:“好好休息吧,这样才舒服!”
梅朵想挣扎着起来,白子雄瞪着眼睛说:“我保证不碰你还不行吗?这种美差,该不会也要让你的保镖来做吧?”
梅朵没再挣扎,她从裤兜里掏出块淡粉色的手绢,盖在自己的脸上,安心地小憩了起来。白子雄低头看着那块手绢,左边绣着大红、鹅黄、湖蓝三色三朵格桑花,两高一低,错落有致。右边用黑色丝线绣着“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的诗句。白子雄看得胸口砰砰直跳,这虽是茶花烟的广告语,但绝对是吊脚楼前初次相遇的情感写照嘛。她的恼怒生气,她的挥枝抽打,真的不光是同情那些瘾君子,真的包含了对他的在意和担心。没错,一定是的!
一觉醒来,日已西斜。梅朵皱着眉头问:“怎么不叫醒我啊?”蛤蟆不在,白子雄没有说话,伪娘一脸的心疼:“两个小时了哎,雄哥一动不动地就这么干坐着,也没个栏杆靠一下,好可怜哟!”
“啊?”梅朵一脸的玩弄:“你可怜吗?给你个机会自己换个词。”
“辛苦,是辛苦!”白子雄白了一眼伪娘:“没文化,就少开尊口。”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梅朵乐呵呵地笑着站起身来,走到篱笆边上,看了看含苞待放的两株小野菊,情不自禁地说:“小憩方醒日西斜,不见差人立庐前。篱下雏菊三两朵……”忽然,她慌喊一声:“天哪!我的手绢呢?我的手绢呢?”白子雄装出一脸的茫然:“不知道啊?我刚才也眯了会儿,估计……是被风给吹走了吧?”其实,白子雄故意支开蛤蟆,为的就是窃取梅朵的那块手绢。因为,这方手绢对他来说,价值万金。
“郁闷,郁闷死我了,那可是我一针一线亲手绣的呀!快帮我找找,快呀!”
寻找的结果可想而知,梅朵噘嘴轻骂:“气死我了!”
阿珠给她阿爸收拾好之后,走了出来,蛤蟆正好从山下跑上来。梅朵问他去哪儿了,蛤蟆回答:“雄哥让我去车里拿……拿纯净水了。”梅朵眼珠子一转,走到白子雄身边,问:“你敢让我搜一下吗?”
白子雄呵呵一笑,极其暧昧地说:“欢迎亲爱的你,来亲密接触!”
“死不要脸的臭流氓!”梅朵说:“蛤蟆,扶我去馥郁家。”
“是,总裁!”
阿珠冲屋里喊:“阿爸,我走,我和梅姐姐后天再来看你。”邱老头闻声走了出来,一直目送梅朵她们下山,迟迟没有进屋。梅朵夸赞馥郁:“干的不错!不过这里的几个头,可以稍微用点力,应该能挤出来。你站边上,我来。”
梅朵亲自给乃利挤压毒疮,边说话,边用力:“乃利,以后不能再吸毒了。你长这一身的毒疮,跟你吸毒是有关联的。你明白吗?”乃利刚回答了个“嗯”字,就马上叫了一声:“啊——”噗呲一声,只见一团白乎乎带浓水的赃东西,直接溅在了梅朵的衣服上。“好了,马上用猪蹄汤清洗,然后上药膏。”
“梅姐姐,你这衣服……”阿珠拧着眉毛说:“好恶心啊,怎么办?”
“是啊,都溅衣服上了。”馥郁说:“要不,换我的衣服可以吗?”
梅朵笑了:“一件衣服而已,回去换掉洗个澡就行了,大惊小怪什么呀?赶紧给乃利清洗、上药啊!你好好照顾你弟弟,我后天再来给他上金蟾膏。”
“真的谢谢你,梅姐姐!”馥郁被感动了,一直送到山下。
梅朵洗过澡,换了身一字宽领黑色的丝绒长裙,然后支开阿珠,把蛤蟆叫进了更衣间:“有信号吗?联系上了吗?有没有定位?”蛤蟆从西装的内兜里掏出手机,边还给梅朵,边说:“半山腰就有信号,联系上了,而且已经定位!”
“那他怎么说?”
“他说马上制定最终方案,而且明天会派人过来送什么…….哦,送单兵终端。他说丛林里手机没信号,部队里的设备就不一样了。”“明天?”梅朵微微一笑:“你明天是得准备不少草药呢!”
前天晚上,梅朵在电话里告诉秦震韬,她准备从高岭村出发,让他发条安全路线过来。哪料到,秦震韬在地图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个高岭村。秦震韬说:“我估计是叫法不同,或者是当地登记不规范造成的。你想办法在高岭村给我打电话,这样就能通过卫星定位,来明确具体地点了。”
在高岭村打电话谈何容易,白子雄几乎是寸步不离。蛤蟆拿钱出门买手机那次,伪娘就派人派车紧紧跟随。后来因为梅朵的发飙,白子雄虽然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派人监视,但只要蛤蟆开着那辆香槟色的奥迪出门,庄园外面的一辆黑色轿车必定尾随。庄园外面的车,你能硬说是他白子雄派的人吗?蛤蟆每天早上都会出门一次,帮梅朵采购吃的、穿的、用的,以及后来所需的中药和西药。你一个贴身保镖,办完差事不守着美女老板,管自己四处游荡,那不招白子雄怀疑吗?
无奈之下,梅朵只能利用白子雄的弱点,用一方手帕,两句诗,让他自己在高岭村支开蛤蟆,蛤蟆这才有了避开耳目打电话的机会。蛤蟆真心夸赞:“总裁妙计,果然厉害呀!”梅朵莞尔一笑:“你这马屁,拍得很一般。”
蛤蟆刚想离开,结果实在憋不住,就问:“总裁,你是怎么料到,白子雄会一步一步跟着你的妙计走呢?你抽了他,他不生气,还……”梅朵笑着反问:“如果是你儿子哈根杰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你盛怒之下会怎么做?”
“先劝,劝了不听,那就只能打啊!”
“没错!你的打,叫恨铁不成钢,是父爱的一种表达方式。白子雄本就是个多思多想又自作多情的人,他当然会认为我的挥枝抽打,包含了类似恨铁不成钢的情愫。所以,当我要赶他走,说想休息会儿的时候,他反倒会用柔情,来回报我的恨铁不成钢。这个时候,我再把手帕往脸上一盖,一切都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了。”
蛤蟆很认真地问梅朵:“总裁,我知道自己不够优秀。那天在宴会现场,我听见你和他已经约定三生了。我不奢求别的,只求有他当你丈夫的三生里,你继续当我的总裁,管着我,罩着我可以吗?”
梅朵哈哈大笑:“你赶紧滚蛋,太肉麻了!”梅朵藏好手机边说,边赶蛤蟆。蛤蟆是边开门边说:“这就敲定了,三生之约,你不许耍赖!”门刚打开,蛤蟆就看见白子雄已经站在了楼梯口。
“活腻了吧你?”白子雄咆哮:“你居然敢跟她定什么三生之约?我一枪崩了你信不信!”白子雄说完就直接拔出那把精致的手枪,然后快速上膛,对准了蛤蟆的前额。梅朵急忙夺下那把枪,当即怒骂:“白子雄你疯啦?话都没听清楚你就拔枪顶着人家的脑袋,你简直太令我失望了!”
“他跟你定三生之约,把我白子雄当什么了?”
蛤蟆想解释:“我是说……”
“他要我连续三生都当他的总裁,管着他、罩着他,不可以吗?”梅朵说:“谁都没资格反对,因为…..我很乐意!”
白子雄听了一愣,不再多说。梅朵反倒来劲了:“动不动就拔枪,你是总角之龄的孩子吗?骂不听,打不好,我真是失望透顶!”
白子雄像个做错事情的孩子,努了努嘴说:“以后……以后都听你的还不行吗?别生气了,生气……对宝宝不好。”
梅朵深呼吸了一下,说:“这枪我没收了!明天你带我去林子后面,教我怎么用。以后再敢动不动就拔枪,我就一枪崩了你!”白子雄抿着嘴,忍着笑,那脸上的表情很是奇怪。
“你乐什么呀?”梅朵问。
白子雄挠了挠耳朵,说:“这把枪,我本来就是给至爱准备的!”
梅朵听了情不自禁地哼了一声:“准备让她一枪崩了你啊?”
“十载独听潇湘雨,总怜芭蕉凄楚声。对影苦挨至天明。难得红颜醉倾城,共剪西窗话从前。心似久旱缝甘霖。”白子雄幽幽地叹息着说:“我也曾是大好青年,有理想有抱负。命运如此作弄,不是我想要的。我现在别无所求,只想和你共剪西窗,爱你宠你保护你!”蛤蟆听了,直接打了个冷战,说:“比……比我肉麻多了!”
梅朵向蛤蟆使了个眼色:“滚!”蛤蟆点了点头赶紧消失。梅朵看着眼前的白子雄,的确不俗。玉树临风才情四溢,只可惜,人走邪路,又是迟到者:“如泣倾诉浣溪沙,一阙似啼。谁人风雨总和丽,足休沾,邪路泥。还君所愿有至爱,红鸾梦绮。不忍扯袖离别去,落花时,词相依。”梅朵长叹一声,说:“饭后书房,共剪西窗!”
梅朵说完,关上了门。白子雄原地站着,一动不动。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女人,这就是能和他秉烛夜话,共剪西窗的梅朵。二十一世纪,几人还会过多苛求那平仄之韵,所求的,无非是可以彼此即兴相和的那种雅兴。如泣倾诉浣溪沙,不仅说出了他那一阙的词牌名《浣溪沙》,还道出了词意和她自己的感受。一阙似啼,简直妙不可言啊!谁人风雨总和丽,足休沾,邪路泥。呵呵……那是在训导他,谁的人生能一帆风顺?但无论如何,也不该走邪路。
还君所愿有至爱,红鸾梦绮。这句一语双关,可以是指她自己,也能说是在指别人。不忍扯袖离别去,又再度埋下伏笔。可以是决定不离去,也有可能是离去前的感叹,一语双关。落花时,词相依。这一句啊……是他白子雄苦苦等候了十五年所奢求的幸福生活。她不但说出了她此阙的词牌名《落花时》,还让他含笑闭目想象着,落花飘零的时节里,他和她相互依偎着,望着窗前的花瓣雨,一起作诗填词。梅朵啊梅朵,老天成全,让我遇见了你。你若离别去,我还怎活命?
她发出指令,饭后书房,共剪西窗。白子雄再清楚不过,今晚书房里,他得有问必答句句实言,要不然的话,就没了今后秉烛夜话的机会。
靠在门上的梅朵感觉自己很无耻,她利用白子雄对诗词的狂热,不止一次地投其所好,来牵引他往自己设计的圈套里走,一步一步地临近悬崖。白子雄的性格,注定了他不是个会束手就擒的而是个情愿纵身一跃,为爱殉情的疯子。梅朵不忍心见他在铁窗里抑郁而死,更不想看到他身中数枪倒在血泊中抽搐。梅朵知道结果,一旦被他追上带回庄园,那就是自己必须为了腹中的孩子委身于他的开始。万一白子雄穷追不舍,被特战大队团团围住,那就是他告别世界的末日。两种结果,都不是她想要的。那么,又该如何确保不被他追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