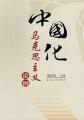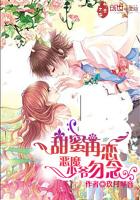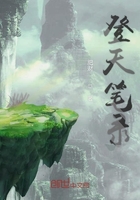“人与命运的搏斗”可以说是悲剧的最普遍主题——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那些好发空洞、单调而又不知所云却甜腻得令人恶心言论的当代美学家们异口同声说出来的看法。这种说法被提出的前提假设就是:人具有自由的意志(意欲)——无知的人都会抱有这一奇想;另外,我们还有一项绝对命令——不管命运怎么阻挠,我们都必须要达到这一个绝对命令的道德目的,或执行其指令。以上的那些先生们就是从这种说法中获取鼓舞和喜悦的。不过,他们所谓的那个悲剧的主题却是一个很可笑的看法,因为我们要与之搏斗的那个对手根本就是一位隐蔽着,且戴着雾一般头罩的侠客;所以,我们所发出的每一击都会落入虚空;要想机关算尽地去躲开这一对手的攻击,但却偏偏一头扎到他的怀里,就如拉乌斯与俄狄浦斯王两人所遭遇的情形相同。再者,命运原本是全能的,我们与之搏斗的做法简直就是一种可笑至极的大胆妄为。因此,拜伦的这种观点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与命运拼争,
就像玉米束子反抗镰刀。
——拜伦《唐璜》
莎士比亚对此也曾有这样的看法:
命运,显示您的威力吧:
我们并不是自己的主宰,
命中注定的就必然发生,
那就让它发生吧!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第 1幕结尾
古人通常把命运看做某种隐藏于整体事物当中的必然性,而这种内在的必然性既不理会我们的意志和请求,也不会考虑到我们自身的罪孽或功德;它只管去指引人类的事务,并且,会通过一种隐秘的关联,将那些从表面上看来彼此并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根据命运的不同需要各自牵引在了一起。如此乍一眼看上去,这些事情只是很偶然地走在了一块,但从更高一层意义上讲,这都是由某种必然性所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通过神谕、占卜和睡梦等其他方式去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也会成为可能了。
只要是由上帝决定的命运一定是某种被基督化了的命运,也就是要把命运变成上帝为这个世界争取最大益处的旨意。
我自己认为,悲剧里面合唱的美学目的首先就在于:被暴风骤雨般的强烈激情所震撼的剧中角色,最好在他们对事情表达看法的时候,也能让观众听一听那些旁观者冷静的见解;其次,剧中由剧情逐步且具体地展现出来的基本道德教训,也能让合唱在同一时间内以一种抽象的、因而也就是比较简短的方式表达出来。就跟音乐中的低音一样,合唱队就是以这一方式来发挥作用的:在后者的持续伴奏下,我们也就能够听闻那演奏当中的每一单个和音里面的基本音声。
就如地球泥石层里的化石模型给我们展示遥远太古时代的生物形体——这种古生物化石模型历经了无数的千百万年,现今仍保留着自身那些昙花一现的生物痕迹;同样,在古代的喜剧里面,古人又给我们留下了能够真实体现他们欢愉生活以及活动的永久记录。这些清晰而又精确的记录就好像是古人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为一种美好、高贵的生活立此存照,用以留传给后世的绵延子孙——匆匆即逝的生活本质的确是令他们不由得扼腕叹息。现在,如果我们给那些躯壳、骨架重新注入血肉,将柏拉图斯与泰伦提乌斯的剧作再次搬上舞台,那么,逝去已久的美好生活又将生动鲜活地再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与古代所留下来的镶嵌地砖一样,经过清水冲洗之后,就会把其本来的色彩重现出来。
发自和刻画了德国民族真实本质以及精神的唯一真正喜剧,除《米娜冯巴恩海姆》之外,就是伊夫兰的剧作了。就如这些戏剧所忠实表现出来的民族优点一样,整个戏剧作品的优点并不是在思想智力的层面,而更多的是在道德层面;但我们却可以说,法国和英国的喜剧情形则正好是与此相反的。
我们说德国人所拥有的独创性是绝无仅有的,一旦他们的独创性确实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像席勒和施莱格尔那样,用那些每行必须四个重音的双行押韵诗律去干涉、指责他们的创作。我不得不说席勒和施莱格尔在对待伊夫兰的问题上是有失公正的,他们甚至对待考茨布,也做得很过分。同样,人们现在在对待罗巴克的态度上也不是很公平的;但人们对由那些蹩脚的粗制滥造者所炮制出来的闹剧,却给予了高度的赞许。
总体而言,戏剧——作为真实反映人类生存、生活的一面最完美的镜子——根据它对人类生存的真切认识,因而在其目的和意图方面,可以被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同时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级,戏剧只会停留在最纯粹有趣的那个层面;剧中的人物在追逐同我们相似目标的过程中,唤起了我们心底的那份同情。情节是通过剧中人物所耍弄的诡计以及他们的性格和各种机缘巧合而铺展开来的;插科打诨及妙语警句之类则都只是作为这一类戏剧的调料来用。第二等级的戏剧会变得很令人感伤;它们刺激起了我们对剧中主人公,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怜悯和同情。剧情变得哀伤、感人;但到结尾的时候,它们会使观众回复平静、得到满足。而最高一级以及难度最大的戏剧则旨在营造一种令人感伤似的悲剧意味:生存中的深重苦痛和磨难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所有人为的努力与奋斗都将化为虚无——这就是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我们被剧情深深地震动了;我们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求生欲念开始回转头来拒绝生命——这是悲剧中所回荡着的一种直接的或者是背景的和音。
当然,我并不是把所有的戏剧都考虑在内,比如那些带有政治倾向的戏剧。它们只会向那些媚人的大众暗递秋波,迎合他们那点心血来潮的趣味。这些都是我们当代文人比较喜爱的批量产品。类似于这些剧本很快——通常是在第二年——就会被人扔到一边,就如那些已经过时了的日历一样。不过,仅这一点是不会让我们那些写作匠烦心的,因为在他们对文艺女神的呼喊中就已经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恳求:“今天就赐给我们每一天的口粮吧!”
人们都说所有的开局都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在戏剧艺术里面,与此相反的说法才是最准确的:所有的结局都是很困难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数不胜数的戏剧作品中得到证明:这些剧的前半部分可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在此之后,戏剧的发展就开始变得模模糊糊、淤塞不畅、摇摆不定,尤其是到了那声名狼藉的第四幕;到了剧的最后,不是搞出一个牵强附会,难合人意的结局,就是结局被观众早先就预料到了;或者,直接就像《爱弥尼亚加洛蒂》那个剧本那样,最后弄来一个令人倒胃的结尾,让观众们扫兴而归。
结尾的构思如此困难,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把事情弄混乱总要比把事情理出头绪来容易得多。同时,也存在这方面的原因:戏剧在刚开始时,我们交给作者的只是一张白纸,接下来就需要他去自由发挥了;到结尾时,我们却对剧情有了具体的要求:要不是皆大欢喜地结束,要不就是悲惨凄凉地收场。而人事的发展并不会随意向某一个确定的方向走去。一个好的结局应该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它容不得半点牵强附会;而且,至于怎么去收尾也不能让观众预先就轻易地察觉到。同样,史诗和爱情传奇也是如此。只是由于戏剧所具有的紧凑特性,所以结局的问题才会显得非常突出,因为创作结局的难度已经加大了。
卢克莱修所谓“无中只能生无”的说法,同样适用于优美的艺术。优秀的画家在创作历史图画的时候,通常会以现实中存在的人作为模特,绘画中的人物头像也同样取自生活中的那些真实面孔。画家依据这些真实原型的美和特征又使之变得理念化。我相信那些优秀的小说家与他们所做是一样的:他们在现实中所认识的人物变成了他们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原型,然后,作家再根据自己的意图再将这些原型化作理念和补充完整。
小说家的任务并不在于叙述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而是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处理得引人入胜。
如果一部小说在刻画内心生活处所用笔墨太多,表现的外在生活越少,那么这部小说的本质也就会越加高贵。这个比例被视为识别小说等级的典型性标志,它适用于各个不同级别的小说,自《特里斯坦桑迪》开始,一直到粗糙无比、充满奇情与动作的骑士故事和大盗传奇。的确没有太多情节的《特里斯坦桑迪》与《新爱洛依丝》以及《威廉迈斯特》里面的外在事件屈指可数。甚至连《堂吉诃德》里面所叙述的行动事件也相对不是很多,而且,那些还全是些毫不起眼和极具滑稽意味的事情。这四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它们类别中的最突出者。我们再拿起约翰保罗的奇妙小说看看:就在那一点点的外在生活的基础上,所展现出来的内心生活却是那么的丰富。甚至就连华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内心生活同样也是很明显地压倒了外在的生活,而后者的出现也总是以带动前者为目的。但在那些低档小说里面,对外在事件的描述,就是为了这些事件的缘故。所谓艺术就在于用尽量少的外在事件,去激发剧烈的内心活动,因为我们真正的兴趣就在于那些内在的东西。
我可以很坦率地承认:《神曲》所享有的巨大盛名在我看来是有点夸大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神曲》中的基本思想太过荒谬;其结果就是到了《地狱篇》,它立刻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基督教神话中最令人反感的一面。作品风格以及隐喻的晦涩难懂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傻瓜最喜欢也最赞叹
别人用花哨的语言和刁钻、古怪的字眼
向他们讲述的东西。
——卢克莱修
尽管如此,《神曲》中简洁且几近精炼的风格以及表达的力度,更为重要的是,但丁自身所拥有的那无与伦比的想象力——这些都着实的令人惊叹。正因为如此,但丁就使他所描绘的那些并不具可能性的事情带上了某种具体的、可见的真实性,也就是相当于睡梦中的那种真实性:这是因为那些事情是但丁自身不可能经历过的,所以,看起来这些东西他肯定是在梦中见到过了,以至于能够用如此清楚、精确和生动的笔墨把它描绘出来。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在第十一节的最后,维吉尔详细描述了破晓时分、星星逐渐下沉的情景,但他却忘记了自己那时侯正在地底下的地狱中;而只有到了最后——这主要部分的结尾处,他才终于“从里面出来,又重新看到了星辰”(《地狱篇》)。在第二十节的末尾,我们再次看到了同样的错误。难道我们此时可以认为维吉尔正揣着怀表,所以,他知道这时候发生在天上的事情吗?依我的看法,这个由记性所导致的笔误,其糟糕程度和塞万
提斯那闻名于世的关于桑丘潘莎的驴子的笔误相比,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丁所创作的这一作品,其题目应该说是相当地准确、独特,而且毋庸置疑它是含有讽刺意味的。喜剧,是吗!就这样的上帝来说,这个世界确实就是一出喜剧:在最后的一幕里,这个上帝报复欲望的永无厌足以及折磨方式的匠心独运,使他从那些对生命忍受没完没了、漫无目的的痛苦情景中获得幸灾乐祸的快感。这些生命都是由上帝自己在百无聊赖中,漫不经心地创造出来的;那些生命只是因为自身的发展违反了上帝的旨意,而且,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做出并相信了一些不能令上帝高兴的东西。除此之外,同上帝的那些闻所未闻的残忍手段相比,所有在《地狱篇》中遭受如此惩罚的罪行都微不足道。的确,我们在《地狱篇》中所遇到的所有魔鬼与上帝本人相比,其凶恶程度要逊色很多,这是因为那些魔鬼依仗上帝的权威行事,自然也是秉承上帝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