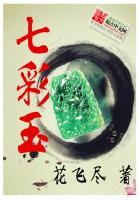曹兴踉踉跄跄打晃站不稳,瞳仁血丝乱系,恶狠狠瞪视沈应,但对面一同喝酒的兄弟同样脸色青黑,鼻孔嘴巴冒血,咕咚一头直挺挺栽倒,抽搐几下没了动静,曹兴大吃一惊,痛苦地捂住腹部,缓缓委顿在地,嘴里断断续续道:“有人……有人……下毒……”瞪大双眼死不瞑目。
约过一盏茶功夫,本已死去的沈应坐起,擦掉唇边血迹,起来用脚把曹兴挑翻身,从他怀里搜出羊皮卷、几两银子,听到外面响起足音,果断跳窗遁走,在行人惊呼声中翻身跃上房顶,几个闪跳起落不见踪影。
厢房门两侧推开,一名体态妖娆的年轻女子缓步入内,身后房门自动合闭,地上血迹犹温,可这女人却视如不见,腰间红色百花褶裙随着她轻盈婉媚的脚步左右摇摆,如同繁花一直开到临窗的桌前,“啊哟!”曹兴一声痛嗷从地上弹起,抱着被踩红的手指呼呼吹气,“师父,你踩到我手了,好痛,你得赔。”
佘倩莲扭身坐在沈应的位置,眼望窗外,懒懒地打个呵欠,以手托腮,食指在桃花瓣颜色的面颊轻弹,“你还知道我是你师父呀。”她的声音沙甜软糯,有种娇滴滴的酥媚韵味。
曹兴捂着心口惨叫,“师父这话伤人,就像一把尖刀深深插进我心口。”
佘倩莲咯咯笑道:“你好无聊。”
“别这么说嘛。”曹兴贪婪地在她身上扫视,涎脸笑道,“师父您怎么来啦?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要是皱一下眉头,我曹兴就是丫头养的。”
“人家不放心你。”佘倩莲水淋淋的妙目横他一眼。
“有什么不放心的?老子又不是三岁小儿。”曹兴直勾勾地盯着少女,“咯嗤咯嗤”狠嚼胡豆。
“因为小六啊。”
曹兴得意道:“师父您就放心好了,就那小子,打架我让他一只手,下毒更不用说,我跟您学了十年,他才学了十天而已,他以为在酒碗里下毒再跟我换碗,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道我早就服下解毒药,下次见面非吓他个屎尿齐流不可。”
“知道你能干,你厉害,所以才不放心,他要是被你害死了,我也跟着倒霉,最后警告你一次,再敢多事添乱,就算你再能干,我也宰了你喂狗。”
曹兴被她左一句“能干”右一句“能干”撩得心头火热,毫不在意她话中杀气和威胁,色授魂与地道:“我怎会害他?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佘倩莲拿过沈应的酒碗,撇嘴道:“嘴里叫朋友叫兄弟,暗地放冷箭下毒手,你们这些臭男人没一个靠得住。”
“冤那。”曹兴举起双手大叫,“这都是那小子干的好事,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你别一棍全打死,最起码我就是例外,百年难遇的好男人,虽然他屡次坏我好事,无端指责我,还在背地踩我影子说我坏话朝我吐唾沫,可我从来都是以德报怨……啊,别喝!”他见佘倩莲红唇凑近酒碗,连忙大呼阻止,“这碗那小子用过,脏。”转头朝外大喊小二拿酒碗来。
佘倩莲转动手腕,清亮的酒汁在碗中飞速旋转,风情万种地白他一眼,“虚伪,这碗上有毒我会不清楚?你在他碗里放蛇蝎草,他在你碗里放断肠散,你们两个坏胚半斤八两,一股脑死掉才好。”
曹兴骨头都软了半截,痛心疾首地道:“师父你说的没错,这坏胚太不是东西了,我好心请他喝酒,谁知他包藏祸心,竟然下毒谋害我,要不是看师父您面子,大爷非弄死他不可。”这时小二拿酒碗上来,一路上腹诽不已,喝酒就喝酒吧,酒碗跟你们有仇么?一会儿弄碎一个,一会儿弄碎一个,开门看到刚才喝酒的男子变成娇滴滴的美女,顿时舌头打结,说话都结巴了,曹兴一脚将他踢个跟头,“看什么看,再看老子挖你眼珠!”撵狗一样把人轰走,气呼呼关上门,转头立即换上笑脸,掂起酒坛给师父倒上一碗,自己也满上举起跟她一碰,仰头喝光。
“好辣。”佘倩莲吐吐舌头,粉颊爬上一层醉人的晕红,曹兴喉咙上下滑动,笑得合不拢嘴,再给她满倒一碗,双手端平递给她,豪气干云地道:“我们师徒难得相聚,今天一醉方休,来,干了。”
“不,不喝了,醉了。”佘倩莲摆摆手,娇靥越发红润迷人,白皙的脖颈也染上霞彩,湿淋淋的美目朦胧迷离,薄薄的嘴唇潮湿润泽、娇艳欲滴,让人忍不住想一亲芳泽,曹兴咕咚吞咽口水,殷勤劝道:“再,再喝一碗,就一碗。”
“你先喝,你喝一碗,人家喝一碗。”佘倩莲娇躯软软地伏在桌子上,左臂枕着螓首,拿起酒碗递到他面前。
“好,好,好。”曹兴看女人喝醉,兴奋得浑身发抖,仿佛嗅到了她唇间潮热的芬香,双眼通红地接过酒碗一饮而尽,碗口朝下,“该你了。”
佘倩莲不理他,从桌上撑起身子,慵懒地打个呵欠,“臭淫贼烂淫贼,我都守三晚上了还不现身,让我抓住定要叫他好看,好困哦,找个地方睡觉去。”
“好啊,好啊。”曹兴眼睛啪的一亮,搓手笑道,“我知道有间客栈,位置隐蔽,服务热情,房间装修高档豪华,隔音效果好,离这儿不远,徒儿这就带师父去。”
“你?”佘倩莲轻挑娥眉斜视,笑吟吟地摇头,“你不能去。”
“为什么?”曹兴不服气地大叫,“我怎么不能去了?”
佘倩莲仪姿优美地走到门前,回首掩唇娇笑,“你去拉稀,人家可不等你。”
“什……什么意思?”曹兴脸色微变,心里生出不好的预感。
佘倩莲委屈地道:“人家被你喂了一把天女酥,身上又热又软,满脑子胡思乱想,一个不小心,把泻药掉进你酒碗里了,乖徒儿,你会怪师父吧。”
“你……”曹兴满心绮念化为乌有,嘴角抽动眼梢痉挛,“你在我碗里放泻药?”肚子哗哗啦啦直响,一阵汹涌便意袭来,顾不得和她计较,夹紧臀沟风风火火冲出房门,一路怪叫“让开让开”直奔茅房。
……
荒僻无人的小巷,沈应脸色铁青地把空白羊皮卷撕成两半,用力过猛牵动伤处,胸口一阵发痛,深深呼吸平息怒气,看天色还早,出巷口沿着河堤闲走,不知不觉又走到雁山附近,钟铃梵唱从红墙内飘传而出,林树之间露出几角殿舍宝塔,朝南大门上,黑底金边的匾额端端正正写着“无尘寺”三个鎏金大字。
门前左侧停着许多马车,右边一串摊位,售卖一些供香素果、字画玉佩、符纸香烛,临河岸边有两棵水桶粗细的银杏树,树叶已经落尽,喜鹊衔来树枝在树梢架窝,沈应走过去背靠树干坐下,云纹石栏外,水面波光粼动,如同洒银,阳光落在身上,使人昏昏欲睡,半梦半醒间,眼前光线一暗,五六个原本在河边倚靠栏杆晒太阳的乞丐脸色不善地围在左右,一名瘸腿老丐手拿竹棍轻扣石板,“新来的?”
沈应睡意全无,警惕地起身,“我不是要饭的。”
几个乞丐狞然变色,“怎么着,瞧不起我们要饭的?”
瘸腿老丐抬手压下众怒,上下瞧他两眼,“劳驾换个地方歇脚,我们几个吃喝拉撒都在这里,脏得很。”
沈应拱手离去,几个乞丐赶走竞争者,骂骂咧咧返回原地,你靠我我靠你挤成一团,继续晒太阳睡觉。
少了那把匕首,面对几个叫花子都觉得危险,路过肆桥边马记铁匠铺,花一两银子买了一把揣在怀里,徘徊杨柳枝巷,一直等到太阳下山仍然不见侯归里人影,出城时天已经擦黑,月出东山,洒落冷峭辉芒,远远瞧见门前火光闪烁,阵阵笑声喧哗吵闹,原以为有客人,走到近处才发觉不对,屋里漆黑,门前大火烤着香喷喷的狗肉,五个粗汉分坐周围,喝酒吃肉,不时发出大笑。
“回来啦,等你好久了。”朝东坐的汉子最先看到沈应,像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样笑容满面地热情招呼,沈应认得这人是昨天和胡屠打架的赖四,一眼看过去,其余三个也在,唯独坐在北面身穿灰衣的中年汉子不曾见过,笑声一静,几双眼睛齐刷刷看过来,戏谑、冷笑、轻蔑不一而足,姬艾高声叫道:“胡屠,坚持住,你儿子看你来了。”
胡屠脸孔青肿,眼睛鼻子嘴巴都在流血,双腿朝外翻折,早被他们打断胫骨,脖子上套着拴猪的麻绳,另一端绕过横梁捆紧陈氏双手,这女人赤裸躯体上青一块紫一块,脚底放一块烧红的铁板,胡屠涕泪横流,脸色青中带白,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拉住绳索,以免她碰到铁板烫伤,双眼充血突出,仇恨、凶狠都已经变成绝望和哀求。
“义儿……”陈氏哆嗦嘴唇,用尽力气喊了一声“快跑”,脑袋无力地垂下去,胡屠双眼暴睁,泪水夺眶而出,被割去舌头的嘴里“啊、啊”凄吼。
沈应向前迈出右脚,赖四笑眯眯拦住去路,亲热地道:“来来,过来喝两杯暖暖身子,早知道兄弟会来,我定去醉梦楼搬两坛将军醉来。”沈应迈出左脚,王虎吐掉嘴里的狗肉,喷着酒气用砍柴刀挑起他下巴,恶狠狠地道:“怎么着?四哥请你喝酒,不给面子?”
“放了他们!”
“啊?”赖四侧头把左耳对向他,用小指掏掏耳洞,转头看着身后几个兄弟,一脸疑惑地道,“这位兄弟刚说什么?我好像没听清楚!”
王龙瞪眼狞笑,“放个屁!”
“不要生气,以和为贵。”姬艾把王龙手臂按下,嬉皮笑脸道,“既是兄弟开口叫咱们放,咱们多少要给个面子不是?瞧你们也不是那块料,还是我来吧。”背对沈应一撩袍脚,撅起屁股放个响屁。
赖四几人齐声笑骂,一边用手扇风一边后退,“矮鸡你恶不恶心?一天到晚屁滚滚。”
“矮鸡他娘就是吃屁长大的。”王虎手捏鼻子大骂,
姬艾鄙夷道:“是你自己不行,少怨别人。”
“老子不行?有种比过,输的是孙子。”
“比就比,谁输谁是孙子。”怒气冲冲定下赌局,姬艾上前拍拍沈应肩膀,脸色深沉悲痛,“都说我姬艾坏透顶,其实他们不知道我这人最心善,昨儿吃那么大亏,十几寸长的口子,放个屁都疼得紧,按道理要活剥了这黑厮的,可我下不去手啊,小弟我不想把事情做绝,要我放过这杀猪的不难,只要你把我屁股舔干净,我姬艾二话不说扭头就走。”
那稳坐的黑汉忽然高喝,“当心!”示警声还没落下,惨叫已然响起,“啊!我的眼睛,我……”棚顶流光倏闪,姬艾凄厉尖号戛然而止,一条细细红痕出现在他脖子上,鲜血夺涌而出。
“矮鸡!”赖四瞠目大叫,王虎怒吼“我去你姥姥”,举起砍柴刀狠狠劈下,虽说不过街头斗殴的水准,但这含恨一刀力道不小,要是砍中,脑袋都得跟柴棍一样分成两瓣。
沈应抽身飘退,从刀光匹练下脱出,只要左足一点,趁势向前袭进,王虎此时空门大开,必定没处可逃了,但他没有这样做,灰衣汉子气度森严、气息绵长,绝非庸手,最紧要的是他所在位置,真要叠浪杀进,等于迎头送到他手上,王虎还不知道自己小命被人掂量了一道,卯足力气连劈几刀没砍到人,又恼又恨地怒骂起来,用力将笨重的柴刀掷出,额前空气一震,一股森冷寒意擦着前额眉尖掠过,王虎汗毛都竖立起来,想都不想地使个懒驴打滚躲开,心有余悸地摸摸眉毛,一见指上鲜血,恐惧顿时变成恼恨,咬牙切齿地叫道:“乖孙儿,你只会躲吗?有种跟你爷爷打过。”
赖四抽出藏在背后短刀,从后面堵住沈应退路,刺啦挑破他的衣袖,精神一震叫道:“并肩上,弄死他。”王虎从柴堆里抽出一根四尺多长的竹竿,挥舞得嚯嚯生风,王龙掏把尖刀找机会偷袭,背后风声一紧,沈应拧身一肘正中赖四鼻梁,赖四双眼迸泪,鼻血簌簌落下,囔着鼻子叠声咒骂。
沈应心神全在那灰衣汉子上,举刀格挡王虎扫来的竹棍,要是那把寒铁匕首,就算坚硬的黄花梨木也毫不费力切成两断了,可这一两银子买的粗糙货实在不怎样,刀棍交接,发出沉闷声响,胳膊震得酸麻,匕首险些脱手,王虎力气上占了便宜,心中大喜,谑笑道:“瞧你还能耐,来呀,爷爷打得你满地找牙。”
赖四擦去鼻血,刀尖照他腰眼捅来,王龙大叫一声“看刀”,手上却甩出大捧石灰粉,白扑扑烟尘刚起,一条人影迅疾穿出,闷哼和倒地声同时响起,一掌击退王龙,沈应半空中不可思议地折转飘旋,倏然落在赖四背后。
“不要!”赖四目光僵硬,瞳孔放大了一倍不止,脖子上尖锐的刺痛感令他魂飞魄散,“有……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王虎刹住脚,手中竹竿遥指敌人,怒容满面吼道:“敢伤四哥一根汗毛,叫你全家陪葬。”
“闭嘴!”赖四恨不得敲碎他牙齿,这时候还威胁人家,脑子喂狗了吗?发现匕首只是割破点儿皮肉,没有下死手,心思活泛起来,僵硬地挤出讨好笑脸,“兄弟好俊的功夫,赖四有眼无珠,输得不冤,只是我们几个都大牢在籍囚犯,早晚要掉脑袋的,死在这里,官府追查起来,势必连累兄弟,朋友好交仇人难做,兄弟莫要置一时之气,自毁前程。”
沈应眉毛都没动一下,看向朝南端坐的汉子,“你不打算出手?”要不是忌惮此人,就这四个歪瓜裂枣,他早一刀一个砍翻了。
他们打生打死,这汉子金刀大马坐在一旁倒像看戏,把啃净的骨头丢进火堆,轻飘飘地反问,“我为什么要出手?你想让我出手?”
王家兄弟一脸愕然,赖四愣了一下,哭丧脸叠声大叫,“大哥救我!”
“要是姬艾没死,救你一命倒也无妨,现在嘛,没那个必要。”
赖四怎么也没想到靠山居然靠不住,又是愤怒又是恐惧,尖声叫道:“你,你这……别忘了你是跟我们一起出来的,我死在这里,你回去也无法交代。”
“不劳四爷操心,我原本就没打算回去,过了今晚,这世上就再没有刘纲这号人物了。”
赖四听他叫四爷,心更往下沉,嘴里一阵发干,“她说过,她说过会救我出去,她用得着我……”
汉子微微一笑,双眼亮如寒星,“你很聪明,想必已经猜到她身份,像你这种家伙跟在她身边,我怎能放心?”不理会赖四杀人般目光,汉子若无其事地在姬艾衣服上擦去油渍,起身哼着小调从目瞪口呆的王氏兄弟中间穿过,走出草棚踏上大路,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
“站住!”
那汉子脚下不停头也不回,“想报仇的话劝你还是省省力气,你轻功不错,但在我手下照样撑不过十招,不杀你不是不想杀你,而是不想杀他们,毕竟叫了我几年大哥。”
看着那个越走越远的背影,赖四脸上因为愤怒而扭曲,眼底却藏着深深的惧意,“兄弟,有话好说。”
“放开四哥!”王龙揪住胡屠头发,把砍柴刀架在他脖子上,狞笑道,“不然我宰了他。”
赖四真想抱住王龙亲一口,按捺喜意装出一脸懊悔,“兄弟,我们跟胡屠无冤无仇,其实也不想与他为难,都怨侯归里那狗贼,是他让我们找胡屠榨油,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兄弟你高抬贵手饶过这次,我赖四发誓,以后绝对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对对,我们改。”王虎连连点头。
赖四又叹道:“这些年我私下里攒了一笔钱,总有一百多两,明天一早送来,就当给兄弟赔罪,你看如何?”
胡屠“呜呜”直叫,急切摆头哀求,王龙刀口压紧他咽喉,“老实点。”胡屠奋力一挣,脖子压住刀口一抹,溅起大蓬猩红,王家兄弟大惊失色,赖四瞳孔缩如针尖,双手飞快抓向匕首,一股剧痛瞬间贯穿神经,视线立刻模糊起来,恍惚看见王虎扑过来惊怒交加地喊着什么,可他一个字也没听清,“咕咚!”耳朵里全是这个动静,越来越慢越来越远,片刻归于沉寂。
“跑啊!”王龙急喊一声,掉头向屋后树林逃窜,耳边冷风呼啸,冻得耳朵发疼,听到弟弟濒死惨哼他也不敢回头,这个蠢猪……使出吃奶的力气埋头狂奔,只要挨过今晚,把这里的事一五一十告诉官差,他们自会收拾这小子,还有刘纲,枉老子把你当老大供着,出卖我们居然还想过好日子,休想!眼前一花,一抹银亮锋芒飒然闪现,他急转右侧发足狂奔,跑出两丈多远,低头茫然看向心口,破麻袋似的瘫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