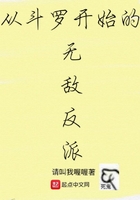又是周末。我从恍恍惚惚的梦境里醒过来。年岁的增长,从来不会让记忆增多,失去的岁月流光总会在梦回时分深深卡进我们的骨头缝里,一年年的日渐深刻,绝不远走,直至成为我们生命力的红痣,像某年某月疼痛惹来的烙印。我很痛苦自己这做梦的恶习,每次睡眠必有梦,就算那睡眠的时间再短,梦也会改头换面却换汤不换药地扑将过来。醒来,我就和梦瞬间分离,恍若未见。我俩这对奇怪的搭档莫非要相伴相杀终生,揉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苦涩一笑,醒来就好,——人这辈子谁不会梦几场?
“叮……”电话。谁的?希望不要是领导和老妈的。领导的督工和老妈的絮叨真是天底下最要命的磋磨啊。再瞅瞅,哈,陌生号码。这年头陌生来客都是不容易的人,要么是骗子,要么是传销,要么是找你干活的。我一边在心里感慨着,一边随手接通免提。
“喂……哪位……”我的声音带着晚起后的疲倦和周末阳光的慵懒。
“几点了?你这不会是刚醒吧?我是栀子。好久不见了,见见?”我像被谁定住了一样,一张年轻的甜美而爽朗的女子音容瞬间涌入脑海,那是个差点被我遗忘的老朋友了。我仿佛穿越到十多年前,我和她对面而坐。
她咯咯笑着逗我,那个俊对你肯定有意,看到你就脸红到脖子根。
我瞬间也红了脸,心突然慌起来,好似里面揣了只兔子,跳得人束手无策。我追着眼前比我高半头的明媚的女孩拍打,哪有这么回事,我都没跟他说过几次话,他见谁不是脸红啊?你再乱说,当心我撕烂你的嘴,然后告诉班主任去。
大约那时候班主任是我们的天,是我们的神,那个上学交不起学费的年代,总是白皙挺拔、一身白衣、步伐轻盈、神态静朗的年轻班主任恍若是江南水乡上空的总是无比温和的太阳,让我们惊艳。
“好的,好的,我错了,我错了,保证不说了我,逗你玩的嘛,着什么急呢?”她慌忙停下,连连告饶,任由我不轻不重地捶打她,一边挨打,一边求饶,嘴上带着疼,却满脸晃着笑。这惹得我愈发气急,终究不再下手,跺脚离开。
那时候的我们,那时候的我们啊……我连连叹息着,那时候真的是那么美,又那么要命的岁月。“好,必须见的。”我笑着冲电话那头说道。是的,必须的。隔着这么多的时光,这么多的人和事,必须见见。怎么能不见呢?
“那就回头见。还在我们学校东头的那个茶馆吧。”
那是个传奇一样的茶馆。那茶馆里连着网吧。紧挨着学校。每到散学和周末,那茶馆必然爆满。年青的十多岁的男孩女孩,沉静的老师们,周围的路过的不熟悉的人,都会在那茶馆里涌现。我却不经常去那,因为我穷,也因为我不爱热闹和太过忙碌。但是那个茶馆却是熟悉的,因为曾经班上有个很帅的哥们在那里泡了几天几夜最后被班主任大肆通牒,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以为那茶馆会早晚被拆除,但是一直到我们的学校迁移,那茶馆依旧倔强地矗立在斜阳里,终究不肯挪移半步。而当年的那个哥们据说也终究没能娶到他神魂颠倒的班花,潦倒半生。
那茶馆么?我微吁一口气。物是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