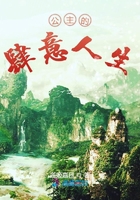刘仙堂一行回到郭家门外,孙大头满脸是血正躺在地上,五犬又往大头身上踹一脚,这才转过脸问刘仙堂:“你的老婆呢?”刘仙堂点头哈腰:“太君,我老婆出去了。我给太君报告的时候她出去了。”“到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刘仙堂皱着眉。“混蛋!”五犬抬手给刘仙堂一个嘴巴。刘仙堂挨了打,却一点儿也不沮丧,指着身后的砖头说:“太君,他可以证明见了赵富宾!”“噢,你的,知道?”五犬转头看着砖头。“啊啊。”砖头害怕,直往后退。五犬盯着砖头:“你的,不要害怕,说,赵富宾的,在哪里?”
砖头支支吾吾:“我爹被……啊啊死了,我……啊啊回去上坟、复三,在村头……啊啊看见了啊啊赵富宾……”“不对不对,是……”刘仙堂想让他改口。五犬大声喝斥刘仙堂:“你的!”然后一转脸看着砖头,“说下去,在哪个的村头?”砖头哆嗦着:“在我们、啊啊村头。”五犬问:“你们的,什么的村头?”砖头说:“大杨庄村头。”
“不对,是平乐镇村头!平乐镇!”刘仙堂大声叫喊。“给太君说,是平乐镇村头!”二孬吓唬他,“你不想活了?”
“五犬太君,”云鹤鸣大声说,“你都看了,刘仙堂在极力制造瞎话。时砖头是大杨庄人,他在村头见到的赵富宾,自然是大杨庄村头。砖头也说是在大杨庄村头。他今天在大杨庄村头见到了赵富宾,就说明赵富宾没有来过平乐镇。他没有来过平乐镇,我们咋能给赵富宾看过病呢?五犬先生,刘仙堂他是在诬陷!在陷害良民,你要明鉴啊!”
“太君,他十四岁就在郭一山家做工。他是郭一山家的亲戚。他说的村头,一定是平乐镇村头。砖头,是不是平乐镇村头?快说是不是?”刘仙堂极力引诱。“你不怕杀头了?”二孬也威胁他。
“你的!”五犬挥起指挥刀喝住刘仙堂和二孬,扭头又问砖头,“究竟的,哪个的,村头?”“啊啊,啊啊,大杨庄。”五犬一郎盯着刘仙堂,一步一步逼上前来:“你的,良心的……”“太君,太君!”刘仙堂害怕了,高声喊着,“我是亲眼看见的!我真的是亲眼看见的呀!”“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五犬一郎抓住刘仙堂的胸膛,使劲打他的耳光。二孬一见,连忙后退。刘仙堂挨了打,仍然辩解着:“太君,我的良心的大大的好!”“死了死了的!”五犬一郎把刘仙堂推倒在地,猛的拔出指挥刀,高高举起。“哎哟太君……太君!”刘仙堂惊叫着,满地乱爬。
“哎、哎哟……”当啷一声,五犬的指挥刀掉在地上。扭动着的五犬一郎像做了一个凝固了的高难度的舞蹈造型,再也动不了了!
“太君!太君!”翻译忙上前,欲搀五犬。“哎哟!哎哟哎哟慢……”五犬动不了,难受之极。刘仙堂趁机爬了起来。二孬快步上前,对着表哥耳语几声。刘仙堂连连点头,似乎魂又回到了身上。他小心地走上前,对翻译说:“长官,郭一山没用真本事,他是在应付太君!”“嗯?”翻译终于明白过来,对着五犬一阵低语。五犬瞪一眼郭一山,对翻译示意。翻译走过来:“郭先生,刘仙堂说你给太君看病没用真本事,是不是真的?”郭一山摇头。翻译盯住郭一山的脸:“那,为什么太君屡看屡犯?”郭一山不看翻译的脸:“三分治,七分养。太君他不养!”“不对!”此时的刘仙堂已经完全醒过神来,“太君这是扭腰,也叫习惯性扭伤。只不过太君扭得厉害,不好治了,但不能说治不了……”二孬上前:“对对!我表哥也是好先生,太君,让我表哥给您治吧?保证手到病除!”翻译看着刘仙堂。“你的,可以?”五犬一郎看着刘仙堂,眼睛里忽然有一丝亮光。刘仙堂看见了,连忙点头:“可以可以,我完全可以!”翻译用日语对五犬说:“太君,那就叫刘仙堂医一次?”五犬疼得咧嘴,想了想,就点了头。
刘仙堂忽然有了精神,他舒展了一下紧张的双臂,慢慢地走到五犬一郎身边,对着二孬喊了一声:“板凳!”“来了来了!”二孬飞快地搬来一张板凳。刘仙堂恭身做一个下坐的动作,说:“太君,您请坐!”五犬腰疼着,坐不下来。刘仙堂和陈翻译小心翼翼地帮着五犬一郎往下蹲。鬼子终于坐到了板凳上。刘仙堂仔细地摸着五犬的背。五犬皱起眉头:“你的……”“啊啊太君,您老忍着点儿!”刘仙堂孙子一样。刘仙堂示意翻译帮忙。翻译站在五犬对面,双手扶牢五犬双肩。哆哆嗦嗦的刘仙堂猛地用力一推:他想给他复位。“哎哟哎哟!”五犬痛叫一声,倒了下去。众鬼子抢上前来扶住五犬。“刘仙堂,刘仙堂的,良心的坏……”五犬痛得吸溜着嘴,大骂。“抓起来!”翻译官用日语大喊一声!“哈依!”几个鬼子不由分说把刘仙堂按倒在地。“太、太君,我还没有看完呢……”刘仙堂叫着。押着他的鬼子用枪托砸他。
“请、快请郭先生!”五犬一郎被刘仙堂这么一折腾,一脸的痛苦不堪。“哈依!”翻译应一声,快步来到郭一山面前,用命令的口气说,“郭先生,你给太君看!”郭一山看一眼翻译,语调平静:“你告诉五犬,一山不看!”翻译一听,马上换了口气:“郭先生,我知道您在生太君的气,可是刘仙堂的诬陷,太君并没有相信呢!”郭一山冷笑一声,说:“一山救的是病人,一山不敢救豺狼!”翻译笑了笑:“豺狼?要是你救的豺狼,咬死了另一只对你威胁更大的豺狼,你干不干呢?”一山坚决地摇了摇头。
“太君,太君!我的治疗还没有结束呢,我能给太君看好!”刘仙堂不怕挨打,仍然大声叫唤。
翻译官一摆头:“听见没有?你要明白郭一山,刘仙堂看病不是为了太君,而是为了杀你。而你要是给太君看好了病呢?太君就把他杀了。既保全了自己又杀掉了仇人,你何乐而不为?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好好想想吧郭一山,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天天都有!”郭一山仰头看天,仍是平静的语调:“一山不救豺狼!”翻译翻了脸:“真的不救?”“真的不救!”翻译官用食指对着郭先生一捣:“哼哼,郭一山,你要付出代价的!”
有鬼子抬来了担架。翻译连忙跑过去,和众鬼子一起,把五犬一郎抬上担架。五犬既不能坐,也不能躺,他侧歪在担架上,痛苦万状。翻译和五犬用日语小声嘀咕了一阵。“哼哼,我要用他们的鲜血抚慰我身上的病痛!统统枪毙。”五犬一郎咬牙切齿,“机枪准备!”“哈依!”翻译站起身,大声喊:“机枪准备——”情势骤然紧张。周围鬼子的枪口全都对准群众,一片拉动枪栓的声音。狼狗狂叫着。有孩子吓哭了,直往妈妈衣襟下钻。
翻译再次走到郭一山身边:“怎么样郭先生?你可以不看,你的老婆孩子,你的乡邻乡亲,可都在这儿呢!你要真的惹恼了太君,他们可都得跟着你通通完蛋!”郭一山说:“陈翻译,看病的是我,不看病的也是我,与他们何干?”翻译说:“混蛋!与他们何干?他们是你的亲人!想想吧,你那个‘豺狼’的死理儿和这几百口子鲜活的生命哪个重要?”“先生!”云鹤鸣哭了,她晃着丈夫的胳膊,说,“看吧,看!”郭一山深吸一口长气,痛苦地说:“好吧!”“这就对了嘛!”翻译笑了,他伸手拉住郭一山,大步向五犬走去。
五犬一郎看郭一山答应看病,对着郭先生咧了咧嘴。郭先生不理他,俯下身来,对着担架上的五犬一郎猛地一推。“哎哟!”五犬一声痛叫。众鬼子上前按倒了郭一山。
“先生!”云鹤鸣一声高喊,猛跑上前。“郭先生!”“郭先生!”众百姓齐唤。
“哈哈哈哈,”刘仙堂禁不住笑了,说,“太君,郭一山是要杀你!”
五犬一郎一翻身跳下担架,对着地上的郭一山伸出拇指高叫:“郭先生,你的神医!哈哈哈哈……神医的干活!”众鬼子松开郭一山,也跟着狂笑起来。
郭一山忽然泪流满面。云鹤鸣上前搀住先生。
游击队战士进入平乐镇的时候,刘仙堂正给五犬治伤。等郭一山给鬼子看完,游击队刚刚进入隐蔽地点。带队的是白挺松,他看老百姓和鬼子混在一起,一时没敢动作。
五犬一郎站直了,得意地甩了两下胳膊,走到一山夫妇面前,说:“郭先生,刘仙堂的诬陷,我的明白!死了死了的!”陈翻译连忙翻译。五犬一郎一阵狞笑,又说:“慈禧太后的白玉药王,我的看看!”
云鹤鸣明白了五犬的意思,对翻译说:“陈翻译,您告诉五犬先生,白玉药王六年前就丢了!是一个贼人趁逃反的时候偷走的,全村人都知道!”
“哼哼!”五犬听完笑了,“你的放心,白玉药王的,我会,找回来!”他忽然一挥手,用日语大声命令着:“刘仙堂的,带走!”有人上前押住刘仙堂。刘一个劲地喊冤枉。
五犬又喊:“郭先生,还有他的徒弟,带走!”有鬼子上前抓住郭一山和郭济财。
五犬手指着彩凤鸣、财媳妇和一川媳妇,还有另外两个年轻媳妇,用日语高喊:“她,她,她,她们,统统地带走!哼哼,白玉药王的,交换!”
鬼子们如狼似虎,上前抢人。大门前一片哭喊声。几个鬼子把郭一山和郭济财推推搡搡押走了。“先生,先生!”云鹤鸣喊着,一个鬼子兵朝着云鹤鸣砸了一枪托,云鹤鸣倒在地上。
鬼子抢一川妻郭戚氏,郭济聪去拉,被鬼子打倒在地。一方妻和郭济有拉住财媳妇的手,鬼子兵一脚将一方妻踹倒在地。端刺刀要刺郭济有。有一跳躲开。一方妻坐在地上哭起来:“财,媳妇呀!”
彩凤鸣抱着孩子,两个鬼子来夺。庆吓哭了。花娘看见,高喊着也来抢。鬼子兵把孩子夺到手,猛地往上扔去。“庆——”花娘喊着。孩子重重地摔在地上。“庆——”人们喊着齐扑上去。
叭!叭!枪声响了,扔庆的鬼子应声倒地。“刘仙堂,快卧倒!”随着游击队战士的喊声,枪声大作。又有鬼子倒在地上。鬼子大乱。
云鹤鸣爬起来就去抢救孩子。她使劲掐着庆的人中穴。一动不动的孩子,瞳孔渐渐散了。“庆!庆——回来吧!快喊!”花娘在叫魂,她呼唤孩子们一起叫,“庆,庆——回来吧!”“庆,庆——回来吧!”馨也喊。“弟弟,回来吃糖!——弟弟,姐姐有糖!”草喊着,从兜里真的摸出一块糖来举着,像是弟弟就在不远处。云鹤鸣无力地站起来。“咋样,鹤鸣?”花娘带了哭腔。云鹤鸣摇摇头,泪如泉涌。“弟弟——”草放声大哭起来。宝和馨也都哭了。
郭二先生的身边,聪跪着哭。一川傻傻地站着,不时地做出傻笑的样子,却发不出声音。
一方倒在地上,妻和有上去架他。
满场里都是哭声。
白挺松带着游击队员跑过来。众人看见,齐站起来。“白大哥!”郭济远迎上去,“给我一杆枪吧,给我一杆枪,我要打鬼子!”喊着,大哭。“济远,济远兄弟!”白挺松扶住他的肩头。郭济有也跑过来,高喊着:“给我们枪吧,我们要杀鬼子!”“我们要杀鬼子!”不少年轻人喊着。
大门前,这边是不到一岁的庆的小小的尸体,头上流着血。那边是年近八十的郭二先生的尸体,紧攥着衰老的拳头。路对面的门边,躺着年迈的聋奶奶,一头灰白的头发随风拂动。白挺松忽然流出泪来,喊一声:“娘,我们来晚了!乡亲们,我们来晚了!”
“孩子,快去救你爹他们!”云鹤鸣往外一指,“要狠狠地打鬼子和那些汉奸!”“娘您放心!”白挺松一扭脸,对战士们大喊,“弟兄们,我们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为乡亲们报仇!”战士们喊。“快,追!”白挺松一挥手。“白大哥,白大哥我也要去!”郭济远追上去。郭济有和郭济聪也跟着追上去。“回去,你们还是孩子!不要耽误时间了,你们快快回去!”白挺松坚决地阻住他们。“白大哥!白大哥……”三个孩子撵着喊。“回去吧!”白挺松大声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