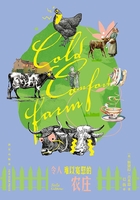巧巧想的是在花奶奶脖子里夹草秸,当她爬到背上时才发现,花奶奶的脖子里根本没有皱纹。巧巧立时没了兴趣,正想下来,忽然想起两人的约定,只好耐着工夫懒在花奶奶背上。
“老先生啊,一山娶亲,半路又回来了你知道吗?”这才是花娘出来找他们的真正原因,巧巧一闹,到这时候才得空说,“哪有半路回来的理,不兴!”
“半路回来?为啥?”郭老先生皱起眉头看着老婆。花奶奶正要回答,槐树下的赖孩儿大声地喊起来:“老先生,老先生你说外国人的眼睛是哪一种蓝?洋蓝还是青花蓝?”他们正争论马利奇眼珠的颜色,货郎担子姬麻子说是青花蓝,油漆店学徒赖孩儿坚持说是洋蓝。洋蓝是大清时从外国传来的颜色,蓝得薄亮。郭老先生拈了拈胡子,说:“年轻时是洋蓝,老了就是青花蓝。”“大伯,嘿嘿蓝天!”一川过来了,手使劲往上指。“嗳,一川说得对。”郭老先生抬头看一眼,“是天蓝!天蓝得干净,也蓝得丰富,哪一种外国人的蓝眼都可以比得……”
“哎呀表哥,你可回来了,疼死我了,你快给我看看吧!”一身孝服的刘仙堂刚走进门楼,就听见他表弟二孬的叫唤。“咋啦二孬?”刘仙堂铁青着脸,放下铁锨走过来,猛地一拉二孬的棉裤。“哎哟,哎哟表哥慢点儿!”二孬神经质地叫着,“你是不是跟谁生气了?哎哟……”刘仙堂不理,还是又使劲往上拉了拉:二孬的右小腿肿得很夸张,亮亮的,像吹饱气的猪尿泡又抹了一层油。粗黑的汗毛根根竖起,红红的汗毛孔随时准备着往外滋血。
“骨头折了。”刘仙堂直起身,边脱孝衣边问,“咋弄的二孬,能伤成这样?”二孬的三角眼使劲一挤:“哎哟表哥,昨天夜里,尤瞎子,这个老土匪!他让我们三个去凿龙门石窟古阳洞里的魏灵藏。魏灵藏那是啥样的石头,那是全龙门山最难凿的石头!一凿一片火光,一凿一片火光。我们凿了半夜……”“一凿一片火光人家会不知道?”刘仙堂说。“龙门山那么大,别说石头冒点儿火,就是放火烧房也不会有人知道。是有人使坏!”二孬又咧了一下嘴,“刚凿了两个佛头,正要往外运。忽然打起枪来了,枪子把洞口的石头打得一片明。叭,一片火光,叭一片火光!我们丢了佛头,爬起来就跑。天黑看不清路,我跑错道,钻人家窝里去了。我一看坏菜,往山下滚吧……捡了条命,你表弟我是捡了一条命啊表哥!”“几块烂石头还值当动枪?”“哎,表哥,你是不知道,一个佛头听说就值一千多块大洋,专有外国人收购。”“一千多块大洋?一块石头就值恁多?那你看见是谁抢的?”刘仙堂有了热情。“我哪还敢看!枪子它不识好赖人!哎哟,我大难不死……”
一匹紫红马停在门外,高扬头打着响鼻,身穿藏青色长衫的青年人从马上跳下来,拴马在门口树上,径直往屋里走来:“二孬,又瞎吹哩不是,你受点儿伤真是不屈……嘿嘿刘先生好啊?”年轻人取下头上土黄色的宽边礼帽。“哎呀富宾啊,听说你现在是二拇指了,恭喜高升啊!”刘仙堂热情地招呼着,忙把椅子搬过来,扭头高喊一声,“上茶!”刘妻一手提了大青花白瓷茶壶,另一只手端几个牙白色茶碗走过来。“娘,我去玩儿了!”五岁的女儿花蹦跳着往外跑。“这是你嫂子!”刘仙堂笑着。“啊啊,嫂子好漂亮啊!”赵富宾开着玩笑。
“头儿,我可是大拇指派的差,您可得替俺说说情,我这腿要是万一残废了……”二孬做出苦相,看着赵富宾。“放心吧二孬!你要相信你表哥的医术!”赵富宾忽然压低声音,“夜里你跑时,是不是听见有人高喊,‘二孬,把佛头留下’?”二孬歪头想一会儿说:“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好像有人喊,‘二孬——’”“好,这我就知道是谁抢咱的佛头了!”赵富宾一拍二孬的肩。“哎哟!”二孬夸张地叫一声疼,又问,“你知道是谁抢咱的佛头了?谁呀头儿?我给他没完!他得赔老子的腿!”赵富宾说:“还能有谁?你想想,咱的买主是美国人普爱伦,乌麻子的买主是意大利人马利奇……”“唉,又跟他妈外国人牵连上了!”二孬泄气了,“头儿,这外国人咋恁喜欢佛头哩?他们弄回去当爷供哩?”“嘿嘿,物以稀为贵嘛!他们弄回去好卖钱!”“外国不是啥都有吗?咋稀罕咱这儿的佛头呢?嗨,咱反正有的是,只要给钱咱就给他弄。守着龙门哩!只是我这腿……”“嗳,”赵富宾站起来,“刘先生,拜托了!回头一总结账!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
郭一山看了个外国人,金黄的胡子洋蓝的眼,会说不打弯的中国话。平乐镇像烧开了的一锅胡辣汤,白菜粉条肉沫沫,一时全沸沸扬扬。刘仙堂从坟里回来,没进村就听说了。他当时只是恨,恼恨马利奇为什么不到他永春堂!忌恨郭一山又他娘出了风头!愤恨全村人兴奋得像吃多了春药!一剂“恨药”在心里煎着,什么味的恨都配全了。所以他拉表弟的棉裤时不觉地就下重了手。赵富宾和表弟的一番对话,闪电般击穿了煎恨的药锅,一个绝好的主意忽然就站在了他的面前:哼哼,够他郭家喝一壶了!他看天色尚早,就急忙进屋去换衣裳。
“花他爹,你要干啥去?”老婆刘王氏看他长袍马褂地装扮着,嘴里还铿铿锵锵地敲着锣鼓,像拾了金的叫花子一样高兴,陡然就生出不安来。刘仙堂不理她,穿戴完毕,又对着镜子梳了梳胡子。“你究竟要去干啥?”妻子再问。“干啥?”刘仙堂盯着老婆的脸,“哈哈哈哈,我要告诉老土匪尤瞎子,抢劫魏灵藏佛头的意大利人马利奇,他是郭一山救下来的!”老婆说:“郭一山是先生,救一个病人有啥不该……”“有啥不该?马利奇抢了尤瞎子的生意,郭一山帮助了马利奇。那我问你,他郭一山算不算也抢了尤瞎子的生意?”“他爹,先生看病,他和两家的生意有啥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刘仙堂瞪起眼睛。刘王氏忙陪笑脸:“就算有关系,尤瞎子他也不敢惹人家外国人!”刘仙堂恼了:“尤瞎子是不敢惹外国人,可是他敢惹郭一山!哼!今天犯到我手下了,我要不叫他郭家家破人亡,我、我不姓刘!”说着就往外走。刘王氏伸手拉住丈夫。“放开!”妻子不放。“你放不放?”刘仙堂铁青了脸。
刘王氏的手抓得更紧:“她爹,千年搁社万年做邻,他看他的病人咱坐咱的堂!人家郭家没有对不起过我们啊!”说着一使劲,刘仙堂被她拉进屋里。“没有对不起过我们?我问你,咱爹咋死的?”刘仙堂指着门上的丧联理直气壮地喊,“咱爹咋死的!陕西姓胡的那个孬种来咱平乐镇看病,在咱家住了两天了,一听咱不姓郭姓刘,站起来就走了!老爹气不过,追上去给他要钱,扑通一头栽到了地上,这难道你都忘了……”“那不是姓胡的没钱嘛!咱看病要钱他郭家看病不要钱……”“你给我闭嘴!”刘仙堂攥紧拳头对着老婆晃了晃又放下去,“我他娘最不信这一套!他为啥不要钱?他是沽名钓誉!只要有他郭家这名利之徒在,我看咱刘家、咱刘家的子子孙孙就别想过好!”
刘王氏用哀求的眼神看着他:“他爹,郭家传了五代了,咱刘家不是才两辈吗?听咱爹说,咱过去是卖药的,并不看病……”“臭嘴!你也想说老爹的坏话吗?不错,自古是看病不卖药,卖药不看病。可光卖药能发家致富得大利吗?又卖药,又看病。这是咱爹的创造你知道不知道?你只要还是刘家的媳妇,你就得记住老爹临死时说的话:郭家不灭,刘家不兴!”刘仙堂说过,站起来猛地蹿到门外。“她爹——”刘王氏大喊着上前又拉。刘仙堂冷笑一声,阴鸷地看着老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刘仙堂饶不了他!”猛一把将妻子推倒在地,转身跑出屋门。“刘仙堂——”刘王氏哭了,她爬起来追到门外,指着丈夫的背影喊,“那怪郭家吗?兴你刘家聘,就不兴人家郭家聘?那是月香她爹有眼,没把闺女嫁给你个王八蛋……”“啥?你说啥?”刘仙堂忽然又拐了回来,“月香她爹有屁眼!她嫁郭一山是二婚,我那时候刚满十八,还是个童男呢!要叫月香自己挑,会挑他那个二婚头!月香就是他郭一山害死的,我饶不了他姓郭的!”说着,恶狠狠瞪妻一眼,很正义地转身出了大门。
“刘仙堂,你坏良心……”刘王氏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刘王氏小名叫桃儿,是小财主王发财的二闺女,十五岁时给县城首饰店姚老板的儿子订了婚,后来才知道姚家的儿子是个傻子,王桃儿大哭一场,三天三夜水米不打牙,王发财害怕了,加倍偿还了姚家的订金,算是退掉了这门亲事。之后三四年,再无媒人敢登王家的门。俗言“十七八的大闺女”,十七十八,已经算大,此时的王桃儿已过十九,真成了王发财的一块心病。那年端阳刘仙堂赶会,正赶上月香帮爹往街上抬油篓,刘仙堂一眼就看上了月香。初生恋情的小伙子压抑了几天才扭扭捏捏地给爹言明,谁知道刘家的媒人来到冯家时正遇上郭家的媒人在喝茶。一家有女百家求。冯家倒是很热情,只是结果令刘家难堪和气愤:冯家把彩球抛给死了老婆的郭一山!难堪,气愤,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刘仙堂从此生病,蔫蔫地不思茶饭。恰在此时,王桃儿的姑父来到了刘家。一方急着要出嫁,一方急着要冲喜,很快,二十岁的王桃儿就成了十九岁的刘仙堂的老婆。
新婚之夜,刘仙堂抓住王桃儿的胳膊,压低了声音问:“你是月香吗?”王桃儿不明白,就说:“我咋是月香?我是桃儿。”刘仙堂一下子把王桃儿抵在墙上,再次发问:“你是月香吗?”王桃儿不敢回答了。“说,你是月香!”刘仙堂命令她。王桃儿不语。刘仙堂猛在她大腿上掐了一把。“哎哟——”王桃儿小声叫唤。“说,你就是月香!”“我、我是桃儿,王桃儿……”刘仙堂又掐她一把。“你是月香吗?说,你是月香!”刘仙堂两手掐住桃儿的脖子。桃儿真的害怕了,哭着说:“嗯,嗯,我、我、我是月香……”“真是月香?”刘仙堂有了喜悦。“真、真是月、月香……”王桃儿抹一把眼泪。刘仙堂一下子温柔起来,他把她抱在怀里,又是摸,又是亲,他结实地骑着王桃儿,自己却鼻涕眼泪不住地流,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直到尽兴了倒头酣睡。这以后,她就有了两个身份,白天她是桃儿,是刘仙堂的老婆王桃儿。夜里就成了月香,成了刘仙堂心中的情人。王桃儿有伤心,王桃儿也有安慰,丈夫倒真是在她的忍辱的配合下,渐渐地强壮了身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火棍抱着走。
”再怎么着也比嫁个傻子强吧!只要丈夫能好了病,再怎么着也是值得的。戏台上的人不是天天在扮演吗?我就扮演扮演月香那又怎么样呢?退一步海阔天空,王桃儿就退一步。在傻子面前王桃儿宁死不退。在刘仙堂面前她必须勇敢退却。不过,她还是伤心。一提起月香她就伤心。她曾想捏一个小面人,写上月香的名字,天天往上浇开水。也曾想到庙里降香,求万能的神把这个女人收走。可是当她见到月香,看到月香的单纯和美好时,一下子就感到了内心的羞愧。这只是你丈夫的单相思,跟人家月香有什么相干?说实话,当月香喊了两天,死于难产后,她流了几天伤心的泪水。看到眉眼都仿月香的巧巧,她偷偷地给孩子喂过多次奶。王桃儿有时候很恍惚,人家一说月香如何,她就感觉说的是她。她毕竟扮演过月香,甚至她有一半的生命过程打的是月香的招牌。她扮演月香当然是被迫的,是不情愿的,可随着丈夫身体的渐渐好转,随着女儿的顺利出生,更随着自己身心的渐渐受用,她几乎可以说开始喜欢月香了。她开始喜欢月香了可月香却死了!她为此专门到庙里烧香祷告。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磕头,她知道她想不明白神自会想明白的。
她最不明白的是丈夫对郭家的恨,郭家并没有招他惹他,郭家人过得很低调,郭一山一身儒雅,见了谁都点头致意,没一点儿名医的架子。有一次她去给巧巧喂奶,郭一山非让她带回来两封果子。要硬说招他惹他刘家了,那就是郭家开了药方让病人来他刘家拿药了,可那不是刘家心想的事情吗?刘家的药铺有人家郭家一半的功劳啊!“杀父之仇!”你的父亲是自己栽倒在地上,被鸡脚獾子( 俗信的一种小妖 )拿走了性命的。再说,惹老人家生气的那是陕西的客,跟人家郭家……唉,真是越说越不是理!“夺妻之恨!”人家夺你的妻了吗?要说有恨,顶多你恨恨冯家。可冯家的闺女冯家自己作主,难道非得听二家旁人的?月香难产,郭家抢救了两天两夜,郭老先生事后大病一场,人家的媳妇人家不疼?要说恨,倒是郭家该恨恨你!你折腾人家媳妇的名字整整三年,你得了人家的利还要再害人家……
“娘,娘,我饥了!”女儿从外边跑回来,站在娘身边。桃儿收住泪,忙扯着女儿回屋拿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