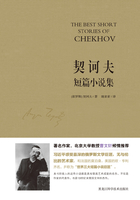味辛热微毒治气血凝滞跌打损伤
—— 《 日华子本草 》
院里的杏花开过三次,恰到含苞待放的第四次悄然来临的时候,郭家迎来了大喜的日子。首先是孩子的百日庆祝,要宴客,要取名,要戴锁子。其次是郭老先生的三周年祭日。这小子会来,他的百日,恰和爷爷的三年祭日是同一天。还有,两天前,郭一山备足银两,去金老板的典当行里请回了白玉药王。双喜临门又加上一祭,百年不遇,云鹤鸣给丈夫商量,决定风风光光的操办一场。爹死的时候,正值匪患初息,未能尽意,这次,一定要让爹及九泉之下的先人们放心。一家人齐聚客房,一山请花娘给孩子起名。花娘笑了,说:“我会起个啥名啊!你是爹哩,又识字,你给孩子起吧!”一山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好像是想的样子。其实他早就想了一百遍,几十个名字在心里打了几百架了,三十四岁得子,会不想吗?不过,当他决定说出儿子名字的时候,还是在心里又过了一遍。他说:“就叫郭济远吧!济,就是济世救人的意思,咱是医生,这是本分。远呢,就是范围广大。
济远,合起来,就是希望他将来的医道、医术能超过祖上,有更大更远的影响。”“济远,济远……”花娘像吃东西品味一样地重复了几遍,“嗯,好名字!尤其这个‘远’好,男孩子,就得远!小名呢?”“您给起吧?”云鹤鸣看着花娘。“我起?我想给俺孙子叫个宝。宝贝的宝!郭家长门头一个孙子,还不宝贝吗?”花娘说着,禁不住喊了一声,“宝!”怀中的孩子忽然笑了。“瞧,他笑了!”巧巧大叫着,“他喜欢他的名字。宝,宝,郭济远,宝,宝,郭济远!”巧巧大叫着,忽然扭头问,“爹,我叫啥名字?”花奶奶说:“你叫巧巧。”“大名?”巧巧不依。云鹤鸣说:“你叫郭巧巧。”花娘不满了:“小闺女子家要啥大名呀,就是巧巧。”“为啥弟弟有两个名字我只有一个呀?”巧巧又问。云鹤鸣说:“你是大名连着小名。”“要是你爹还活着,今天见了他孙子,不知道会高兴成啥样呢?”花娘忽然有些感伤。“是呀,”云鹤鸣接上,“爹死时才六十六,到今年也就是六十九岁,年龄也不算大呀!”砖头走进来报告:“刘黑子的响器班已经来到,现在上坟吗?”郭一山站起来,说:“上坟!”
这次人多,刘黑子把全部人马都带来了。他手捧着一杆大笛走在前边,左边,三个男的,分别是大狗二狗三狗,右边,三个女的,分别是大儿媳和两个女儿,十七岁的大桃红和十五岁的小桃红。因为是三年祭日,没有了丧事时的悲怆和凄凉,吹的全是喜庆的调子,丹凤朝阳,喜鹊登枝,一股脑儿全上来了。调子欢快,女客漂亮,两千多人的平乐镇一下子兴奋起来。男女老少全跟着看,尤其是那些十七八岁的风流少年,追着喊着指点着大、小桃红。刘黑子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知道,今天和他唱对台的,是当地有名的梆子剧团洛记班。他要不拉出全部队伍,说不定要丢人砸家伙的。紧随唢呐之后,是绑了双杠的八仙桌子,两人前后抬着,桌上端放着披红挂彩的白玉药王爷的雕像。再后边,是拴了双杠的一把圈椅,上边放着亡人的牌位。郭一山就走在这把椅子的后边。
到了墓地,亡人归位。药王爷落驾。点燃鞭炮,焚化纸钱,唢呐高奏,锣钹齐鸣,郭一山扑通跪倒,大声地祷告:“爹,一山不孝,叫您牵挂,三年了,孩儿一刻不敢释怀,白玉药王,今天终于又迎回咱家了!爹,您请上座吧,儿请您回家看戏了!”一山深深地磕下头去,抬起来已是泪流满面。
回到家中,郭一山把药王爷和爹的牌位摆放端正。退回来又磕了个头,刚爬起来,时砖头从外边跑进来,大声说:“先生,马先生来了!”砖头已经十八,完全是个大小伙子了。“马先生?哪马先生?”一山一时没想起来。砖头说:“马利奇呀!”“马利奇?在哪儿?”一山话音未落,马利奇和一个四十来岁的清瘦和尚走进院来:“郭先生一向可好?”马利奇胖一些,蓝色的眼睛仍然闪烁着孩子般的好奇和热情。“还好还好!”郭先生应着,示意二人进屋。
马利奇不进,三年没来,他转着头看了一圈儿,又说:“郭先生,我是来向您贺喜的!祝贺您喜得贵子!”马利奇向郭一山拱拱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郭先生今年是三十四岁,对吗?”“马先生好记性!”郭一山笑着说。“不是我记性好,是因为先生和我同岁,按中国的说法,我们都属羊,午马未羊。哈哈哈哈。”马利奇说过,掏出一对银手镯和一把银锁,“我问了银匠师傅,他说,这把锁戴在孩子脖里,就把孩子锁住了。这一对银手镯呢,也是拴的意思。哈哈,你们中国人很有意思,让孩子披枷戴锁,扮成罪人,就能长大成人,长命百岁了!我把这些送令郎,祝福他身体健康,长命富贵!”马利奇把手里的镯子晃出一片的声音来,逗得周围的人全笑了。“这位是我的朋友,白马寺的弘元法师。”马利奇对郭一山介绍。“久仰久仰!”一山忙说。“阿弥陀佛!”弘元法师竖起手掌唱了一声。“马先生请,法师请!”一山再让两人。
到了客房,一山才知道弘元法师是来看手的。刚才有袈裟盖着,现在一伸出来,才发现食指和中指肿得厉害。郭先生托住法师的手,轻轻摸了一下,说:“砸得不轻,食指骨头碎了,中指劈了!”法师“噢”了一声。“郭先生,您怎么知道是砸的而不是压的?”马利奇问。郭先生笑一笑,说:“砸的皮破,骨头易碎。压的皮不破,骨头易劈。”弘元法师皱起眉头。“不过不要紧,贴服膏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郭先生说着,拿过法师的食指轻轻地捻动,随后拿来药碗涂了药,用生布包了起来。“我买了一个鼎,法师说是周天子祭祀用的礼器,上边有字,我让法师认认是什么字,不小心砸了手。”马利奇说着看法师一眼,“不是压的吧,法师,鼎不重嘛!”“法师研修佛理,也研修甲骨学?”郭一山露出佩服的神色。“哪里?甲骨是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殷商文字,周鼎上的文字又晚了一代,学界称它为金文。我没有研究,只是喜欢而已。”法师说。
砖头快步走到门口,伸头往里张了一眼。一山见他慌张,知有事情,忙走出来:“有事?”砖头把郭一山往外拉了拉,说:“俺爷又来了?”“啥?”郭一山变了脸色,“在哪儿?”砖头往外指了指。一山皱起眉头:“快喊鹤鸣。”砖头应着转身就跑。云鹤鸣正在屋中逗孩子,砖头跑进来喊一声:“云先生,先生叫你。”“叫我?”云鹤鸣把孩子交给花娘,走出屋子问,“有事?”砖头嗯一声,扭头就走。云鹤鸣跟到前院,见一山满脸阴云站在院里,就问:“啥事?”一山扭头看一眼外边,说:“时老头儿又来了!”“他来干啥?”云鹤鸣警惕起来,“前年打官司,虽说他吓跑了,咱不是还转个圈周济他了吗?咋着?还想闹?”
时老头儿此时已经来到门前。时老头儿这次不是走来的,他是由两个壮汉用车子推来的。云鹤鸣走到门外时,几个年轻人正奚落他:“哎哟,这不是时老先生吗?保证又去县里告郭家了!看,又挨县太爷打了吧?”“是吗?”旁边有人也跑过来,“这县太爷也够黑的,咋能把人打成这样?有理没理,也不能往死里打呀!”“哈哈哈哈。”人们放肆地笑着。到了跟前才知道,时老头儿受伤了。送他来的两个男人,既无人端水,也无人让烟,很尴尬地站着擦汗。云鹤鸣对砖头说:“快去,请先生给老人家治病!”“那——”砖头似有话说。云鹤鸣小声说:“只兴他不仁,不兴咱不义。去吧!”“啊。”砖头应着转身就走。“哎!”云鹤鸣喊,砖头又站下来,鹤鸣吩咐,“不要给你姑说。”“中中。”砖头点了头,扭脸飞奔而去。云鹤鸣看着门外的两个推车人一直擦汗,就说:“两位兄弟,快进屋里坐吧,这么远的路!中午在这儿吃饭!”“哎哎不了,家里忙着呢,我们还得回去!”年长一点儿的男人很不好意思,“是你们镇上的刘先生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听是郭家的亲戚,就连忙把人送来了。我们也不知道还这么复杂……”扭了脸看着年轻的同伙小声又说,“你看这是啥事!”
郭一山快步来到车前,弯下腰仔细地看着老头儿:时老头儿双目紧闭,仍然哆嗦着。郭一山拉开老头儿的脏裤子一看:腿肿得像冬瓜,明晃晃的。有一处皮肤黑烂,淌着脓水。“把木床抬来!”一山大声说。众人急忙把门楼下的木床抬到车子边。“把他抬床上,慢点儿啊!”郭先生说着,弯下腰和砖头等人小心翼翼地把时老头儿挪到床上。“太脏了,要洗!”一山说,“端盆凉开水!”“中。”砖头应着就跑。一山又喊:“再拿碗白酒!”“中中。”砖头扭脸又应。巧巧也过来了,挤到前边看。
送时老头儿的两个汉子看车子空了,推起来就要回去。“慢!”云鹤鸣从兜里掏出几枚铜板,递往年长的男人,说:“对不住了,既然一定要回去,那就路上买碗饭吧!”“哪能要钱!净给你们添麻烦!”年长的汉子推辞着。云鹤鸣把钱硬塞给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