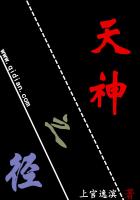不过他又劝自己,打败郭家,打败一个有着二百年行医史的家族,几千斤小麦算什么?值!郭一山年轻少壮,值二百块大洋,五千斤小麦;郭老头子年老体衰,就只能是半价!想到这儿,他禁不住哼了一声,不是我说他值一百,是郭老头子自认的一百。要不,刘某人花了一百块大洋他为啥就自己死了呢?你以为你能值多少?就一百!他忽然想起王桃儿的话,狼群里跑只羊,横竖都是羊吃亏。没杀死郭一山,按讲他花不了一百块大洋,可胡子、狗子、小个子都不愿意,因为他们被大拇指各罚了二十,挨打丢人不说了,这二十块总得你出吧?刘仙堂也就是应得慢了点儿,胡子立马翻脸了,说刘先生不出也行,郭一山啥样你啥样就行了!刘仙堂知道,他是在威胁他:郭一山被打得走不成路啊……他于是就出了一百。“这也值!”刘仙堂说出了声,“总给他郭家一个大打击!哼!”
刘仙堂也害怕。刘仙堂害怕郭家知道了饶不了他。郭家在平乐这么多族人,就是不告给政府,挤兑也挤兑死他们了!可是等了十来天未见动静。他就想,郭家还是不知道。
王桃儿的叔伯哥王剪儿在崖下开荒,一批子土砸下来,折了脚踝,兄弟几个抬着王剪儿来到了永春堂。说实话,他们并不想来这儿,前年王剪儿也受过伤,往地里送粪呢,被惊牛踩了一蹄子,脚趾头断了两个,就是在郭家治好的。眼下的郭家不是正办丧事吗?刘仙堂知道王剪儿,也知道王剪儿到郭家看病。“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骂王剪儿是小人,为省俩钱六亲都不认了。刘仙堂看了病,说:“剪儿哥,脚踝碎了!”王剪儿头上的汗淌得更多。“十伤九病,您得吃点儿药啊!”“兄弟,您就看着办吧!”“放心,我给剪儿哥您下最好的药!”“谢谢您了兄弟!”王剪儿很感激。
刘仙堂拿着小秤进里间称药,王桃儿快步跟进来,一脸讨好地说:“他爹呀,虽说是叔伯兄弟,也亲着哩,就别要钱了吧?”“不要钱,你吃风屙沫啊?亲戚是亲戚,咱不给他多要就是了!”刘仙堂停在桌边,转着头瞅药。一包一包的草药码在桌上。他一扭脸,对妻说,“把那包人参拿过来。嗳嗳?那边的!”王桃儿有些困惑:“这人参?你不是说是红萝卜干吗?”刘仙堂恼了,恶狠狠地说:“你懂个狗屁!快,就拿那一包!”王桃儿犹豫着。刘仙堂走上前,把王桃儿搡开,拿过来便称。王桃儿还想说啥,见丈夫不理,就气哼哼地站着,看他作恶。
刘仙堂称了药,满脸是笑地走到外间,说:“剪儿哥,这是五剂药,吃下去就见大轻!”“谢谢妹夫了。”王剪儿说。“谢啥呀!我说不收钱了!恁妹说,小本生意……哎,五百文吧,要是外边的人得一千呢……”刘仙堂一脸正经。“你……”王桃儿气得用手指他。“给剪儿哥续杯热茶!”刘仙堂堵住妻子的嘴。到了夜里,刘仙堂骑在王桃儿肚子上,大声地威胁她:“你以后少给我打别!我说要钱,就得要钱!龟孙儿土匪糟蹋的钱从哪儿出?你肚皮上能种出钱吗?你的×里出得了钱吗?”王桃儿大气不敢出,只得暗暗流泪。月香死后,他就新添了毛病,一不高兴,就脱光了身子骑她的光身子,两手在她的脖子上比比划划。她感觉,总有一天这个疯子发了疯,会把她活活掐死在床上。
郭家的生活虽然走上了正常,郭一山虽然坐在了大门楼下,但郭家的人都知道,有一道难题一直未解,那就是怎么样对付刘仙堂。在平乐镇郭家是大姓,从明初移民到今天的民国,绵绵廿一代,济济一千多众,他刘家才几个人!三门的一方找到一山说,大哥,趁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把火烧了他龟孙!新媳妇一听就摇头。新媳妇说,谁知道他和尤瞎子的关系多深呢!再说,害人如害己,三条人命可不是小事!让人得便宜。先生,咱就让他一回吧!郭一山想了想,说,知道了啥病就等于好了一半。咱装做不知道,防着他就是了!
郭一山正在门下看病,来了一群跑反的,说是铁门镇的。冯玉祥的军队进攻,吴佩孚的军队防守,整打了两天,街上躺的净是死人,镇里的人全跑光了。铁门镇在洛阳西,平乐镇在洛阳东,相距不上五十里。“铁门镇不是张钫将军的家吗?千唐志斋还在不在?”一个老人问。“只讲活命了,谁还管啥千唐志斋呀!”跑反的男人喝了碗凉水就走了。跑不跑?平乐镇上一时风声甚紧。一方晚上又来找一山,他说:“大哥,趁跑反这乱劲,找你认识的老陈他们给他做了算了!”郭一山皱着眉,不知道该接啥话。一方说:“大哥,你再想想,要是行,给我言一声,我去给老陈他们商量。他能花钱买咱的命,咱也能花钱买他的命。看他娘谁厉害!欺负咱姓郭的没人是不!”一方一走,媳妇就说了他跟二叔来时想要秘方的事。一山没说什么,但他下定了决心,息事宁人,快传医脉。
冯玉祥兵不血刃占领洛阳,平乐镇又过起了安静的日子。新媳妇喜欢研墨,拿一方印章般大小的墨锭,在卧着水牛的端砚里细研,亮亮的墨锭越变越矮,砚里的清水就越变越黑,略带臭味的墨香也就越来越浓了。她喜欢墨香。墨锭也香,但它的香味细,薄,硬,是一根一根的,一缕一缕的。墨汁的香味厚,软,浓,是一片一片的,一团一团的。墨锭的香味在身外,淹不住你;墨汁的香味在身里,浸得你湿透。硬的变软,薄的变厚。靠的就是个研。一山看病要开方,以前都是自己研墨,荷香来了,荷香就替了他。荷香识字,也喜欢研墨。荷香研墨可以用“文静”形容,她研时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一星儿墨点儿都不溅。她喜欢闻墨,能连闻三次,就是研好了。鼻子里有标准。到了月香,就得催她研。月香研墨可以用“生动”形容。她研时砚台老咂桌面,咚咚地响,好像砚台不是石头而是块木板儿。当然溅墨也就正常了。月香好笑,研着研着就笑了。
一山问她研墨有啥好笑。她说,研墨开始像是胳肢人,一偷一偷的;最后像是挠痒,一抓一抓的。说着就扭着身子快意地笑。一山兴起,上前抱住她就胳肢她,胳肢窝儿,膝盖儿,大腿跟儿……月香躲着,叫着,笑着,直到扑通一声躺倒在床上。要形容新媳妇的研墨,就得用“虔诚”二字了。云大妮的爷爷是个秀才,一辈子教书为业,“敬惜字纸”是他的终生教诲。学生研墨有三不准:一不准坐研养尊;二不准咬牙皱眉;三不准影姿不端。跟着哥哥到学堂,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她研墨!有一次她刚摸到墨锭,爷爷看见了,说,大妮儿,谁让你来的?玩儿去!她的泪水就出来了。云大妮又在研墨,她弯了腰站着,不咬牙,不皱眉,不拧腰,不斜背,两眼看着自己的手一环一环地在砚池里轻绕,像在极高处看一只找寻栖息处的天鹅。墨香的味道越来越浓了,她换过左手再研下去。一山过来,拿笔尖蘸了一下,说,行了吧!她说不行,什么时候,香里带点儿甜味的时候就可以了。
郭一山展开宣纸,在上边写了一个“雲”字。新媳妇笑了,说:“这个字我认识。”一山又写一个“大”字。“这个我也认识。”郭一山不动声色,又写“妮”字,问:“这个呢?”“这个我能猜出来,云、大、妮,对吗?”新媳妇很得意。“我再写几个字考考你!”郭一山说着又写。新媳妇说:“你别考了,我又不认识字!”“郭一山”,郭一山写出自己的名字。“嘻嘻嘻,”新媳妇笑了,说,“先生的大名嘛!这我要不认识,还配做郭家的媳妇嘛!”“你可以嘛!”一山高兴了。“可以啥呀,斗大的字不识一布袋。”新媳妇说。“你已经识两布袋了!”郭一山说。新媳妇受了表扬,大胆地扶住丈夫的肩膀:“我爹说,郭家是书香门第,家里的小鸡都能认两笸箩字,他就教我认了这两布袋!”郭一山说:“好,今天我再教你认两布袋,你愿意学吗?”新媳妇笑着接道:“有老师愿教,哪有学生不愿学的道理!”
“當歸( 当归 ) 生地 大黄……”郭一山写着。“这是药名吧?生地、大黄,不都是药名吗?”她指着“當歸”说,“这两个笔画多的字我不认识。”媳妇睁大明亮的眼睛看着丈夫。“你真聪明!”郭一山亲她一下。第二天晚上,一山要考她,问,昨天的六个字忘了没有?她说哪会忘,就六个。果然一画不丢。一山说,我再教你六个吧,只要你学会了,我每天都教你六个字。说着就写了:连翘 白芷 赤芍。
新媳妇说,你再写几味呗,让我多认几个。郭一山略一犹豫,立即又写了三味药:甘草 羌活 独活。“连翘、白芷、赤芍,甘草、羌活、独活。嘿嘿,还押韵呢!”新媳妇笑了。
郭一山下意识地往外看了看,郑重地说:“记住这九味药,也就记下了咱郭家祖传的第一个秘方‘接骨丹’了。”新媳妇瞪大眼睛:“哎,你咋把祖传秘方给我说了?不是说传男不传女吗?”郭一山一把拉住妻子的手,压低声音说:“传男不传女,是说传儿子不传闺女。因为闺女早晚是要出嫁的,一出嫁,就把秘方带走了。你是郭家的媳妇,不是郭家的闺女!”“祖上有传媳妇的吗?”新媳妇问。郭一山摇了摇头,说:“祖上没干过的事我们就不干了?只要对事业有利,我们就能做。走,你不但要认字,还要认药!”郭一山说过,拉住媳妇的手就往外走。二百年来,郭家的药房是不进女人的,这天晚上,它正式接待了平乐正骨的第五代传人郭一山的新媳妇,他一个一个地打开药柜的抽屉,让她一味一味地看了个遍,一味一味地嗅了个遍。从闺房的粉香到新房的墨香,云大妮走了二十年,从新房的墨香到药房的药香,她仅仅用了两个晚上。眼睛似的药柜将记住:第一代到第四代,平乐正骨产生了四个正骨大师,而第五代,将有两个大师出世,并将把平乐正骨的事业推向极至!
看着兴奋异常的妻子,一山说:“我不但要教你学医,还要给你再取个名字!”“取名字?”新媳妇扑扇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啊,我是学生了,要有个官名对吗?”郭一山为媳妇取名“云鹤鸣”,还特意作了一幅白鹤翔天的图画,旁批一行小字:云中一鹤 高翔长鸣也
“云鹤鸣!”一山大喊。“啊!”新媳妇下意识地答应。“现在开始上课!”郭一山有了学生,一下子精神了很多。“哎哎哎,别慌先生别慌,学生还没行拜师礼呢!”云鹤鸣说着,忙跑进里间。她脱了上衣,换上崭新的旗袍,又拿梳子对着镜子把头发拢了拢,最后捡起笤帚扫了扫鞋上的土,这才走出来到了丈夫跟前。
郭一山微笑着看妻子:“真行礼了?”“先生,”云鹤鸣喊一声,连忙害羞地低下头去,自语似地说,“我爷是个教书先生,我大伯也是个教书先生,我们云家的男孩儿都认字,女孩儿却一个也不能上学。小时候我做过多少次上学的梦,印花布的书包都缝好了,到后来还是没能进学堂。谢谢先生,从今后我也能当学生学认字了!”云鹤鸣敛一下衣襟,忽然双膝跪了,恭恭敬敬地给丈夫磕下头去。“嗯,嗯!真磕了?”丈夫笑着忙去搀她。云鹤鸣站起身,抬头看着丈夫,两行热泪顺颊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