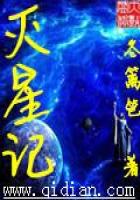“我高兴?我只有难受我咋能高兴!”郭一方摊开双手表白着,“高位截瘫……你身体再好……哼!再说,那是亲家母呢,我咋恁想让她死呢?她死了我有啥好处呢?说这话……大小便失禁,呼吸困难。你不死——”郭一方小声自接,“谁死?”一方看一眼老婆,禁不住又说,“早年咱伯看那个媳妇,二十岁不到,年轻不年轻?井里没水,她以为有水呢,一头栽下去,顶到泥上。就这,拉过来不死了?高位截瘫,谁也没法!这媳妇,哼!”“好了吧!”郭崔氏瞪丈夫一眼,气不打一处来,“你就不能少说点儿!成天戗戗戗戗!”一方狠狠地看老婆一眼。郭崔氏接着往下说:“兄弟媳妇骂她娘她知道不对,自己说老公公难听话时就不知道对不对了。财呀,你一辈子的事多着呢!”娘说着,看儿子一眼。
云鹤鸣忙完了亲家的事,大声对改妞说:“改妞,你娘身边不能离人,一有啥事赶紧叫我。”“中中,大娘!”改妞连声应。
门楼下,咬唇皱眉的壮年男人一声不吭地坐在治疗床上,见郭济远擦着汗走出厢房,大声说:“郭先生,该给我看了!”“好的!”济远响亮地应一声,坐在了壮年人的对面。旁边的小伙子禁不住插话:“红薯窖挖好,我哥出来了,身子一歪,掉窖里了,腿了一下!”摸着壮汉的大腿跟,济远小心地揣摩了一下,说:“你不要用劲,尽量放松啊!”说着,右手抓紧病人的下肢,左胳膊使劲一顶,“好了!走走。”壮年人睁开眼睛。“咋样?还疼吗?”十九岁的郭济远一脸调皮。小伙子连忙搀他起来。“不要搀,让他自己走!”济远很自信。壮年人站起来,试着小走两步,感觉没事了,就在门楼下来来回回走了几趟,禁不住对济远伸出拇指:“哎呀小郭先生,你很快就会赶上老郭先生的!”
济远无语,一脸的灿烂。
看好病的壮年人出门走了几步,就听见一句问话:“老大,这是郭先生家吧?”抬头一看,面前站三个男人,两个年轻人用一条床单和两根柳棍做了一个软担架,问话的是五十多岁的老人,肩上背了个土黄布袋,一看脸型就知道这是一家人。“看病的?”壮年人问。“啊。小三……”老者正要解释,壮年人笑了:“就是就是,进去吧!”“哎哟,总算到了!”长者叹一口气,对着担架上的男孩儿说,“三,咱到了!”
外边的对话济远都听到了,外地口音,他有些好奇,站起来迎到门口:“您是?”“啊啊。俺是陕西宝鸡的。”老者搓着手,“小三摔坏了,治了快仨月了,越治越差火,没方儿了,俺爷儿四个就扒着货车来了。早年俺爷来平乐看过病!他说他开始还住错家了,治了两天了,才知道郭家在这边……”“啊,啊啊!”云鹤鸣正给人看病,站起身来,“啊,您,姓胡?”“对对对。您是……”老者惊问。“她是云先生!”旁边有人大声说。“云先生?不就是郭氏正骨的掌门人吗?我在路上就听说了!”长者一扭脸对着担架说,“三啊,你可得救了!”
“快抬过来吧!”云鹤鸣热情地说。两个汉子把担架抬过来。云鹤鸣问:“能坐吗?”“不能。”老者边应边把肩上的馍袋子放在地上。先生说:“让孩子躺床上!”众人帮忙把孩子移到床上。云鹤鸣走上前,和济远忙给孩子诊病。
老汉的大儿把爹拉到旁边,小声说:“爹,三也来到了,俺俩回去吧?”“就是爹,俺哥俩先回去吧,免得时间长了家里结记!咱出来三四天了!”老二说。“中吧!”老者一转身,掂起地上的粗布袋子,说,“这馍还有小半袋子呢,您俩都拿着,路上吃!”“您和俺兄弟吃啥哩?”老大犹豫着。“找着先生了,您就别管恁些了!”老者坚决地递过来。老大接过馍袋子,对着正看病的先生说:“云先生,谢您了,我和我兄弟先回去了!”“回哪儿?”云鹤鸣抬起头,一时有点儿茫然。“宝鸡嘛!”老大说过,和老二一起对着云鹤鸣鞠了一躬,转身往外走去。云鹤鸣直起身,看着弟兄俩破旧的衣服,在兜里摸了摸,摸出几个铜板递给儿子,说:“济远,去,让他们路上买茶!”“哎!”济远接过来,去追两人。
云鹤鸣给小三看了,又让儿子再给三检查。
郭济远站着,先观察了腿: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郭济远弯下腰再检查,摸、触、揣、探,忙了一阵,抬起头来,说:“两条腿不一样长,说明是脱位。可他又有明显的骨折现象,并且复位很差。”郭济远看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说,“应该是骨折合并脱位。”一扭脸问老汉,“胡先生,孩子究竟是咋伤着的?”
“他呀,正背着柴禾在路上走呢,财东家的马车忽然惊了,挂着孩子拖了很远……唉呀,捡一条命!”胡老汉摇着头。
云鹤鸣看着儿子,认真地点一下头,说:“开始是骨折合并脱位,很准确。可现在,病人已经两个多月了,该是个啥病呢?就是典型的外伤性、陈旧性骨折合并脱位。准确说,是股骨头骨折合并髋关节脱位。脱位没有复位,骨折没有接好,孩子为啥一直发烧不退呢?就是这两种原因在作怪。”
“以前是咋看的?”郭济远问。“我们那儿没好医生,一个老太太给孩子捏了捏。她说骨头折了,等一段长好了就没事了。谁知道,唉!”老人很后悔的样子。
“济远,你看?”云鹤鸣看着儿子。济远又想了想,说:“娘,先给他复位吧!”娘问:“为啥?”济远说:“两个理由。一,复位比正骨简单;二,陈旧性骨折已过两月,再拖下去就不好治了。复位后,病人痛苦减轻,再接着说治疗骨折。”“咋治疗骨折?”娘面带微笑。“两个多月,病人的骨折虽然没接好,但已经长了骨痂。我的意思,破掉骨痂,重新续接。”郭济远说过,禁不住看娘一眼。他看娘不动声色,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马上又补充道:“病人今年才十五,不把骨头正过来,他一辈子就成残疾了……”“中吧,就按你说的办!准备吧!”云鹤鸣满意地看着儿子。
指着纸上的骨骼图样,云鹤鸣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给儿子和媳妇分析着财岳母的病情。“大嫂,大嫂!”一方喊着,和老婆郭崔氏及财夫妇走进屋子。财妻把一手巾兜鸡蛋放在桌上。
“哎,孩子,你这是干啥哩?”云鹤鸣大声阻拦她。“大娘,俺娘这事让您忙得……我是感激不尽,也没啥给您拿……刚嬎的,大娘您,补养补养。”财妻结结巴巴地说着。“孩子,这是咱自己家,又不是外边!你娘她也得补养!”云鹤鸣仍不愿意。“大嫂,您就收住吧!”一方说,“这些年净给您添乱找麻烦了,您兄弟、您侄的礼您是一点儿也没享过,今天好容易给您拿过来了,您就别再推让了吧!”
郭崔氏故作嗔怪地看丈夫一眼,笑了:“几十的人了,咋样说话哩!大嫂家不是比咱强嘛!不是不愿意拿,是拿了也没啥稀罕不是?”“中中中中,就你会说中不中?我这一辈子算是抬不起头来了!”郭一方笑着阻住老婆,一扭脸看着云鹤鸣又问,“大嫂,亲家这病,你看,究竟是咋回事?有啥妨碍没有?妨碍究竟会有多大?上午人多也没好多问。”
云鹤鸣叹一口气,说:“自己家里,咱就有啥说啥。亲家伤的是第六节脊椎骨。具体症状你们都看见了,肋间肌麻痹;下肢痉孪性麻痹。肱二头肌有反映,肱三头肌反射现象就没有了。其实,脊骨伤了只是现象,损了督脉才是实质。督脉贯脊通脑,总督周身之阳,被称作‘阳经之海’呀!伤得轻了,肢体功能会出现暂时性丧失。伤得重了,人很快就不行了。好在,亲家伤的脊关节低了些,要是第二三节脊椎,一半天里,人也就了了。”
“咦,大娘,您说俺娘真的恁厉害?这一抵,就能抵出这么大个事来?”财妻说。“这一抵!”公公禁不住接上,“你想想,她抵的目标是人,结果却抵住了墙。人多软,墙多硬,还会不出问题!”
鹤鸣说:“济远,晚上你多去看两次,一有情况,马上喊我。”“中中。”济远忙应。“别别,大嫂。济远也是忙一天了,叫他财哥值班!”一方抢着说。财妻也说:“就是大娘,叫您侄守着吧,孬孬好好,也是您的徒弟不是!”鹤鸣想了想:“那好吧,济远,和你财哥轮着,你守上半夜,财守下半夜!”
上半夜风平浪静,济远一边守着病人,一边坐灯下静静的看书。后半夜财来换班,他端了一碗汤,轻轻推开郭家大门,忽然听见一片的狗咬声。郭济财站住脚,下意识地往外看了看。
“这就是郭济财。”躲在黑暗处的刘仙堂小声对胡子说,“郭一山的徒弟,郭一方的大儿子。”“咋样,冲一下?”二孬掏出枪来。“别慌,看看都有啥人。”刘仙堂说,“他家可是游击队的老窝……”
听见狗咬,砖头扛着枪大步走过来,泥鳅和有也跑了过来。砖头大声问:“泥鳅,村东看了吗?”“放心时主席,我们转了两圈儿了!”泥鳅和有一起走了过来。泥鳅十六岁了,声音有些稚嫩。“泥鳅啊,不能这样明着转,要注意隐蔽!赵县长说,近段暗杀团很猖狂,记住,咱村还有个刘仙堂呢……”砖头说。“刘仙堂?他个王八蛋瘸子,敢回来露露头,我们就给他抓起来!点他王八蛋的天灯!”这个是十九岁的有,说话嗡嗡的。
刘仙堂拔出刀来。二孬也跟着拔枪。胡子拉住他们:“慢。小不忍,乱大谋。走!”三个人扭头钻进浓浓的黑夜。狗又咬起来。
砖头往外瞅了瞅,说:“注意隐蔽!搜查!”
第二天早晨,砖头还没醒有就过来了,他说村头墙上发现了反标,扬言要杀农会主席哩。砖头笑了,说:“好啊,我等了很久了!叫他龟孙来吧!走,看看去!”背上枪就往外走。驴驹从烂被窝里钻出来,大声喊:“爹,我饥了!”砖头站下来,扭脸看着儿子:“饥了吃封果子!”驴驹皱着眉:“果子腌心!”“喝点儿凉水。”砖头不耐烦了,大步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