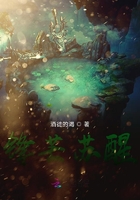他把燃烧着的打火机递了过来,我低头点着后吸了一口。他接着给自己点着,深吸一口香烟后,把烟雾从口中长长的喷出,目不转睛的看着我。我从面前的盘子里拿起另一个面包放到嘴里,桌子上空了的餐盘已经被撤了下去。
“我对你这个人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又有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他说。
“可能是我不太喜欢说话的原因吧。”我说。
“也不是,反正是无法用语言描述清楚。总之,无论是穿衣打扮还是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都让我羡慕不已。”他说。
“呵呵...这从何说起呢?”我问。
“就说我们在图书馆借书吧,你大多读的是英文原版书籍,这对我来说就仰慕不已;你喜欢浏览《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主动了解国家大事,并参与其中,但凡有这样习惯的人大多是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又身居高位的人物才具有的特性。”
“呵呵,你言过其实了。”我说。
“真的,国家这个词感觉离我很遥远。”他说,“就具体事情而言,你总是会跃过事情的本身去解读背后发生的原因,并试着找出真相,这在我以前的朋友中是绝无仅有的。”
“切,仅仅是多学习了一门语言。这可能也和以前的经历有关吧,仅此而已。”我若无其事地说。
“但在我看来确实是不可思议。”他说,“我见你很少存钱,休长假的时候经常背包远行,这让船上的其他人都议论纷纷,觉得无法想象。”
我略微点头:“呵呵,钱怎么花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再说,挣钱不就是为到更远的地方去嘛!”
“旅行对你来说,真的那么有意义吗?”
“当然,穿过田野,趟过河床,攀上高峰,去倾听大自然喁喁低语的言辞,一步,一步,一步……在深重的脚步中渐渐地感悟到生命的箴言,而那些关于攀登的记忆和苦难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愈加珍贵,直至升华成人生的财富,我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呵呵,感觉你说得很夸张,”接着,他摇了摇头望着我说,“总而言之吧,像你这样的人,我以前没见过。”
“呵呵。”
我听他说完后,稍微停顿了一下,感觉内心很释然。自己好像突然领悟到某种真理,而这种领悟是在漫无目的的游荡中产生的极度困惑和烦躁,刚才却在一吐为快的宣泄中倾泻而出。我稍微思索了片刻,接着把手里的面包放入嘴里,细嚼了几下后咽入肚中,然后抽出桌上的餐巾纸擦了擦嘴角。
“要不要来杯咖啡?”徐斌问。
“嗯,来一杯吧。”我回答说。
“加糖吗?”
“随便,”我张口答道,“苦和甜对我来说,都能接受。”
“好的。”
他站起身来,到咖啡机旁拿了两个空玻璃杯,按下咖啡机按纽,一股细流慢慢地注入杯子,接着他在竹篮里拿了两个白色糖包放在餐盘上端了过来。我们俩打开糖包倒入咖啡中,接着用调匙不停地搅动着杯里黑色液体。
“你有没有感觉老古这个人神神道道的?”我问。
“嗯,整天喋喋不休,真是嘈透了。”
“我是说,返航的时候,我看见他从甲板下往厨房搬了几箱鱼,我心想都要靠岸了,谁还会在船上吃饭呀?”
“噢,你说这个呀!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习惯了!都是看在他姐夫的面子上,他姐夫是咱们渔业公司的总经理,现在世界运行的方式不就是就样吗?”
“无耻。”我忿忿不平,“改天我们想办法捉弄他一下。”
“没必要。再说偷来偷去,都是他们家自己的买卖。”说到这,他忍不住噗嗤一笑。
“怎么了?你为什么乐成这样?”
“上回,水手长搞了他一次了,他刚把鱼搬到厨房里,我们就把门关上了。”
“哈哈,他肯定会在里面歇斯底里地大嚷大叫,”我笑着模仿道,“放我出来,放我出来。”
“没有。那时船已经靠岸,稽查人员正在登船检查。他肯定听到那两个胖子操着一口纯正的东北话问东问西,我想这家伙肯定在里面大气都不敢喘。”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都走了,一直关了他一夜,这家伙最后憋不住,拉在了厨房的地上。”
“哈哈哈.....”我们相对大笑着。
“最后还是我去给他开的门,我第二天早上装着上船拿东西,听见他在里面大喊大叫。于是就装作一如既往的质朴问道,是谁在厨房里?”
“他在里面说,难道你还听不出我的声音吗?是我。”他稍做停顿,端起杯子饮了一口咖啡放下,接着说道,“然后我才给他打开门,他千恩万谢的感谢我,事后他反过来不停地问我,到底是谁把厨房门给关上的。哈哈哈.....”
“再后来呢?”
“后来挨了船长一顿剋,他认为我们做的过火了,哈哈哈...不能让他拉在厨房;过后大家也都不了了之了,他虽然劣迹斑斑,但毕竟都是在海上工作,抬头不见低头见,需要团结;再说,大家都是生死相依的兄弟,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在海上的人对这些琐事都看得很轻。”
“是。”
我们相望着点点头,然后站起身来。
我们俩在大街上无所事事的闲逛着,黑色柏油路上车水马龙,街道两旁摆满了售卖的海鲜产品摊位。高低起伏的叫卖声覆盖了整条街道。大街上往返穿梭的多是质朴善良的女人们,男人们出海捕鱼,女人们沿街售卖,夫妻间合理的分工凸显了这个小岛上工作的特殊性,最终形成“石岛”独特的渔业文化。
下午,我和徐斌躺在院子里叠起的渔网堆上。我注视着晴朗的天空,云彩正在慢慢地在头顶上聚拢,被风掠起的纸片在高空中翻滚着,一会随风飘落了下来,一会又被风吹向了高空。
“我们去下螃蟹笼吧?”徐斌问道。
“不出去找女孩吗?”我意味深长地反问道。
“今天不想去,昨天晚上搞得有点过火。”他兴趣索然的摇了摇头说。
“呃。”
我翻起身来寻找着那片起伏不定的纸片。
“你在找什么?”
“一片纸片。”
“哪片纸片?”
“喏,在高空中飞舞的那片。”我用手指指向高空。
纸片在空中被风裹挟着向船坞的方向飞去,直到在我们的目光中消失。我们俩从空置的铺位下面掏出几个圆形的螃蟹笼,放上一些食堂废弃的鱼头和鱼尾,提着笼子向海边走去。
夕阳斜挂在地平线上,海边的沙滩已经被潮水淹没,与海滩毗邻的树木已经长出了嫩叶。林子里的空气清洁而明澈,鸟儿在枝头上左顾右盼,小草已经钻出了地面。
每次当渔船靠岸时,我总是会在这里转悠。这片树林大约有一千六百多亩,林子里大多是粗壮的槐树。每到夏天时,他们挺拔的树干在绿色的茂密的树叶中屹立着,非常的优美。树冠则高高地耸起,呈现在湛蓝的天空中,被阳光映射到地面上会形成一大片一大片的阴凉;西北角靠近人行道是一片银杏林,每年当到了深秋时,黄色的叶片总会窸窸窣窣地落到地面上来,直到铺成厚厚的一层,一阵秋风吹过,总是会听到哗哗啦啦的响声;各种鸟类在林子里安家,繁衍生息。灰喜鹊站在枝条上叽叽喳喳的叫着;燕雀在空地里跑来跑去;黄褐色的小松鼠敏捷地窜梭在树干间。
晚霞的红光缓缓地滑过树林,眼前的一切渐渐地变得模糊起来;码头的路灯还没有点亮,木制的渔船正在浅海区捕捞贝类,海平面上散落着渔船环照灯发出的红绿相间的光芒,犹如在空中放飞的“孔明灯”。“哒、哒、哒”船上的柴油机发出嘶哑的咆哮声。
码头北边到处裸露着的布满深色海藻的石块,潮水正在上涨但还没有淹没石堆。我俩顺着混凝土筑成的岸边把螃蟹笼放了下去,三个螃蟹笼上端的尼龙绳收在一起后长长地系在了岸边的三角铁架子上。潮水不断的上涨,漫过石堆后一直上涨到与遗留在岸堤上的黑色印迹看齐,螃蟹笼早就已经淹没汹涌的海水中。我与徐斌对视着一笑,在码头的水泥台子上坐下。
潮湿的风迎面吹来,浓烈的鱼腥味充斥着鼻腔,“啪、啪、啪……”大海推拥着潮水向岸边的巨石激烈的碰撞着。黑夜的幕布慢慢地罩住了朦胧的海平面,码头上亮起的灯光连绵不断地伸向繁华的都市。
过了一会儿,雨点从空中悄然落下,在海面上敲出一个个的小浅窝,雨水不像是春天那般细腻、缠绵,而是像夏日一样猛烈而急促,远处“威海卫”灯塔在雨帘中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周围的景象在朦胧的雨帘中渐渐地模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