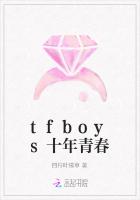西风狠烈,在一望无际的大漠之上纵横肆虐,黄沙弥漫到天际尽头。
天涯尽头,斜阳残照,半轮落日散发金黄色的光芒。在这片大漠,落日和狂风是常客。
哦,对了,还有他!
他,自漠北极恶之地而来,一身灰黑色的破旧衣衫,头发蓬松散乱,任由狂风摆弄。在地平线上,这个瘦削却又坚挺的身影孤独的走着,走着。
他,背着一把刀,用黑鹿皮包裹着的刀,这把刀随他出生,随他成长,随他风雪中见惯生死。
他,无人知其来历,无人知其过往,若问他名唤为何?
阳关北去不过百里,有一客栈,常坐于楼梯口的白胡老头儿会对店内吃酒的客人吹上几句:“若不乖乖付上酒钱啊,那刀客会从沙漠而来,将你们的狗头砍下挂在客栈前的酒幌子上。”
这时,酒客们会纷纷说些客气话,有的还会多要几两酒再付了酒钱。
该说不说,常在这片行走的,不管是拿命换钱的商客,还是掠夺钱财的马匪,但凡是听到刀客这两个字,都得耸耸肩,然后把心提到嗓子眼儿上来。
一日复一日,北风不休,黄沙不止。
他来了,他来了,他步履蹒跚的走来了!
西风古道,黄沙灌目,一缕悠悠长烟直上云天,地平线上没有任何生物,没有草木,茫茫无际的大漠在东升旭日的照耀下,呈现金黄的颜色。
渐渐的,似有一个人影冒了头,在地平线上,从沙漠深处走来,他在北风中坚定的独行着,背后是一把瘦窄长刀。
“就是他,上!”
毫无人影的大漠突然从那沙里窜出数十个灰衣刺客,人人手执一把斩马刀,直指刀客而去。
本来赶路疲惫不堪的刀客瞬间觉醒,十几把刀乍然劈来,刀客翻滚前扑踹倒两人,借两人身体腾空而起,趁势抽刀应敌。
所谓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是十几把锋利的斩马刀。一柄柄斩马刀紧逼刀客,他左闪右躲,在夹缝中寻找机会。
侧身躲过迎头一刀,他趁势以自己的刀别掉了对手的斩马刀,直接割喉敌人,血还未溅出,又是两把刀砍了过来……
长风呼啸,血映残阳!
远处,龙门客栈门口,一个白胡老头儿斜靠在门框上,眺望远方,和平日一样在等着什么。
大堂,打尖儿的住店的在享用着白胡老头儿起早就折腾出来的饭菜。这家店拢共就三个人,后厨有个掌大勺的糙汉,是白胡老头儿的儿子,前边跑堂的加算账的后生是孙子。三代人守着这老店属实好几十年了,风雨经了多少遭,也不知是为何偏偏耗在这里。
那坐堂中对着门的一桌客人最是聒噪,四个人争吵着给那中原江湖的武道大手子排上名号……
“凭着一只手力压几大派掌门的凌云寺挑柴人南柯上师,你说他够不上内家拳前三?开玩笑吧。”
气呼呼的壮汉抄起一杯酒饮了干净,然后等着对面端坐的白净书生。
左右两人也不急,只等书生反驳。那书生沉稳,面容挂起三分笑意,娓娓说道:“两年前,也是晚春,骁骑将军李玄廷亲上灵隐山和南柯上师坐论佛法,三日后李玄廷下山,南柯上师闭关修炼。”
“什么意思?”坐着的三人皱眉问道。
他们的对话也是引起旁人不少兴趣,这吃酒的客人大多是走南闯北的江湖客,所以还不等书生解释,却有一人接下话茬,“自然是南柯上师被后辈以拳脚功夫羞辱了,不然这泱泱天下,你可曾听说有诵经的和尚闭关修行?”
“是啊,是啊!”众人明白的同时,自然是对李玄廷这个名字上了心。
“将门虎子,当年李奕李大将军三千勇士死战匈奴五万骑兵,宁死不退,黄沙掩骨!最后活了六百人也没让后半尺之地,那是何等英雄啊。”
书生接下旁边人的话,继续说道:“那六百人也成了如今天下人都闻风丧胆的烈火飞骑。”
听到这里,坐在楼梯口的白胡老头儿悄悄叹了叹气,似是想起了什么陈年旧事。
有桌客人吃完上了楼,孙子小白手脚麻利,收拾了碗筷又出来擦桌子,这会儿功夫听得刚才那桌在讨论逍遥剑客徐遗墨和东海狂刀鲁沉山二人打起来谁更胜一筹,一番江湖语让小白听得入了迷,坐在凳上就瞧着眼前四人
徐遗墨和鲁沉山打起来谁能胜说不准,但输的肯定是围观的看客。二人境界皆为域境以上,覆手之间风雨如注,岂是寻常人能够品评言说的。
“哎,老几位,你们总说徐遗墨和鲁沉山为域境最强,域境是什么意思?”
书生看了一眼小白,大笑说道;“娃娃,天下武学派别不一,内外功夫,拳脚,心法,轻功,气功,有佼佼者,但多的是庸人。区分武学境界的有七境,是为晓境、洞天、破命、无相、上清、真玄、羽化。五境之上即为域,凡是入了上清境界都可自凭能力开启域,域之强,有千里传音万里寻踪,更可凭空造物搬山挪海。”
“这么厉害!”小白感觉十分神奇,这不已经算半个神仙了吗,难道真有那么夸张。突然,小白联想到了那个人,他当即就问书生:“大哥,你说那刀客算得上什么境界?”
年轻后生的话是有些人没弄明白的,书生身边坐的酒客就挠头问道;“刀客多了,你说的是哪一个啊?”
在这阳关以北,能说出这番话的,多是走海(江湖生意人的切口黑话,意思是在某地以自身能力谋取钱财。)的生客。书生抄起白扇轻拍那人脑门,“无知,大漠刀客,唯有一人,这七八年里除他以外,自称刀客的人要么刀丢了,要么人没了,你啊说话小心点。”
“是啊,这方圆数百里只有一把刀,那把见血才出鞘的北歌!”
客栈内,众人吃着喝着,议论声此起彼伏。本来稳坐在楼梯口的白胡老头儿突然冒出一句:他来了!
众人听得分明,皆从大门向外望去,只见远远的沙地上踉踉跄跄走来一人,他身形左右摇晃,但就是不倒,他十分瘦削却在狂风中不断向前。
十多双眼睛看着,他一步一步,由远及近,缓缓的慢慢的,从人影到愈渐清晰。赫然之间,七尺男儿傲立风中,他望了望那斜挂上空的太阳,坦荡一笑,拔腿朝客栈走来。
满满一客栈的人,酒不喝了肉也不吃了,只盯着屋外不过数丈间的那个刀客,他左摇右晃跌跌撞撞到了门外,却是脚下一个踩空,随着身子摔倒在地,人也终于晕了过去。
那一瞬,坐于楼梯口本稳如泰山的白胡老头儿耐不住了,他速速起身三步并作两步跨到刀客倒地之处,熟稔的将那年轻刀客搀起,背在自己身后,不理会眼睛直勾勾盯着的众人,把刀客驼入后院。
场中略微静了那么小会儿,小白面向众人,大呼:“各位吃好喝好!”
后院。白胡老头儿把刀客丢在水井边上,自己则坐在一旁的石阶上打量着他。
……衣服还是去年冬月那件,说好的过了除夕就换身新的
……脸上也多是沙尘,恐怕从西北陀罗城到此地三百多里又是走着来的,那刀上的血迹也不知有没有擦洗干净,不过看他破烂污秽的衣衫也能想明白了。
白胡老头儿等到傍晚,这才捶打捶打自己的腰腿,缓缓起身走到井旁。老头儿从水井中打上来约莫多半桶水,对着年轻刀客的脸便泼了上去,透心凉的井水一下激醒刀客,他晃晃脑袋睁开眼来,一看到是白胡老头儿,一边起身,一边咧嘴笑言:“老头儿,怎么还没死呢!”
“呵呵,你都没死,我怎么可能死。”
也是,刀客常年过着刀尖上舔血的生活,是要比白胡老头儿老死的可能性大。
“上元节在陀罗城城主府的那票是你干的吧,攒了三年的酒肉钱这次也该结清了。”白胡老头儿一脸精明样,盯着刀客腰间的钱袋子。
刀客先不理他,随手解下钱袋,丢给老头儿,便走向前院大堂。白胡老头儿双手接下钱袋,疑惑之时听到刀客留下句话:“算明白,多的我还有用。”
大堂里依旧是人满为患,这在平日是不多见的,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破落地儿,能攒着这么多人,恐怕也都是为了一睹年轻刀客的面目神采。
刀客走到大堂,不理会任何人,又跨出客栈,却是来到客栈左侧一个石碓处,有胆儿大好奇心盛的出来窥一眼,发现刀客对着石碓跪了下去。
那是一座有些年头的坟墓!
一小会儿,小白手捧托盘走出,托盘上是一碟牛肉,一只鸡,外加一壶酒。他将托盘放于墓前,便向后退去。
“爹!娘!儿子不孝,自打上元节末仇人们该杀的都杀绝了,这刀也是该封上了。”刀客一把抓起半碟牛肉,塞入口中,随之灌进烈酒,远远围观的众人直呼豪爽不羁,颇有英雄气概。却无人知那刀客生死数年间,只有烈酒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