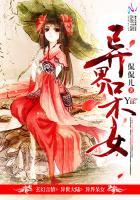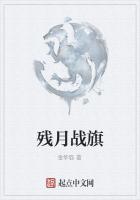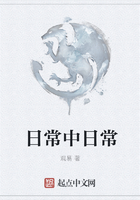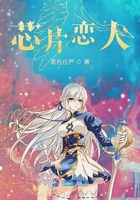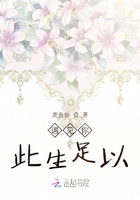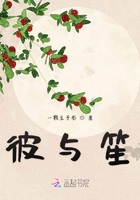身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也电告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
无可奈何之下,在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只好对《大公报》记者胡政之说:“吾已令我部士兵,对日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此事自应由政府负责交涉……仍望国民冷静隐忍。”为此,张学良一直深为悔恨。他迫于军令,不得不采取不抵抗政策,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他曾说:
“东北丢了,我张汉卿恨不得碰死,以去耻辱!”但是,也就在此时,却传来了张学良不爱抗日爱跳舞的谣言。张学良将军此刻的无奈和恼火,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马君武是从哪里得知的谣言?谣言又从何而起的呢?其实,这一切,都是日本人干出来的丑事。
在“九一八事变”前,为了能不战而下东北,日本最开始对张学良采取了绥靖政策,极力拉拢,结果遭到了张学良将军的严词拒绝。恼羞成怒的日本人,于是决定搞臭他的名声。熟悉中国文化的日本特务知道,要使一个中国人名誉扫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其私生活上制造绯闻。事也凑巧,影后胡蝶此时也正好去北京拍摄《自由之花》的外景。由于这部片子涉及到了袁世凯与日本无耻勾结的情节,日本人深为忌恨。于是,既为了打击张学良,也为了报复胡蝶,日本人经过精心策划,由日本通讯社散布了“九·一八之夜”的谣言。
很快,谣言就传到了马君武那里。当时,马君武正在上海办事,他闻讯义愤填膺,于是挥笔写下了《哀沈阳》诗。作为一位爱国学者,马君武(188l一1940,原名道凝,号君武,广西桂林人,曾留学日本、德国,我国第一个工科博士,“南社”著名诗人)一直从事着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在早年留学日本期间,马君武曾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历任总统秘书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广西省长等职,并在梧州创建了广西大学。有着拳拳爱国之心的马君武,自然是无法忍受这些“绯闻”的。
当然,也有人说,马君武发表此诗,跟他与张学良之间的“不快之事”有关。据说,马君武在北平创办私立民国大学时,曾请张学良给予经费支持。可是,张学良由于军费已穷于筹措,东北义勇军尚无力接济,因此对民国大学爱莫能助。于是,两人生出了不愉快。而这次谣言一出,马君武便大肆宣扬,以此报复。
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试问,上面那些日本人的幕后消息,当时的马君武又怎能知晓?平心而论,马君武之所以写这首诗,主要还是由于不了解内情,而一时激愤所致。这一点,从诗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对日本人强占东北的切齿之痛,便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此,当马君武知晓“不抵抗”的真相后,就立即发表了《致蒋介石、汪精卫电》:“日本已占据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狰狞如鬼,对外则胆小如鼠……”此时的他,已经知道自己冤枉了张学良和胡蝶。
而“九·一八之夜”中的另外一个“主角”胡蝶,更是冤枉透顶。她根本就没见过张学良,哪里谈得上一起参加舞会?
很多年之后,《胡蝶回忆录》追忆此事,胡蝶这样写道:“世间荒唐的事情还真不少,沈阳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那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约一周,未料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公案。”
原来,1931年9月的下旬,胡蝶随明星公司导演张石川等人,来到北平拍摄《自由之花》、《落霞孤鹜》和《啼笑因缘》三部影片的外景。这次拍摄任务非常繁重,需要在中山公园、北平公园和颐和园等多处拍摄外景。
一个多月后,拍摄任务完成了。在胡蝶等人离京前,梅兰芳在家中宴请了胡蝶一行人。席间,梅兰芳暗示说:“‘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在戏院看我的演出。”意思是说,他是知道实情的,“九一八”那晚,胡蝶根本没和张学良跳舞。
然而,蒙在鼓里的胡蝶哪里知道梅兰芳此言何意?等到胡蝶回到上海,已是11月下旬了。她刚一到家,就发现气氛不对:母亲似乎刚哭过,而父亲也在生气。她正在疑虑出什么事了,父亲却把一摞报纸摔过来:“你在北平干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呀,你自己看看吧!”
胡蝶拿过报纸,赫然几个大字标题映入眼帘:《红颜祸国》、《不爱江山爱美人》、《东三省就是这样丢掉的》。等到看完内容,胡蝶又惊又怒,她厉声斥责:“这根本不是事实,全是造谣!”闻讯赶来的张石川、洪深等看到了这些文章也很气愤。起初,他们想登报澄清,又担心会被人认为是欲盖弥彰。谁知,事态却越闹越大。很快, 《时事新报》上就出现了马君武的《哀沈阳》诗,并登有胡蝶的照片。一时间,舆论对胡蝶非常不利,到处都是指指点点。
此时,明星公司认为不能再沉默了,再沉默下去无论对胡蝶本人还是对公司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就在马君武诗发表的第二天,《申报》连续在11月21日、22日刊登《胡蝶辟谣》的启事。
尽管发表了辟谣启事,胡蝶对于马君武还是采取了理解的态度:
“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在她看来,“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讨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匕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这就是胡蝶,一个大义凛然和胸襟宽阔的女人。
香港脱险记
胡蝶的一生,是充满了荣誉与鲜花的一生,也是饱尝了苦难和艰辛的一生。人们往往记住了她的风华绝代、光彩照人,却忘记了她屡次遭遇的劫难。这些劫难,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须臾未离开胡蝶。1986年,20余万字的《胡蝶回忆录》终于完成,胡蝶如此追忆自己的一生:“翻开褪了色的相册,思潮如涌。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留下了我的欢乐,也留下了我的辛酸,饱尝了生离死别的痛苦。”
这句话里面所说,在香港留下的辛酸和感受的生死离别,就是指胡蝶那段惊心动魄的香港脱险经历。
1937年,已经是家喻户晓影后的胡蝶,准备暂时息影,好过一段平静的日子。那时,她已经和潘友声结婚,拥有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
可是,安宁的生活没有过多久,日本人的战火就烧到了上海。
淞沪会战开始后,身居上海的胡蝶己无法寻觅宁静。无奈,她只好与丈夫一起避居到了香港。
来港之初,由于这里还未被日本占领,战争的威胁还比较远,因此胡蝶一家的生活还是十分惬意的。那时,潘友声在洋行工作,收入颇丰。而胡蝶则操持家务,偶尔参加一些电影拍摄和社交应酬。总体上,生活相当平静和舒适。
尽管如此,见识过内地战乱的胡蝶仍在隐隐地担心,她时刻关心着战事发展。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们虽然苟安于此,却一直心悬着内地的抗战,而且依战事的发展,我们也曾预料,不可能在此长久住下去。”正是在这种预感下,胡蝶的心情也一天天变得焦虑不安起来。
十分不幸的是,胡蝶的预感应验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加紧了对香港的侵略。敌机没曰没夜地轰炸,香港已危在旦夕。
当时,很多在港的著名演艺界人士已经想办法离去,而胡蝶却因为家小的拖累,而一时无法成行。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胡蝶只得天天躲避空袭,全家生活在惶恐不安中。
离开香港,回到内陆,成为了当时胡蝶一家的唯一出路。然而,这又谈何容易?香港沦陷后,日本侵略军为了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极力拉拢香港文化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在香港,具体执行这项政策的,就是时任侵略军报道部艺能班班长的和久田幸助。
和久田幸助就任后,得知梅兰芳、胡蝶等中国艺术界名流都在香港,便决定先把他们拉下水。在他看来,只要先成功拉拢这两人,日本实行怀柔政策便会十分顺利。因此,梅兰芳、胡蝶就首当其冲地成为了和久田幸助“糖衣炮弹”的攻击目标。
然而,和久田幸助如意算盘打早了一点:梅兰芳蓄须明志,坚决不肯跟日本人合作。恼羞成怒的和久田幸助见奈何不了梅兰芳,便开始对胡蝶软硬兼施。
在胡蝶那里,和久田幸助同样碰了钉子。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准备“拜访”胡蝶、晓以利害之前,胡蝶已经前去看望了自己的老师梅兰芳,并且更加坚定了不跟日本人合作的决心。
胡蝶看望梅兰芳,恰好就在和久田幸助离开梅府的第二天。实际上,胡蝶早就得知梅兰芳住在香港,只是一直没机会前去拜见而已。在胡蝶眼中,梅兰芳就是自己的老师,因为她确曾在1935年赴苏联参加国际电影展会的途中,向梅兰芳学习京剧。梅兰芳的德艺双馨,一直以来,都让胡蝶相当敬佩。胡蝶常骄傲地对别人说:
“我还是梅兰芳的亲传弟子呢!”
在梅府见到恩师,胡蝶激动万分。然而,此时的梅兰芳,因为精神焦虑,显得十分清瘦,没有了以前那潇洒俊秀的气质。加上蓄须明志,更让梅兰芳看起来苍老了许多。
寒暄之后,胡蝶直接问道:“梅先生,听说日本人这几天正逼您到日本东京去唱《天女散花》?”
梅兰芳神情严峻地答道:“是啊。如此国难当头之际,我岂能到东京为虎作伥。那个叫和久田的已来过几次,都被我严辞拒绝。”
胡蝶敬佩地点着头:“那么,梅先生是否有意去重庆?”
梅兰芳答道:“我不会去重庆,我暂时哪儿也不去。我想,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份中国人的骨气,谅他日本人也奈何不得。”
接着,梅兰芳担忧地说:“胡小姐,我现在倒很担心你,听说日本人也要找你。而你一个弱女子,能抵挡住他们的威胁利诱吗?
不过请你千万记住,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保持民族气节!”
梅兰芳这番话,给了胡蝶很大的精神动力。她严肃地答道:
“请梅先生放心,我胡蝶决不当‘汉奸明星’!”
此刻的胡蝶,内心肯定已经做好了跟日本人周旋到底的准备。
就像老师说的那样, “只要有一份中国人的骨气,谅他们日本人也奈何不得。”
然而,敌人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胡蝶的。刚从梅府回到家,胡蝶就发现和久田幸助早已来了。
和久田幸助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开门见山地说:“胡女士能在战时留在香港,我们非常高兴。现在已有一批文化名人逃离香港返回内地,我们希望胡女士不要这样做。只要在你肯支持我们‘大东亚圣战’,并参加‘共荣圈’,我们决不伤害你,特别是像胡女士这样中外皆知的大明星。”
胡蝶对他的用意心知肚明,因而不置一词。
和久田幸助接着说:“大日本皇军对你们这些有名望的人,拟定了三条政策,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宽容。第一,如果你们愿意留在香港,我们妥切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第二,尊重你们名人的自由,如果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的话,即时无条件放入;第三,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场上互相合作。不知胡蝶女士对上述条件是否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