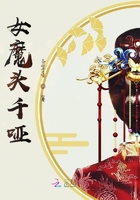刘清远和阿福回到大院,刚刚进到办公楼走廊里的时候,正好赶上王有良领着人从会议室走出来。
王有良看到阿福扶着半昏不醒的刘清远,回头对班子成员们说,你们先回到会议室,再喝一杯茶吧,我要和咱们的刘大主任单独谈谈。
雷开点点头,把手往后一挥,带着干部们又进了会议室。
王有良冷冷地对刘清远说:到你的办公室去说吧。
刘清远定定地看着,像是没有听懂,也没有反应。
王有良不管他,自顾推开主任室的房门,进到里面坐在沙发上。
阿福看到这个阵仗,竟然急出了一身冷汗,连拖带拉地把刘清远推进办公室,勉强站在那里,正对着王有良。刘清远站也站不稳,仍是定定地看着他笑。
王有良看到刘清远这个样子,也没有更多废话,只说了一句:“你还有脸回来?你可把脸露到天上去啦。明天开会,专门讨论你的作风问题!你先准备一下交待材料吧。”说完就立起身来,摔门扬长而去了。
那个开会时两次发笑的女办公室主任站在会议室门口观察动静,见到王有良向外走,就向屋里喊:“大家都出来吧,走了。”会议室里的各位显然没有想到与刘清远的谈话结束的这么快,只听一阵乱放茶杯的声音,还有人慌乱中带倒了椅子,发出巨大的响声。人们小跑着去追,经过主任办公室的时候可以透过半开的屋门,看到刘清远晕倒在地上,任刚端着一杯水站在旁边,阿福正在手忙脚乱地给他掐人中。
刚走了不到十分钟,王连甫开着吉普车来到大院。
王连甫二话不说,一头扎进主任办公室,对任刚和阿福说:“快快快,把人弄到我车上去。我的车子就停在大楼外面,没有熄火。”
任刚和阿福正在六神无主,听后来不及多问,就一前一后把刘清远抬了起来,向楼外跑去。走廊里没有一个人,但他们能感觉到有无数双眼睛,从各自的办公室里往外窥探着,彰显着每个人都想知道事情原委的情愫。事情的结果已经非常明显,那是无须猜测也不用探究的了。
把刘清远安置在后座上之后,王连甫开车就向大院外面跑去。任刚在后座上扶着刘清远,顺便问了一句:“咱们这是去哪儿?是送刘主任去医院吗?”
王连甫头也不回地:“去啥医院,他又没病。去我的招待所吧,那里还安静些。”
坐在前座副驾驶的阿福和任刚异口同声地发问:“为啥?”
王连甫哼了一声:“你们还不知道?阿炎的死信在滨海市已经传开了!老常气病了,医生检查是心肌梗塞,正在抢救。常燕现在是腾不出空来,要是有空,早就到这来大闹天宫了。还有阿炎的姑父姑妈,也要找刘清远讨个说法。领导也正盯着他,你们说这个时候还能去医院?”
两个人被这一席话惊呆了,再次异口同声:“你咋知道的?”而他们心里想的却是,你怎么来这么巧,你叔叔的问罪大军刚走,你就来了?
王连甫又哼了一声:“你们别忘了王有良是我什么人。我和刘清远毕竟是同学,他们的关系我不管,但我总不能眼看着他陷入麻烦。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就住在招待所,大门也不要出,照顾好刘清远就行了。”
任刚问:“那单位的工作呢,不管了?”
王连甫直接嗤之以鼻:“屁。你们的大哥都完了,你们还有什么工作!别的不说了,阿福你把公车私用,又毁成那个样子,扣你十年的工资能不能还得起?都够判你三年的了。还有你任刚,前些年伙同韩得宝整我叔叔的事,你敢说没有参与吗?有的账都在人家那里放着呢,不愁清算哩。还要工作?先省省吧,把刘清远的病养好再说。”
说着话的功夫,吉普车已经拐进小道,开进后门。大雪初晴,大街上基本没有什么行人,招待所的后门更是悄无人声。任刚点了点头,看来这个王连甫预算周详,早就想好了窝藏他们兄弟三个的计划。也说不定他早就知道了今天的结果,早就躲在附近哪条街巷的角落,等他叔叔的部队一撤,就开始实施他的逃亡转移计划了。
这是他们叔侄精心策划的一出双簧戏呢,还是为了同学之情的冒险大营救?任刚想不出个所以然,阿福就更加无从得知。
用了整整一天时间,院里院外屋里屋外被王家旺收拾的一尘不染。在王家旺的记忆里,就是他娘在的时候,这个小院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光鲜干净过。虽然是摇摇欲坠的土坯房,但只要打扫出来,也带着三分喜气洋洋的神采哩!
房顶上的积雪都扫下来了,院子里的积雪也都堆在了角落里,甚至还被老旺用铁锨堆砌成两个大雪人的样子,可爱的发傻。
孩子交给了婶娘,让她先用羊奶帮着喂养着,自己要把这个家拾掇得焕然一新啊,好安置这个从天而降的新成员。婶娘看到这个冰雕玉琢似的孩子,惊喜的不得了不得了地,一直问前问后问这问那,王家旺什么都不说,就一句:“村头柴火垛底下捡来的,是俺娘送来给俺当儿子的。”再问,还是这句话,多一句不说。
婶娘就不再问了,只说左一句“可怜的孩子哟”,右一句“这是作的什么孽哟”,把那孩子亲也亲不够,放到炕上再抱起来,抱起来再放下,手足无措六神无主。
王家旺也不管她,让她得意着去吧,反正这是我的儿子,我要把咱们爷儿两个的窝先收拾好再说哩。
等他把院子和屋子都收拾完了,再过来看孩子的时候,见婶娘家的屋子里已经站满了人,一看都是本村的婶子大娘还有新过门的小媳妇儿,这情形竟比谁家娶亲还要热闹,直把老旺弄得一愣一愣地,不明所以。敢情!原来是婶娘实在忍不住心里的喜悦,临潼献宝一般挨家挨户去告诉,弄得全村的女人都跑来看“狗蛋娘给狗蛋送来的儿子”了。
一看到老旺进了院子,满屋子的女人都炸了窝:
“你看你看,孩子他爹来了哩。”
“你看你看,这孩子的下巴颏还真有点像狗蛋哩。”
“瞧你这张嘴呀。人家都当了爹哩,你还能狗蛋狗蛋地喊!人家有大名呀,叫什么什么旺旺来着?”
“你们家那条黄狗才叫旺旺哩。人家是叫家旺,是吧家旺?”
屋子里的女人们叽叽喳喳不休,又是嘻嘻哈哈不绝,一阵一阵的声浪都快要把屋盖子给顶起来了。
哇地一声,把一屋子的叽叽喳喳声都给震住了。原来熟睡中的孩子被这一片噪杂惊醒了,睁开眼见到一屋子的人,有些害怕,就大哭起来。娘呢娘呢?那个天天喂自己吃奶的穿花衣服扎红围巾的好看的娘呢,怎么不来抱自己不来给自己喂奶吃了?怎么这么多没见过的人呢,这是在哪里呢怎么一下子全变了呢?
孩子搞不懂,搞不懂就愈加努力地大哭。
“老旺,你的儿子哭了,你不管吗?”站在屋门口的一个女人向着院子里的老旺大声叫嚷。
“是老旺来了吗?让他快来喂他的儿子,他的儿子饿了呢。”另外一个女人喊。
“还是让老旺他媳妇来喂吧,老旺没有呀。”一个中年女人嚷。
“老旺还没有娶媳妇哩。你年轻,正奶着孩子,你来喂吧。”一个老女人冲着一个小媳妇说着,就去掀她的胸襟儿。屋子里一片哗然大笑,孩子却哭得更加震天响。忽然之间,像被刀子割断了纳鞋底的棉线一般,孩子的哭声嘎然而止,变成了咂咂地吸奶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