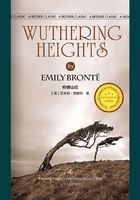“所有人都目光短浅,这才是最可怕的!从前冬天我一直住在莫斯科……但现在我丈夫库克申住在那儿。并且莫斯科现在……我不知该如何描述——也不是以往的样子了,我想去国外,去年就差点儿成行。”
“不用说是去巴黎吧?”巴扎罗夫问。
“巴黎和海德堡。”
“为什么要去海德堡?”
“要知道,本津在那儿!”
这话倒让巴扎罗夫哑口无言。
“Pierre,萨波日尼科夫……您听说过他吗?”
“没,没听说过。”
“哪能呢,Pierre萨波日尼科夫……他还常在利季娅·霍斯塔托娃家里。”
“这女人我也不知道。”
“哦,就是他准备陪我去,感谢上帝,我是自由的,没孩子连累……瞧我说了些什么:感谢上帝!不过也没什么。”
叶夫多克西娅用已熏成褐色的手指卷好一只烟卷,用舌头舔了舔,吮了会儿,点燃吸了起来。女仆端着托盘走了进来。
“啊,早餐来了!一块吃点儿?维克多,打开瓶塞,该您负责。”
“我负责,我负责。”西特尼科夫连声说,又尖声笑了起来。
“这儿有漂亮女人吗?”巴扎罗夫喝完第三杯酒后问道。
“有,”叶夫多克西娅回答,“不过她们头脑空虚。比方说monamie奥金佐娃长得就很好。可惜她的名声有点儿……这倒也不算什么,只是她缺少独立的观点,没有广度……这些她们什么也没有。整套教育体系必须改变。我已想过这个问题了;我们妇女受的教育太糟了。”
“我们对她们也没办法,”西特尼科夫附和道,“她们应该受到鄙视,我就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轻视她们!(有机会轻视或表达自己的轻视,对西特尼科夫来讲,是最惬意的事;他很喜欢攻击女人,自己决没料到,几个月之后他会拜倒在妻子的石榴裙下,仅仅只因为她是杜尔多列奥索夫公爵的小姐)没有一个女人可以理解我们的交谈;没有一个值得我们这些正经男人一提!”
“她们完全没必要理解我们的交谈。”巴扎罗夫说。
“您指谁?”叶夫多克西娅插了句嘴。
“漂亮的女人。”
“怎么!您是赞成普鲁东的观点喽?”
巴扎罗夫傲慢地挺直身体,“我不赞成任何人;我有自己的看法。”
“打倒权威!”西特尼科夫嚷道,他十分高兴可以有机会在自己崇拜的人面前强烈地表现自己。
“可马科列伊自己……”库克申娜说。
“打倒马科列伊!”西特尼科夫的呐喊惊天动地,“您要为那些娘儿们报不平吗?”
“不是为那些娘儿们,我是为女权辩护,我发誓扞卫女权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打倒!”不过西特尼科夫立即又止住了,“不过我不否定女权。”他说。
“不,我知道,您是斯拉夫派!”
“不,我不是斯拉夫派,虽说……”
“不,不,不!您是斯拉夫派。您是《治家格言》的信徒。您手里最好拿根鞭子!”
“鞭子不错,”巴扎罗夫说,“只是我们已到最后一滴……”
“最后一滴什么?”叶夫多克西娅抢断了他的话。
“最后一滴香槟,最尊敬的阿夫多季娅·尼基季什娜,是最后一滴香槟——不是您的血。”
“当有人进攻女人时,我不能撒手不管,”叶夫多克西娅继续说,“这十分可怕,太可怕了。您还是不要攻击女人,最好读读米什列的《De l,amour》。那的确是本绝世好书!先生们,还是让我们来探讨爱情吧。”叶夫多克西娅又说,一只手散漫地放在皱巴巴的沙发垫上。
突然大伙都缄默起来。
“不,干吗要讨论爱情呢,”巴扎罗夫开了口,“您刚提到奥金佐娃……您似乎是这么称呼她的吧?这位太太是谁呀?”
“她长得特别迷人,很妩媚!”西特尼科夫怪声怪气地说,“我来向您介绍,她既睿智又富有,还是寡妇。遗憾的是,她还不算进步;她应该常和我们的叶夫多克西娅接触。为您的健康干杯,Eudoxie!来,碰碰杯!Et toc,et toc,et tin-tin-tin!Ettoe,et toc,et tin-tin-tin!
“Victor,您真淘气。”
早餐持续了很久。香槟一瓶接一瓶,一连开到第四瓶……叶夫多克西娅一直喋喋不休;西特尼科夫跟她一唱一和。他们闲聊得最多的是——婚姻究竟是什么,是一种虚文浮礼还是罪过,人是否生而平等,以及到底什么是个性。最后叶夫多克西娅喝得满脸通红,用扁平的指甲敲着音色不准的钢琴键盘,用一副沙哑的嗓声唱起茨冈歌曲,接着又唱赛穆尔——希夫的情歌《昏昏欲睡的格拉纳达在打盹儿》,西特尼科夫头上包着一条围巾,扮演死去的情人,当她唱到:
你的双唇和我的,
在热吻中融为一体……
阿尔卡季最终忍不住了,“各位,这儿已像疯人院了。”他大声道。
巴扎罗夫只时而插进几句嘲弄,主要在喝香槟。他大声打了个哈欠,站起来,也没和女主人道别,就拉阿尔卡季一同离开了,西特尼科夫跳起来,赶忙跟上去。
“喂,怎么样,怎么样?”他问,献媚地在他们左右跑来跑去,“我说过:她是个先进的人物!这样的女人多点就好了!就这一点来讲,她是个高尚的道德现象。”
“那你父亲的铺子也是个道德现象?”巴扎罗夫说着用手指指他们正路过的一个小酒馆。
西特尼科夫又尖声笑了起来。他对自己的出身深感自卑,因此对巴扎罗夫的忽然亲热(称他为‘你’而不是‘您’),他不清楚该感到庆幸呢,还是气恼。
十四
过了几日,省长官邸的舞会如期举行。马特维·伊里奇是这个舞会的真正“主角”。本省的首席贵族逢人就说只是出于对马特维的尊敬才来的,省长在舞会上,甚至纹丝不动时,也没停止“发号施令”。马特维·伊里奇待人的谦和和傲慢相当。他对所有人都特别亲热——只是对有些人带点厌烦,对有些人带点尊敬;在女士面前他en vrai chevalier francais一样大献殷勤,不时地发出阵阵洪亮的笑声,这也跟一个大人物的身份相符。他轻轻拍着阿尔卡季的后背,大声叫他“好外甥”,而对身穿旧燕尾服的巴扎罗夫,只是捎带着赠了一个漫不经心、故作宽容的一瞥,从喉咙里冒出一句含糊不清的客气话,只能听见“我”和“很”这两个字;他伸给西特尼科夫一根手指,朝他略微一笑,但头已经转到另一边;甚至对库克申娜他也说了句“Enchanté”。库克申娜来参加舞会也没穿硬骨钟式裙,还戴着双脏手套,头发上插了只极乐鸟。来宾相当多了,跳舞的男宾也不少;文官大多挤在墙边,而军官们却跳得十分起劲,尤其是其中一位,曾在巴黎待过六周,在那儿学会了各种大胆豪放的感叹,比如“zut”,“Ah tich-trrre”,“Pst,Pst,mon bibi”等等。他发音特准,地道的巴黎腔,但同时又拿“si j’aurais”代替“si j’avais,”,把“absolument”的意思当作“一定”,一句话,他说的是大俄罗斯的法国土语,当法国人没必要恭维我们法语说得和天使一样时,“comme des anges”,他们会大大嘲笑这位仁兄的。
我们知道,阿尔卡季舞跳得不好,巴扎罗夫则一点儿也不会,他俩待在角落里;西特尼科夫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他的脸上显露出轻视的嘲笑,嘴巴刻薄地评头论足,眼睛放肆地四处张望,似乎感受了全方位的享受。忽然他的脸色变了,转向阿尔卡季,似乎有些惶恐不安地说:“奥金佐娃来了。”
阿尔卡季回头看去,只见一个一袭黑衣的高个子女人,站在大厅门口,庄重高雅的举止令他倾倒。她裸露的双臂优雅地垂在亭亭玉立的身躯两旁;几枝轻盈的倒挂金钟沿着她柔亮的秀发漂亮地垂到微削的肩头;稍微前突的白皙额头下是一双浅色的水汪汪的眼眸,宁静而聪慧地(只是宁静,而并非沉思地)瞧着,嘴角留有几乎察觉不到的一丝微笑,脸上透出一股亲切温柔的力量。
“您认识她?”阿尔卡季问西特尼科夫。
“很熟的。想让我给您介绍吗?”
“好吧……等这曲卡德里尔舞跳完后吧。”
巴扎罗夫也留意到了奥金佐娃。
“她是谁啊?”他说,“和其它女人不一样。”
卡德里尔舞一完,西特尼科夫就带阿尔卡季走到奥金佐娃面前;但他未必真的和她很熟,他窘得语无伦次,她有点吃惊地看着他。不过当她听到阿尔卡季的姓时,脸上露出亲热的神情。她问他是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儿子。
“正是。”
“我见过令尊两次,而且常听人提起他,”她继续说,“很高兴认识您。”
这时一个副官跑过来,请她跳卡德里尔舞。她答应了。
“您也跳舞吗?”阿尔卡季恭恭敬敬地问道。
“我跳啊。您为什么以为我不跳舞呢?是不是觉得我太老了?”
“哪里哪里,您怎么会……那么请准许我请您跳一次马祖尔卡舞。”
奥金佐娃宽容地笑了笑。
“好吧,”她说着望了望阿尔卡季。并不是傲慢地,而是像一个结了婚的姐姐在看很小的弟弟。
奥金佐娃比阿尔卡季只大几岁,她刚过29岁,但在她面前他觉得自己婉如个小学生,一个傻头傻脑的小伙子,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显得更大一些。马特维·伊里奇带着一副高傲的样子上前来恭维她。阿尔卡季走到一边,继续打量她,甚至在她跳卡德里尔舞时也目不斜视地望着她。她和舞伴讲话与和那位大人物一样,神色自然而从容,头和双眼轻轻地晃着,还柔声笑了两三回。她的鼻子和所有的俄罗斯人没两样,有些肥大,也算不上肤如凝脂;但阿尔卡季仍然觉得他从没见过这么迷人可爱的女人。她的声音老在他耳边萦绕;她衣裙上的褶子也和别人不同,似乎更挺更宽,而她的举止也格外轻盈自然。
马祖尔卡舞曲一响起来,阿尔卡季就觉得心里有点胆怯,他在舞伴身边坐了下来,打算交谈,可他的手不时挠头,就是找不出一句话。不过他只胆怯激动了一会儿,奥金佐娃的沉寂感染了他:不到一刻钟,他已毫不拘谨地和她谈起自己的父亲、伯父;说起他在彼得堡和乡间的生活。奥金佐娃彬彬有礼地仔细听着,扇子轻轻打开又合上;当有男伴来请她跳舞时,他的闲聊就被打断了;西特尼科夫来请过她两次。她回来,又坐了下来,拿起扇子,甚至胸部也并没起伏得更快,阿尔卡季又接着闲谈,在她身边交谈,凝视她的双眼和美妙的额头,凝望她端庄而聪颖的面容,他感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浸透全身。她话虽不多,可言语之间透露出她的生活阅历;从她的某些见解中,阿尔卡季断定,这个年轻女人有很多的感受,太深的思考……
“西特尼科夫领您到我这儿时,站您旁边的是哪位?”她问。
“您注意上他了?”阿尔卡季反问,“他特别帅是吧?那是巴扎罗夫,我朋友。”
阿尔卡季便讲起“他朋友”来。
他说得那么详细,眉飞色舞,以至于奥金佐娃也转向他,关注地望着他。这时马祖尔卡舞已近尾声。和自己的舞伴分开,阿尔卡季觉得十分遗憾,和她共同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小时!当然,在这段时间里他总觉得她似乎在屈尊俯就他,而他好像该感激她……不过年轻的心是不会因此而苦恼的。
一曲完了。
“Merci,”奥金佐娃站起来说,“您答应要来看我,请带您朋友一起来吧。我倒十分想见识这位有胆量怀疑一切的人。”
省长走近奥金佐娃说已备好晚宴,并心事重重地朝她伸出手。她离开时,又对阿尔卡季回眸一笑,点点头。他深深地鞠了个躬,凝视着她的背影(在他看来,那闪动着银灰的黑绸里的身躯是多么婀娜),想道:“现在她已把我抛在了脑后。”心里浮起一种莫名的谦卑……
“怎么?”阿尔卡季一回到那个角落,巴扎罗夫就问,“感觉快活吧?刚才有个老爷向我说,那个太太是——哟,哟,哟!不过那个老爷也像个白痴。哎,你认为,她是不是真的——哟,哟,哟?”
“你这什么意思!”阿尔卡季说。
“算了吧!多么纯真无邪啊!”
“那我就不明白您那位绅士了。奥金佐娃十分动人——毋庸置疑,不过她那么冷漠那么矜持,所以……”
“静止的水里……你自己知道!”巴扎罗夫抢断了他,“你说她特别冷峻,味道就在于此。我想你喜欢冰淇淋吧?”
“可能,”阿尔卡季喃喃道,“我判断不清。她想认识你,请我带你上她那儿。”
“可想而知,你把我描述成什么了!不过你做得相当好。带我去吧。无论她是什么——外省的交际名媛,或是像库克申娜那样的‘解放女性’,至少她那样的肩头我已久违了。”
巴扎罗夫的粗话让阿尔卡季厌恶,不过常常如此——他责备巴扎罗夫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这样……
“你为什么不想让女人有思想自由呢?”他小声说。
“因为,兄弟,我认为女人中只有丑八怪才思想自由。”
谈话到此结束。晚宴后两个年轻人立即就走了。库克申娜在他们的身影后发出一阵神经质的笑声,这是一种不和善和怯懦的笑:她的自尊心深受伤害,今晚这两个人谁也没在意她。她在舞会上呆得最久,凌晨三点多还和西特尼科夫跳了巴黎风格的波利卡——马祖尔卡舞。省长的舞会便以这个可资借鉴的表演落下帷幕。
十五
“我们来看看这个女人属于哪一类哺乳动物吧,”第二天当两人登上奥金佐娃下榻的旅馆楼梯时,巴扎罗夫朝阿尔卡季说,“我的鼻子闻着这儿有点不对味儿。”
“你让我吃惊!”阿尔卡季大声叫道,“怎么?你,你,巴扎罗夫,竟然还抱有这么狭隘的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