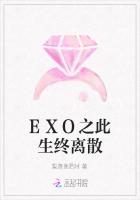孩子的哭泣声吓醒了昏了的宋美娜,她使劲地张开眼睛,脖子使劲地向着孩子哭声传过来的方位动着。她就觉得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劲,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一样,并且都是松软的,也在微微作着痛,这个不好受劲甭提有多不好受了。这是天下全部的男的都不会晓得,不会懂得的难过和难受;这是全部当了妈妈的人所体验的辛苦;这是俺们小孩子们一直弄不明白的宏伟。虽是很不好受,然而比起刚才那一会要强好多。才刚她还行思自个活不下去了,马上要去了,也好想赶紧一死了事,不再受折磨,这功夫她却尽量渴望自个坚强地生存下来,活下来。
宋美娜用虚弱的音量朝张大妈呼唤:“张妈、张妈,把婴儿抱来让俺瞧瞧好不好?”
张大妈一边笑一边哄着孩子,压根没留意,也没有听到宋美娜的话,更没有搭理她。宋美娜一连喊了几声,她才明白。
张大妈搂着孩子走过去,上了床,坐在宋美娜身旁,婴儿还在继续地哭,宋美娜就说:“张妈,这娃娃哭得那么凶,一定是个男孩吧?”
张大妈摇着头一笑讲:“你瞧这小孩生得眉清目秀,干干净净,像他爸不?”宋美娜一瞧讲:“俺瞧有点像,俺猜一定是个男娃。”
“像个球,不对,俺的孩子她娘呀,是位小姐,丫蛋儿,俺瞧这孩子蛮像你。”张大妈欢天喜地地夸着讲,好像这个孩子就是自个亲生的似的。
孩子还在哭着,宋美娜听着娃娃的哭声问张大妈说:“张妈,您瞧这娃娃哭得那么厉害,来让俺抱着悠悠她行吧?”
张大妈用眼一蹬讲:“不成,不成,你刚才贫血身弱,而且刚声产后的身子是要休息的。这孩子手脚并蹬,抓地厉害,不成,不成,肯定不成。”
听到王张妈一整串的不好宋美娜还不死心,继续不死心,然后又请求说:“好俺的张妈啊,你就行行好吧,俺又不抱着她,就是搂着她难道也不行啊?”
“不成,不成,肯定不成,……”张大妈继续坚持着说。
“就一会成不,哪怕一时也成好不?”宋美娜仍在商量着。
听到孩子的哭泣声,张妈瞧见泪水从宋美娜的眼角里留出来,顺着那纤弱的脸睑滑落到枕边上看不到。她心已经被这眼泪泡化了,她朝宋美娜身前移了移身子,拿手掀开被子,把既哭既闹的孩子放在宋美娜早就伸出摆好的胳膊拐里,盖上被子。可谁知道那既哭既闹的娃娃一挨着妈妈的身子上,立马就安静了,也不哭也不闹,不一会已经闭上了双眼,像是累了准备睡觉的模样。宋美娜和张大妈都瞧着孩子安祥的脸蛋,然后彼此对看一下都笑了起来。
“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认得她妈了。”张大妈笑呵呵地讲。
宋美娜有气没有力地说:“真是的啊!”
张大妈又讲:“这孩子不比普通的孩子。”
宋美娜微闭眼睛地说:“咋不能和别的娃娃相比啊?”
张大妈反着问说:“你怎么感觉的呢?”
宋美娜想说不想说地讲:“俺只感觉生这娃娃比其他的都不好受。”
“那就对了啊,”张大妈有趣地阐述道:“那个娃娃重七斤都,比普通小孩重了整整快二斤。所以身子发育咋样。因此生她你就感觉难受极了。然后,你瞧……”。
张大妈拿手碰了碰好像都睡死了的宋美娜,等她会过身来,张开双眼,张大妈拿手指着困睡了的孩子对她讲:“你瞧这孩子得干干净净,满脸的贵气,以后长大了准是人里的凤凰,你千万别把她随便卖给不认识的人啊!”讲完就捧腹大笑了。
正当张大妈和宋美娜两人在床上评价谈说娃娃时,一阵冰凉的晚风加上雨雾和泥土的味道从忽然打开的门闯进了屋子,跟着跑进一个全身上下浇得像个落了汤的鸡一样的人。房中油灯的火焰随着忽如进来的凉风晃了下,马上要熄灭了。张大妈赶紧伸手遮住油灯,火焰将熄灭时反而没有熄灭,房中的光照暗了下马上起来了。张大妈打着冷战,赶紧为母子俩盖严被子,回过身一瞧:闯进的人顺手关上家门,拿手正在擦头里的水!
宋美娜问张大妈说:“什么人来了啊?”
张大妈先应着宋美娜讲:“还能有什么人,是你孩子他爸,”再然后又对他说:“娃他爸,医生你请到了没?”
尚多楠老汉脸很难看地把情况的取来经过讲了出来。
张大妈骂说:“不过来去他娘的,摆什么臭身架,不来他们,俺们的娃娃怎么还能生不成吗?真有意思,请了都不过来。”然后她下床,整理了地下面的埋汰东西,为尚多楠老汉寻来了干净的上衣。
尚多楠走近床边,弓下腰,整个上半身都趴在床边上,瞧着媳妇,伸手抓住她的小手,抹着眼泪地讲:“孩他妈真是苦了你啊!”不一会的功夫,不知道是眼泪,还是留的汗液,还是外面的雨水,反正很快弄湿了那个被子的一角,弄湿了宋美娜的手臂和袖头,弄湿了宋美娜干着的心里。
宋美娜一瞧眼前这位男子的脸庞,听到他这句爱护的语句,一把拉住他这冰一样的手掌,心里就暖乎乎的,感受不到老公的手的温度了。
和过去比,也就是这时这刻,宋美娜才感觉自个是最快乐的,心中才是最踏实的。一小时之前时,她还认为此生此世大概再也看不到患难与共的老头了。好与不好,都过了那么长时间,没有感情也是有恩情的。唯有他在自己身旁,她才能觉得有了依靠,自己的精神有了托付,心中才会稳当,才会舒坦,才能快乐。一想到这里,宋美娜心中一感动,笑着笑出来了泪水,一并人又昏迷了。
张大妈见他们俩好久时间没讲话,进来一瞧,什么也没讲,掰开尚多楠的手叫他换湿的衣服,接着把宋美娜的胳膊放到了被子里,回过身来,坐在床边上。
尚多楠男子顺从地脱了湿的衣服。张大妈就打这个空子在他前面夸这个刚生的娃娃,还以为他很开心的,可谁知道蹲了好几个月的牛圈的尚老汉怎么也高兴不出来,他穿着衣服,想着:“自个才出了牛圈,有了逍遥,如今怎么又多出了个娃娃,自己和娃她娘心中虽是多了份高兴,可是身上也一并多了一个负担,往后的生活可咋办啊?!”
念着念着,就叹起声了。
生活虽是难过,然而时间绝不会由于哪个人的悲惨停止不前的。十多年时间,一晃而过去。
那时仍是哇哇喊叫,只晓得哭的尚丽丽,转眼已经从哇哇学语到慢慢学走;从喊爸叫妈到活蹦瞎跳,从那个小不点的毛丫蛋长成了这个吸人眼球的大女孩,而且仍然是目清眉秀,干干净净,而且比原来好看了很多。
女娃娃一长成了女孩,上门说亲的就伴随着岁数的增大一并增加了。
所有有过干活经验的农民都晓得:在乡下最忙是什么时间,最闲时又在什么季节。
当然,等到庄稼一种,施上肥,一下霜,叶子一落。劳累了整年的农村男人们就开始闲了起来。能离开的就都走了,帮人干些活,效些劳,为自个赚些钱,胡个口;离不开的人,呆在家中,干着闲活等到年末,喂着老牛缓缓磨。
每到这个时间,就也是乡下说婚谈嫁最火的时候,最热闹的完胜时间,乡下把那叫做“提亲讲媒”。大概就是讲:“倘若哪一方瞧上另一方,就让中介人把话讲清,讲透,喜欢就行,不喜欢就黄了。”里面这个牵线搭桥,前去讲话的人也就是俗称介绍的人,也是媒人,假如时常干这种事的媳妇,大家都叫她媒婆娘。
乡下的提亲讲媒特别简单,可能你都能干,其实就是其中一方的人瞧上另一方的娃娃,要想使自个的姑娘许配给别人为妻子,或是要想使人家的姑娘给自己家的男孩做老婆,都会让媒婆去讲。媒婆只需要去把那家的想法明确地传达到另外一家就可以了。
通常来讲:几乎都是男孩那方家里主动找人去女孩那方的家里提亲,自然也是有女孩这方托人去男孩那方的,就是为数不太多,极其少的。
正是在这个婚嫁的全胜时期。
一天的晚饭之后,尚多楠老汉又走出门聊天,宋美娜在锅上整理碗筷,孩子们坐在床上,学习的学习,写作业的写作业,看孩子的看孩子,没事情的围在一个很大的竹筛子旁边掰玉米。
门中猛不防备闪进一个中年女人,进来就冲着床上的娃娃们连笑并讲:
“你瞧瞧,那么些娃娃,小小岁数,都那么乖,那么明白,那么能干,天都暗了,仍在床上掰玉米,也不出去玩闹,可真是你爸妈的造化。”
讲完也没有等别人叫她,然后她自己把鞋脱了,上了床,帮孩子们掰玉米。
娃娃们都不想讲话,没有人搭理她,可她却没完地大声音问这个问那个:
“你上几年级几岁了啊?上哪个学校啊?”
“你爸上那儿里去了啊?你娘干什么去了?……”
娃娃们仍没有人回答,特别是尚丽丽,她一直低头,使劲地掰着手里的玉米棒子,这个掰完,级把空的蕊子用劲甩到床下,接着气昂昂地再拿来个,然后掰。
来的人一瞧就懂得了什么,她特意问起尚丽丽来,尚丽丽没法了,就特别小声讲:
“俺爸你来之前刚走了,俺娘正在锅边忙活呢!”讲着抬头看了下锅边,恰巧碰上娘阻止的眼光,赶紧低下头来,继续做自个的活。
宋美娜开始是在锅边忙活的,闻见有人过来,也只顾听她们讲话,忘记忙活,因此没弄出一点声音,所以来人认为家中没有大人,就有娃娃们。当来的人一听说大人在家,就疯疯火火地趴在床边半人多高的矮壁上,和宋美娜拉起了东家长、西家短,说起了闲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