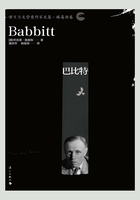如果你仔细去看,兵营在所有当过兵的人一生旅程中,确像一个码头。兵们从这里上岸,驻足,作长久的停留,然后,又从这里上路,各奔东西。
风一刮起来,树叶发芽的时候,新兵该下中队了。
树叶开始落了,老兵该复员了。
一批老兵从塔尔拉走了,一批新兵又到塔尔拉来了。
塔尔拉就像一个码头,迎来了一批批新兵,又送走了一批批老兵……
A1
叶尔羌河像一截马肠子,弯弯曲曲地穿行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河流到西北角的荒滩上,突然像人的胳膊一样弯曲过来,绕了一个大圈子,圈子里面就留下了一个方圆几百公里的岛屿。
这个岛屿就是塔尔拉。塔尔拉像一个圆头圆脑的孩子,安安静静地躺在叶尔羌河宁静的臂弯里。叶尔羌河,静静地注视着她怀里的这个孩子,无论她丰满还是枯瘦,她都以宽大的胸怀、无比的耐心接纳和倾听着发生在塔尔拉的每一个故事,她把这每一个塔尔拉的故事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又不动声色地将这些故事连同塔尔拉祖祖辈辈人的希望和幻想,还有他们的痛苦和忧伤,一齐裹胁着,奔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塔尔拉。
无论用什么方言念着这个地名,都会认为是外国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叶纯子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是在四川攀枝花市的一家鲜花店里。过后,叶纯子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念起来有点别扭有点异国风情味道的名字,从此就根植在了她的心中,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她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变。
在后来所有的日子里,叶纯子也没有搞明白,塔尔拉这个与自己丝丝相连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
叶纯子是随新兵一起来到塔尔拉的。因为她所认识的吕建疆今年在新兵连里担任指导员,只有等到在喀什驻训的新兵连训练结束了,才能让她来到塔尔拉。所以叶纯子就算好日期,在三月底上路来到新疆喀什,没想到这个路程一走就是六天,先是悠悠荡荡三天火车,然后吭吭哧哧又坐了三天的汽车,感觉已经走到了天的边沿,再走就该跌出天的边了,才终于到了那个叫喀什的地方。这一路的艰辛叶纯子还没来得及说,见到吕建疆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没有耽搁看沙枣花吧?”
在叶纯子的印象中,吕建疆永远是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样子,这次却给了她一个意外,不但脸上的神情放开了点,还居然腼腆地笑了笑,说:“还早着呢,塔尔拉的春天要到五月份才能到来。”
“怎么可能呢,在我们那里,五月都快是夏天了!”
你们那里毕竟是你们那里,可这里是塔尔拉。
吕建疆不好意思地笑笑,好像塔尔拉的春天来得这么晚都是他的过错似的,他小声说了句:“对不起,塔尔拉会使你失望的。”
叶纯子当时心想,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对塔尔拉的了解,除过一年前吕建疆去攀枝花接兵时,在鲜花店和叶纯子的那次偶遇交谈了几句外,再就是后来在两人的信件来往中,吕建疆对塔尔拉的叙述了。虽然在他们的通信中,塔尔拉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可实际上叶纯子对真正的塔尔拉并不了解多少,她的印象还只是停留在这个具有异国风情的地名上,和这个具有异国风情地名的地方上那芳香弥漫了整个春天的沙枣花上。
但叶纯子还是不顾一切地来了,在她心里,塔尔拉是一个充满了无穷诱惑力的神秘地方。她就想搞明白,为什么那个当兵的一提到塔尔拉,神情就是那么凝重,目光里充满了让人难以捉摸的内容。也就是从看到那种神情的那一刻起,叶纯子就在心里琢磨,塔尔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让她仅从这个奇怪的名字上就有种想了解它的欲望?也许是叶纯子的骨子里注入了太多的思考,导致了她的固执和好动的性格,所以当吕建疆在信中纯粹是出于一种下意识或者是出于礼节性地说出如果有机会请她到塔尔拉来时,她竟没有一点要客套一下的意思,毫不犹豫地就提笔给吕建疆回信说她要到塔尔拉来。她不顾父母的阻挡,随便捡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毅然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一到新疆,叶纯子就被新疆粗犷、雄奇的的自然环境惊呆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苍茫、辽阔的地方?”尤其是一看到天山,叶纯子简直不能控制自己奔涌的感情,真想大喊大叫一番,渲泻一下一直积压在胸中的郁闷。叶纯子是一心致力于雕塑和绘画专业的,用她专业的目光来看这个地方,处处呈现出自然主义的美感和艺术的张力。
自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叶纯子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业,其实她对职业要求不是太高,只是想有一个能接纳她能让她发挥自己特长的地方就行了,可现实总是不尽人意,她不但找不到一个能施展她才能的职业,而且她还饱受了包括她的亲人在内的许多人情世故的冷暖,为此她一直很苦恼。自从在攀枝花第一眼看到吕建疆,见多了油头粉面、被城市生活捏造得已没有性格的男人的叶纯子,立刻被吕建疆棱角分明、刚毅的黑脸膛吸引住了,她的脑子里当时就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吕建疆这张脸就是个天然的雕塑模型!待吕建疆一开口说话,他纯厚的音质更是充满了磁性,一提起新疆,吕建疆那种急冲冲地想一下子将“新疆”这个概念表达清楚的说话方式,使叶纯子对吕建疆,还有新疆充满了强烈的好奇,这种好奇心困扰了她好长时间,最后又促使着她,毅然地抛开牵绊她的许多世俗的东西,不顾一切地来到了新疆。
在叶纯子眼里,天山是这个地球的脊梁傲然挺立在中亚腹地,它像一个坚强刚勇的汉子展示着雄性裸露的蓬勃肌体,给人一种力的美感。但天山在许多人眼里,它没有能力撑到天上,就在苍茫的荒野上堆起一座气势非凡的高地,使东方大地从此有了高度,有了一片明净的天空和圣洁的厚土。从此,晶莹的雪再没有消融,冰封千里,承受着阳光的厚度,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作为仰望,能够掂量出天空下的天山沉甸甸的誓言一般的重量,这些誓言焦灼了千年万年,很难改变,就像人的信念。叶纯子心里这么想着,吕建疆他们在这么远的地方当兵,一定有这样的信念,才使他们心态如此平静的,那么自己的信念应该是什么呢?她感到很迷茫。
卡车载着新兵一大早从喀什出发,向塔尔拉开进。一路上几乎见不到人影,四周全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浩瀚如海,偶尔出现一些土沙包,连绵起伏,似碧波大海上层层叠叠的波涛一般。卡车行驶在石子铺就的土路上,就像一艘小船在浩淼的大海上航行一般,既辨不出前进的方向,也望不到令人振奋的海岸线。
正是戈壁滩这种毫无边际的沉寂,让最初走进塔尔拉的人会产生一种进入海洋的感觉。
叶纯子坐在专门留给她的驾驶室里,早被颠簸得头脑发胀,一路上她的胃里都在翻腾,有几次差点就要吐出来了,可到最后又只是一阵干呕,她昏沉沉地斜倚在靠背上。吕建疆和新兵们坐在卡车大厢里,叶纯子看到开车的老兵一副认真驾驶请勿打扰的样子,也不好和他说话,正好饱受颠簸的她也是难受得不想开口,便强忍着不适几乎半躺在座椅上默默地看着前方无穷无尽的戈壁滩。车窗外的戈壁滩始终没有改换它的景色,无论走到哪儿,给叶纯子展示的都是空旷和寂寞。叶纯子心里感叹着,如此广袤的戈壁多少个世纪来远离喧嚣远离繁华,就这样静静地寂寞着、孤独着、偏僻着和荒凉着,它的心中,该是有着一个什么样的梦吧,所以才如此执着如此忍耐!如果换了是人,人能忍受这样的荒凉,这样的寂寞吗?叶纯子转过身向后面望去,她听到从车厢里传来的,在车的震荡中摇晃着的咳嗽声,尽管什么也看不到,可她还是感觉到了一种安慰,心中有了踏实感。戈壁滩毕竟只是戈壁滩,让它永远独自守着自己的秘密好了,只要到了塔尔拉,一切都会像她想像中的那样充满了诗情和画意,会使她大开眼界,让她灵感不断的。叶纯子天真而乐观地想着。
因为塔尔拉在叶纯子的心目中已经被幻想过无数遍,真正快要见到它了,难免她心里会激动的,这份激动,使她强撑起疲乏的身子,望着前方和天粘连在一起的茫茫荒原,不由自主地感叹了一句:“这多像大海呀!”
叶纯子就这样走进了塔尔拉,也走进了她的与从前生活绝然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
A2
天快黑的时候,卡车像一艘饱经苍桑、已经疲惫不堪的旧船,在茫茫的瀚海中行驶了将近一天时间,终于靠到了码头一般的塔尔拉。
准确点说,塔尔拉就是荒漠中一座小小的孤岛,在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里,像一个张开臂膀的温暖的家,正等待着外出的人们归来。
早迎接出来的中队长一边大声叫老兵帮新兵们往下搬行李,一边叫值班员吹哨子集合新兵,准备开饭。
营房里一片吵杂声。
叶纯子从驾驶室里跳了下来,她像一道明亮的闪电,在营区里“滋啦”一声划过,所有的吵杂声都被击成碎片,悄无声息地落到了地上,所有的目光都像谁下了口令似的,“唰”地一下齐齐地都聚到了叶纯子身上。
叶纯子很难为情,要不是夜色渐浓,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还是中队长老练,在片刻的愣神之后,他迅速走上前来,笑呵呵地握着吕建疆的手说道:“老吕,真有你的,不但带了一帮新和尚,还接来了一位天使,塔尔拉今年可真是交了好运了。”
中队长中等个头,微胖,看上去壮壮实实的,脸有些黑,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特别有神,并且里面包含着很多内容,一看就是个有头脑又干脆利落的人。
第一次见面,叶纯子就感觉到中队长这个人有军人的气质,并且不失风趣。叶纯子就有一种亲切感,她很礼貌地把右手伸出去,对中队长大方地介绍道:“我叫叶纯子,是……吕建疆……的朋友吧!”她一直没有想过该怎样介绍自己,猛然碰上这个问题,思维一下短路,有点语无伦次了。
“知道!知道!我是王仲军,我们对你太熟悉了。”中队长大着嗓门说着,却没有回应叶纯子伸出来的手。
叶纯子的手被冷漠地晾在那里,她有点尴尬地侧过头望了望吕建疆。吕建疆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就示意中队长快伸手去接叶纯子的手。
中队长依然乐哈哈的,却对叶纯子已经伸出并且一直架着的手好像没看到似的没有理会。旁边人一看都明白他这是装出来的。
叶纯子心里咯噔了一下,咬了咬嘴唇,自己悄悄地缩回了手。
中队长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值班员,集合家伙们去吃饭,不饿是不是?愣看个啥呀。”
值班员集合队伍走了,中队长才转过身来,对叶纯子说:“实在对不起,让你难堪了,这里是塔尔拉,家伙们都在这里看着,我要和你握手,他们会有想法,今夜就得全体失眠了。”
叶纯子听中队长这样一说,觉得有意思,“扑哧”一下笑开了,心里没有了想法,刚才那手足无措的尴尬也消失得不见踪影了,竟好奇地说道:“没这么严重吧,中队长。我也知道你是三中队的中队长。”
“好,我们算是早认识的老朋友了,”中队长笑着说,“不是我故弄玄虚,过阵子你就知道这些家伙们的心理了。”
这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过来:“王仲军,你又在发表什么歪理邪说呢?”
几个人忙回过身来,中队长王仲军对正走过来的发话者说:“政委,我这是给小叶讲咱塔尔拉人的特色呢。”
政委刘新章哼了一声,笑道:“就你那些邪说,塔尔拉的特色都变味了。”
王仲军赶紧给叶纯子介绍:“小叶,这是支队刘政委,我们的直接首长。”
“什么首长不首长的,我是刘新章,是来这儿蹲点的。”刘新章对叶纯子说,“别听王仲军那些说法。小叶,你可是我们全支队都知道的‘名人’了,吕建疆到处宣传你,早把你描绘得大家心里都能刻画出你的模样了。这次你能来塔尔拉,可是我们塔尔拉的大事了!”
叶纯子听政委这样说,白了身旁的吕建疆一眼。
不知天色有点暗了,还是吕建疆故意装看不见,他没有理会叶纯子用目光的埋怨,却说:“政委是老塔尔拉人了,可以说他是塔尔拉中队的创始者了。”
“创始者算不上,但这个中队一组建,我就在这里,”刘新章有点感慨地说,“在塔尔拉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种感情是什么也取代不了的!”
刘新章这么一说,大家突然都沉默了。叶纯子一下子感觉到了这些军人一提到塔尔拉,神色都变得特别凝重,心里便想,看来塔尔拉还真不是个一般的地方呢。
还是刘新章打断了这短暂的沉默:“都愣着干什么,赶紧让小叶进房子里休息,坐了一天的车呢。”
把叶纯子让到中队部坐下后,中队长王仲军把吕建疆拉到外面的房子小声说:“老吕,你这家伙咋不事先打声招呼,她说来就来了,也没有准备准备。”
吕建疆说:“我也没有想到她会来,说来就来了,纯属‘突发事件’,也只好把图书室旁边的那间小屋收拾一下,将就将就了。”
“胡说,”王仲军瞪了吕建疆一眼,“人家可是天使,能降临咱塔尔拉,算是咱们塔尔拉的天大幸事,虽是‘突发事件’,咱可不能随便处置一下呀,怎么能说将就呢?”
说到这里,王仲军又压低嗓子说了一句:“我看这个叶纯子长得还真不赖,川妹子就是水灵,你可别错过这次机会呵!”
“你说什么呀,人家可是奔着塔尔拉来的,说是采什么风,你不知道呀,她可是个画画的,算是个艺术家了,你千万不要胡乱说话。”
“艺术家又咋了?塔尔拉的风多的是,随她采去,可塔尔拉的人也得采采的,人比风实在多了。你可要主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