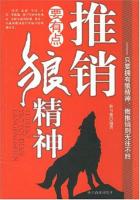在很多方面,他和侯为贵其实属于同一类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更有年轻人的冲劲,喜欢就事论事,管理中不留情面,对自己也不例外,比如,殷太太本来也在中兴工作,但后来他觉得这样不好,非让她离开不可。但侯为贵却重情得多,即便对犯错误的部下,也总不忍对其严惩。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膨胀,侯为贵越来越感觉到一种不好的现象:一个指令下达以后,周围的人却似乎没有听见一般,结果什么作用都没有。公司迫切需要改变这种局面。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他们都是南京人。在侯为贵的事业历程中,南京是非常重要的一站。1991年前后,当中兴的里程碑产品500门局用交换机的研发进入胶着状态时,正是南京邮电学院的一位资深专家—陈锡生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不但提供了大量的设计意见,还向侯为贵推荐了几名关键人才,其中就包括他的学生殷一民。在这之前,殷一民差一点成为北电在广东的一家合资公司的研发人员。陈锡生的另一名学生陈杰早些时候就已经加盟中兴,并且已经成为中兴研发方面的领军人物。数年后,南京成为中兴最大的研发基地之一,研发人员超过5 000人。
在中兴近15年的经历中,殷一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导师眼光独到。他很快便接替了因故出国的陈杰担任公司新的研发领军人,并在中兴2 000门交换机的研发中显露出一流的技术把握能力和不俗的执行力。2002年,当中兴的手机业务处于去留的关头时,他又主动请缨,成为手机业务负责人,并排除阻碍果断投入巨资兴建了工厂,这有利于更好地控制商业化速度和质量,从而在随后的两年中使手机成为中兴的主要业务。此前手机一直是侯为贵力主发展,但收效甚微的一个领域。
当侯为贵下定决心让公司从过去过度依赖自己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并慢慢培养它的独立能力时,殷一民便成为他试图建立距离感,但又不至于使局势失控的第一个支点。现在就看殷一民的了。侯为贵打算不再直接管理公司日常的运转,而是仅仅履行作为一个董事长的职责。
这就意味着,从殷一民成为“少帅”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必须直接承受中兴在通往新的目标道路上的所有压力。由于中兴在2004年成为中国第一家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公众公司, 它必须积极回应全球投资者的任何监督与质问,这又使他压力倍增。在这双重压力的作用下,殷一民可能会成为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公司新的目标和投资者的新预期都似乎没有考虑到2001~2003年的泡沫成分,而且人们很快便发现,公司必须为这期间对海外市场和WCDMA等主流技术的懈怠补交学费。
2004年,中兴的增长惯性仍然在延续,海外业务增长则达到了133%,中兴还在突尼斯开通了其在全球的第一个WCDMA试商用网络,从而使一直停滞不前的WCDMA商用化小有起色。但这样的增长结构明显已经是强弩之末,运营商在CDMA和小灵通上的投资如预期的一样开始减少,曾居功至伟的手机业务也受到国产手机整体步入衰退的影响。在之前的一年,中国本土的手机厂商凭借引进设计和广建渠道的方式,一度占据了国内市场的一半以上,但现在随着西方公司的成功反击,它们能获得的份额急剧下滑。
到2005年5月,“少帅”感到危机已到来。“订货额、发货、收款、合同毛利率和去年同期相比均有下降,而费用支出却上升很快。”他埋怨道。此时国内市场的萎缩超出了预期,如同占卜书上的预言成真一般,人们几乎在第一时间便将责任归结到了命运上。但殷一民并不相信这些,他坚持认为,“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外部环境发生了多大变化,而在于我们自己”,具体来说,是国际市场和战略产品的投入周期过长,以及公司自身的管理效率低下导致了这一局面。
殷一民的这一看法显然是对侯为贵观点的呼应。侯为贵在这年的“五一会议”上对公司执行力度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因为公司上下到那时仍然没能在国际化的战略上达成共识,虽然之前他已经不止一次谈到公司必须努力的方向,即通过对国家和运营商的全面覆盖来避免市场盲点,通过对重点国家和重点运营商的特别关注来提高市场的质量。但显然他的提议仅仅在殷一民等少数几个人那里得到了共鸣和执行。
“我们仍然缺乏必胜的信心,在一些国家进去了又出来了……我们比较长的时间都停留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大部分是非主流运营商,缺少勇气和毅力去面对难度比较大的基础工作,今天在这里我们应该好好总结总结。”侯为贵用少有的激烈言辞说道。
说实话,没有人知道这些“思想工作”起到了多少作用。那段时间很多中兴基层员工乃至部分管理层,对类似的言论已经习以为常了。很多人仍然没有完全从前几年的一派繁荣之中醒过来,一些人甚至认为高层有些危言耸听。
这种氛围注定了变革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为了使一切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自上任以来,殷一民便坚定地、一遍遍地要求部下执行他认为正确的指令。其中包括采取措施加强公司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通过增加通用件的比例来提高研发效率;加强新产品的投资;从产品和技术部门抽调人手前往国际市场组建售前和售后支持平台,以便加强对一线营销部门的支持和提高项目交付的速度;加快研发、生产等资源向全球的合理布局,在瑞典、法国、德国、美国等新增了多个研发中心,以加强对全球主流技术的跟踪,并支持当地的市场开拓;在非洲、印度等地兴建了数个工厂,实现当地生产。除此之外,公司还开始考虑将国内的研发生产基地转向西安等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城市,使资源向主流运营商客户集中等。
总之,殷一民希望尽快使公司变得能像全球企业一样思考和行动,这也是侯为贵梦寐以求的。他的努力甚至引起了美国《商业周刊》的关注,该周刊将他评为2005年的“亚洲之星”,认为他“具有强烈的市场危机意识”。但即便是此时的侯为贵本人,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每一个决策都能够得到完全的执行。在他长期奉行的温和主义、国内市场上的成功以及鼓励小团队利益的事业部制这三重刺激之下,中兴内部已经拥有不受他控制的生命。
很快,殷一民就遭受了挫折。过去,他一直关心公司能否签下足够的订单,但现在他突然意识到如何准时交付这些订单并保证有利可图才是最重要的。2004年的年报显示,中兴仍然有100亿元的合同没有执行,而这些合同大部分都来自国外,在这一年度中兴一共签下了16.4亿美元的合同,但只有约三成的订单得到了执行。虽然由于涉及一些跨年度的执行项目,简单的计算并不完全合理,但如果考虑到对手华为在同一标准上有约70%的海外订单执行率,中兴的交付能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如果不是这样,就可能是公司的海外员工虚构了很多从一开始就无法执行的合同。
“今年我们国际(市场)的各个国家,执行去年签订的合同是对大家诚信的一个考验,大家讲个故事签个合同,骗一下公司考核,那能解决多少问题吗?这样公司能够生存吗?”殷一民显然对出现这样的情况感到震惊,并且不再认为只是公司能力有待提高的问题,而是出现了更深层次的机能障碍。他发誓要改变绩效考核体系,并将海外的区域管理平台由原来的8个增加到14个,希望可以借此对所在市场实现精细化开发,实施更可靠的监控,甚至顶着压力将200多位被认为不称职的海外员工调回国内。
但尽管如此,这位以严厉著称的“少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虽然他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少帅”,但公司的高管团队一直都很稳定,大多数都和他年龄相当,而且在公司服务了差不多同样长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侯为贵的精神领袖的地位又是如此牢不可破,使殷一民的权威性也因此大打折扣。何况,侯为贵给公司留下的稳健文化已经根深蒂固,殷一民几乎不可能对公司进行任何伤筋动骨的大变革,那些小的改善措施就像春天的蒙蒙细雨飘洒在某所百年老校的围墙上,很难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最后,他自己也越来越成为侯为贵风格的一个复制版本。
如果说除了侯为贵之外还有什么力量在支持他的话,那可能就是中兴遭受某种突如其来的挫折了,虽然这也可能会是他在董事会面前的一次考验。在2005~2006年连续两年中,这样的机会真的来了。这期间中兴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停滞的打击。2005年,公司的收入仅增长了1.68%,为216亿元,如果不是海外收入增长了68.3%,结果会更糟糕!而竞争对手华为却增长了40%,为453亿元。两家公司的差距自2003年以后,再次扩大到一倍以上。
而在这之前的几年,就在中兴最红火的时候,华为总裁任正非一度因为在CDMA和小灵通领域错失良机而懊丧,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海外市场,现在却迎来了自己的收获季节。华为来自海外的收入第一次超过了国内市场,达到58%,而同期中兴却只有36%。如果考虑到海外收入的质量,则二者差距更大:华为的规模已经突破欧洲市场,其中获得英国电信21CN的优选供应商地位,成为其获得国际顶级运营商深度认可的标志;而中兴在欧洲几乎毫无斩获,更严重的是,公司大多数人好像根本不记得还有这样一个市场需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