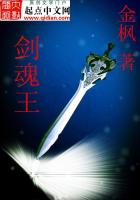旧历一年五次,正月初三(拜年),清明(扫墓),七月十五(施食),十月初一(送寒衣),忌日(忆别),我老伴要祭她的先母。早饭之后,擦净遗像前的柜面,摆四碗供品,行三鞠躬礼。她幼年丧父,为什么祭母而不祭父,为什么不劝我也照此规程行事,我没问过。在这样的名义大实际小的事情上,我们是既各行其是又互相尊重。各行其是,我可以不祭;互相尊重,行三鞠躬礼的时候,我就不好旁观或旁而不观。正面说,我也要立在遗像之前,行礼如仪。这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先说其影响之小者,是鞠躬前先要静听老伴的一番祷辞,总是这些:今天是什么什么日子,我和某某来给您上供,准备的有点心、水果、糖,……您慢慢吃吧!最后是言而兼行,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都完了,下解散令,“你愿意写就写去吧。”影响还有大的。邻居有一位刘奶奶,好说玩笑话,每次行祭礼,如果她看见,就要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言外之意,不过就是那么回事,活人眼目,可有可无。老伴口不反驳,心里不愿意,说这是把大事看轻了。这就使我更加不好办,因为我是连“心到神知”也不信。不信而静听祷辞,行礼如仪,说轻了是演戏,说重了是自欺欺人,总之是很难堪。难堪而不得不做,所以有时,尤其行礼如仪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如果我也真信,那会多好。
这使我想到一些说玄远就玄远说切身就切身的难以命名的问题。题目“难得糊涂”四字,是从七品芝麻官郑板桥那里借来的。他有解释,重点是“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意思是得过且过,不必过于认真。我觉得这是以俗讲传微言,大材小用了。何以这样说?说来话长。是1988年年初,母校北京大学准备纪念建校90周年,来约我写点什么。我左思右想,不幸就找了个“怀疑与信仰”的题目,想说说30年代初在红楼混了四年,“心”的方面走了什么样的路。主脑意思是,从母校学来怀疑精神,遇事想追根问底,可是也赞赏英国培根的话,“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但是惭愧,我只是始于怀疑,而未能终于信仰,尤其是背倚权威的一些信条,我多方勉励自己,结果还是“吾斯之未能信”。这里有什么傲慢吗?完全不是。如果说有,那有的只是无所归依的惶惑,或说烦恼。换为带有积极气氛的说法,是希望糊涂而“难得糊涂”。
因为有这样的烦恼和希望,多年以来,对于有些人,我曾多次泛起羡慕的心情。其中第一位是我的外祖母,那篇文章也曾提到。她坚信一种道门,以为她的善言善行必得善报。报大概有多种,我记得的只是,死后魂灵走往土地庙,小鬼和土地老爷都要客气,并起身让座云云。她活过古稀,作古了,其时我在外,推想瞑目之前一定是心安理得的。这就可证,坚信真就倒也得了善报。我呢,一失足念了些哲学的科学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以致不能信小鬼和土地老爷让座,更以致——,显然就不能不慨叹“难得糊涂”了。
再说一位,是一个同学的同事楚君,当年也相当熟。有那么一次,来看我,不知怎么话题一转,就陷入形而上。他充满善意地开导我,处世,对人,要记住五行的道理,“譬如你吧,一看就知道是木命,走路格登格登响。金克木,所以一定要躲金命的人,否则会吃大亏。”他的话使我很惊讶,但看他那既坚决又善意的表情,想说不信,没有勇气;顺情说好话,当面欺人,更难。我又一次感到“难得糊涂”。
再说一位,是邻居,女性,年岁比我大。推想是出自开明的高门,民国初年就走出家门到教会学校上学。我开始认识她是70年代中期,某某高位女士一手遮天的时候。有一天,这位女士到我们住的学校来,说了表示慰问的话,她见着我就赞叹,今天听见谁说了什么,感到太光荣了,太幸福了。我只好说“是”。不巧,过了不久,那位女士不能遮天了,她像是忘了过去,慷慨激昂地说:“天下竟有这样坏的,真该杀!”我只好再说一次“是”。其后,有时我想到她的有高度适应性的正义感,颇疑惑她有个或者只是心理上的神龛,龛长在而神可以顺应时势更易,所以获得的福报是永远身安和心安。我呢,比她吃粮食不少,竟不能置备这样一个神龛,以致即使想顶礼而不能得。烦恼,自怨自艾,无用,只好又慨叹“难得糊涂”。
再说一位,就信说也许是更值得赞叹的。比如相信天堂尽善尽美,不难建造,因而望见天颜就是最大的幸福,把己身放在天平上必重如泰山,等等。我呢,因为一直不知道有没有天堂,就不能获得望见天颜的幸福,放在天平上就轻于鸿毛。这有时使我想到利害和荣辱,因而又不能不慨叹“难得糊涂”。
羡慕别人的话说得太多了,应该转到正面,说说在哪类大事或小事上,自己苦于求糊涂而不得。想由道而器,说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天”。记得北欧哲学家斯宾挪莎有这么个想法,人的最高享受是知天(他多用上帝,这里以意会)。他写了一些很值得钦仰的书,推想他会自信,他知了,所以已经获得最高的享受。许多人,国产的,如汉人的阴阳五行,宋人的太极图,等等,进口的,如旧约的上帝创造一切,柏拉图的概念世界,等等,都是斯宾挪莎一路,幻想自己已经独得天地之奥秘。对比之下,康德就退让一些,他知道以我们的理性为武器,还有攻不下的堡垒。根据越无知越武断、越有知越谦虚的什么规律,现代人有了看远大的种种镜子,看近小的种种镜子,以及各种学和各种论,几乎是欲不谦虚而不能了。以爱因斯坦为例,自然的奥秘,他探得不少,可是常常慨叹,我们这个世界有规律,但何以会有规律,终归是个谜。他希望能明白,这值得同情,他承认他不明白,这值得钦佩。钦佩,赞叹三句两句,或三句五句,也就罢了。至于同情,就会引来麻烦。什么麻烦?这也许是我私有的,也许是一些人共有的。为了避免越俎,姑且算做自己私有的。
且不说以什么为根据,就“自己”或“我”说,人生,夭折也好,百年甚至更多也好,总是只能一次。生,不能无所求(为解说的减少头绪,限定合理的);因为种种条件的制约,求不能尽得。但也可能尽得;即使不能,还可以用祖传的秘方“知足常乐”来补救。只是有一点,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就是:我们活了一生,生确是“有”,生不能不向外延伸,这外也确是“有”,这总的“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大概是中了相信因果规律的毒,既然已经是“有”,为什么会“有”,总当有个原因,可是我们不知道。过去的多种猜测,我们不能信,能不能拿出个有确凿证据可以使人信服的什么来,以解望梅之渴?看来,至少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办不到。那么,奔波劳碌一生,自己忝为“有”的一部分,对于“有”是怎么回事,终于不能知道,撒手而去,想起来就不能不感到“太遗憾了”。说遗憾也许还太轻,应该说“苦闷”,或“苦”,即使只是知识方面的。由利害的角度看,上策显然是不求知,但那要走回头路,又是不可能的。这就使我有时候深深地慨叹,“难得糊涂!”
二是关于“人”。我是常人,跟一切常人一样,糊里糊涂地有了“生”。生之前,以至可推想为已有而尚未凝聚为“我”的时候,情况不好说,只好不说。专说有了“我”之后,既已接受(假定有此一着)了生,其他随着来的种种就只好顺受。《礼记·中庸》开头说了几句重要的话。“天命之谓性”,我们只好饮食男女;“率性之谓道”,我们只好柴米油盐,并以余力而琴棋书画,等等。这其间,循不知从何而来,以及应如何正名的什么什么规律,我们不得不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最终是医治无效,享年若干云云。由“有了生”到“享年若干”,中间这段路,至少戴着主观的眼镜看,是不短的,或颇长的,或很长的。长,比如是个空的长廊,其中要放一些或很多乱七八糟的,由即位加冕到偶然低头拾得一分钱是一类,由挤车丢个纽扣到走向刑场是另一类。
为了这里的问题容易说清楚,扔开不可意的后一类,那就只剩下可意的,古人有三多九如之说,今人更多,因为古人虽能化蝶而不会贴胸跳舞,可卧游而没有家用电器。太多,只好减缩,说一般有群众基础的,那就是,饮食,吃过红烧肉和烤白薯,男女,生了也许不只一个,都教养成人,此外还可以有立德、立功、立言,等等,可谓懿欤盛哉。问题是,一旦将撒手而去,如果不能如莲社诸公的相信即将往生净土,就不免要反躬自问: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答复可以因人而异。我的认识,满意的答复是没有的,唯一的上策是“不问”。我不幸,常常想问问。这就有如不慎陷入泥塘,既已陷入,挣扎上来就大不易了。不得已,可以自制一种安慰药,曰“自欺”,其疗效是把不见得有什么意思的看做有意思,或大有意思。但这很不容易,不能像“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那样轻易而有把握。可惜的是,不识不知已经离我很远,但又不能不顺帝之则,其结果就成为既大吃羊肉串又大喊没味儿,可笑亦复可怜。这也是苦恼,而且是长期伴随的,所以每一想到,就不能不慨叹“难得糊涂”。
三是关于“时”。时的所指不是时间,是苏东坡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时宜”。这就根柢说没有前两种那么深,却表现得更加尖锐而鲜明,因为尖锐,明说多说就不合适。只好由感受方面略加点染,是我感到惭愧,而且很深重,所以痛心。惭愧什么?是孟老夫子说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我知之而未能行。具体说,是为了能活,我说过顺应时风的假话。由这引来的痛心有等级之差,依不成文法的规定,面对众人,背诵制艺,不动心,听者半数得意,半数谅解,根据吾乡某小学生“惯了一样”的生活哲学,自己也可以不求甚解。
但情况并不都是这样,比如有一次,我就先则很狼狈,继则很痛心。是70年代中期,一位老友,由于关心我的德业和安危,敦劝我应该如何如何。我表示谨受教并述感激之意。他看看我,说:“看你的表情,话不是出自本心。”我只得用更假的话应付过去。其实不能说是“过去”,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其时是在江南。以后我们没再见面,来往信有一些,当然不便提这类事。1988年炎夏,他作古了,接到讣告,我想到终于没有告诉他那次正如他所推断,是假话,心里立即泛起双重的悲哀。人往矣,我有时想到他的善意,就不禁慨叹,当时如果能够信他之所信,皆大欢喜,那该多好。可惜已然的不能变为未然,现在,除了默念几句“难得糊涂”之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到此,有的人也许会想,我是悔恨受了读书的毒害,所以变闲话为诉苦了。也不尽然,因为书上的话,也有增益另一种智慧的,如下面两则就是。抄出,供同病参考。依时风,先外后中。
(1)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神)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旧约·创世记》)
(2)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这两则,我不只看过,而且深有同感,牢记在心。那么,良药为什么没有利于病呢?我想,坏就坏在“知”是个淘气鬼,你有七窍,任它钻进来,它就会胡闹,不听话,并且不计利害,到你有“知”,计利害,想逐客的时候,已经做不到了。做不到,而又忘不掉。除了慨叹“难得糊涂”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