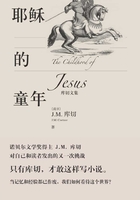那医生抽完第四支烟,随手把烟头向空中一弹,伸了个懒腰,打开沉重的安全门进去了。郁光呆呆地站着,脑子像生了锈一样,突然那扇安全门又打开来,医生在半开的门扉里看着他,说了一句:“相信年轻,年轻的比较顽强。”
回到走廊等候处,阿川还是坐在那个位置,郁光走近一看,那家伙竟然睡着了,郁光在附近找了张椅子坐下来,这一天一夜可真够受的。
怎么会?怎么会是石音?那么温和,善体人意而又富有牺牲精神的一个人,会遭到这种飞来横祸?如果不是要来参加画展的酒会,呆在家里就应该没事吧。但是阿川不去那个见鬼的加油站会没事吧?话再说回来,他如果早去十分钟或晚去十分钟都会避过那件倒霉的事吧。这样不行,推算下去没完没了,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个人又都没责任。美国人有句话叫做“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两个错误一凑合就撞上鬼了。中国人说得更为透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的,我们都是鼠目寸光,以为这个世界是恒久不变的,天地万物为我而设。直到有一天警钟在耳边敲响才醒过来,原来世事一夕之间就可颠倒过来,生命脆弱得如根稻草,碰到一点火星就可烧成灰烬。
人真是那么经不起事,歹徒为了几十块钱,可以轻易地毁了一个人的生命,毁了一个刚刚起步的家庭,给一大批亲朋好友造成伤痛。美国的法制那么健全,可警察拿歹徒差不多就没办法,抓住了也是牢里蹲几年就出来了,照样作恶。可是失去的生命再也不能重生,伤痛也永远不会平复。
什么都别去想,石音能够度过这一关最重要,只要石音能好起来,阿川和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的。可是,这一切由你吗?
医院的气氛特别压抑,郁光的眼皮也逐渐沉重,就在他刚要迷糊过去之时,恍惚间听到护士在走廊上喊“谁是石女士的家属?”一个激灵跳了起来,摇醒阿川。两人脸色发白地冲到护士面前,阿川抖得上下牙齿哒哒发响,那护士看了他们一眼,说:“你们是家属?病人想见见你们,跟我来。”阿川还是紧张得移不动脚步,也开不了口。郁光鼓起胆子问道:“请问病人情况怎么了?”护士说:“刚从麻醉中醒了过来。”郁光说:“那就是说好起来了?”护士说:“我没这么说,她的情况还是很严重,你们在里面不能多耽搁。”到了门口,阿川拖住郁光:“郁光,我很害怕,我怕我会在里面昏过去,要不,你先进去看看?”
郁光道:“胡说什么!越是在这种时刻,你越要表现出坚强来,石音想见的是你。等会进去之后,千万要稳住神,告诉她会好起来的,任何事情都能挺得过去的。记住,你如果垮了,石音增加了精神负担,那样对她伤情不利的。”
他们跟着护士进了加重看护病房,三张床位都躺了病人,石英在靠最里边的一张床上,护士领他们走到床边,床边的吊杆上挂着大袋的血浆,石音的脸色苍白得吓人,对他们微笑了一下,却说不出话来。阿川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郁光真怕他随时会倒下去。所以一手扶着他的腰间,一面对石音道:“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配合治疗,什么也不要担心,外面有阿川和我,一切都会处理好的。阿川你说是吗?”阿川只会点头,半天迸出一句:“急死我了。”郁光的手在他腰上撸了一把,阿川才期期艾艾地说:“好好养伤,想吃什么我去买。”郁光想这小子真不会说话,石音现在是能吃东西的样子嘛?石音的嘴唇动了一动,两人一起低下头来,听到很微弱的声音问道:“画展开得成功吗?”郁光眼泪都要下来了,连忙说:“成功,卖掉好多画。等你好起来我们一起庆祝。”石音点点头,眼皮子却不由自主地沉下去。护士过来说你们得走了,她太虚弱,不能一直说下去。
两人走出病房,都是一身大汗。一抬腕,竟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郁光叫阿川去吃点东西,睡几个钟头。晚上再来替他。阿川说不放心。郁光道:“你再倒了我就没法同时看顾你们两个。快去,把烟留给我,有任何情况我会通知你。”
阿川走后,郁光除了去楼梯口抽烟,就是把头抵在玻璃窗上,呆呆地看着底下的停车场,像甲虫似的汽车进去又出来,间或有辆救护车急驶进来,后车门一开,两个担架员抬下一具动也不动的躯体来,匆匆地推进急诊室。生命之火,在这幢水泥房子里或被煽旺,或者就此熄灭。郁光突然想到有一天自己如果这样被救护车送进来,躺在病床上被插满管子,苟延残喘,那怎么办?脑子里马上否定:那种样子情愿不要活了,生命中如果没有画画,没有冲浪,没有女人,也没有自由意志。那种生命还有什么意思。
继而又悲哀地想到,石音不是被陷入这个地步了吗?多好的一个女人。
晚上阿川来换他,石音的表姐也来了,郁光离开之前和他们一起去值班台询问石音的病情,被告知还在观察期。郁光勉强开车回家,一路上眼皮不住地打架,差不多两天了没合过眼。到了家里,冲了个澡躺下。电话又响了,本想拔掉电话线,又怕是阿川打来,接起来听到的是哭声,他浑身一激灵,汗毛都竖起:石音怎么了?再仔细一听是个女人的哭声,娜塔莎。发昏的脑子才转过来:“嗨,娜佳,怎么了?”
娜塔莎情急之下冒出一串俄语,郁光从没见到她这样,在电话中安慰了好一阵,娜塔莎才控制住号哭,在那儿抽泣。郁光说:“娜佳,发生什么事了?你安静一下,慢慢说,或者你要我过去?”
娜塔莎鼻音很重地说:“不要过来,他们杀死他了。”
“谁?”
“提米却。”
郁光大吃一惊,话筒也掉在地上,捡起来之后他问道:“你确定?你怎么会知道?”
娜塔莎说她近几个礼拜一直在想法还钱,已经通过鲁迪还了一万多,但是还够不上利息数。前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威胁说是最后期限了,不本利还请他们就要最终解决了。娜塔莎到处找人,但根本凑不够那个数目。直到今天,一个信封塞在她的门缝底下,里面是……
“你怎么不找我?”郁光的脑子乱得一团糟。
“我打了好几次,一直没人接。我开车去你家,半路上又打消了主意。”
“为什么?”郁光才想起那天他和萨拉一起出去买酒会穿的衣服了,“别管这些了,现在情况到底怎么了?”
娜塔莎在电话里很响地擤了几次鼻子,过后说:“他死了。”
“你确定?”
娜塔莎说信封里是份《洛杉矶时报》的剪报,说警察在东边的蓄水库里发现一具尸体,男性白人,二十七八岁,死因不明,但警方消息说在尸体上有拷打的痕迹。
“那你也不能确定一定是他。洛杉矶每天都发生谋杀案,帮派分子互相杀来杀去,你没见到尸体就凭一份剪报吓自己。”
娜塔莎闷声道:“我有感觉的,不会错。”
郁光无语,说:“我还是过去看你吧。”娜塔莎坚决说不要,好说歹说,最后她同意在晚上上班之前,和郁光在大象咖啡馆见面。
挂了电话,郁光浑身骨头像被抽掉似的,一屁股倒在沙发上,天啊。这个世界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多事情都发生在今天,为什么阳光灿烂的洛杉矶看起来满目疮痍,为什么命运喜欢对人开如此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