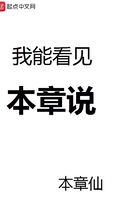阿川在门前的车道上催石音:“要赶快了,郁光说酒会八点开始,现在已经八点二十五分了,我还要去加油。”
石音好容易才穿戴停当,在经过客厅的镜子前又停下来整理鬓发,一面问阿川:“我这样子还过得去吗?不会显得太随便吧。”
阿川穿了一条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翻毛麂皮鞋,上身是灰色的运动西装。说:“我说老婆,你又不是第一次认识郁光,一个画展弄得这么紧张。说不定他自己穿了那套脏兮兮的工作服跑去酒会,这小子做得出来的。”
石音对着镜子涂最后一遍口红:“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们两个平时再脏乱再邋遢我都不管,但这上场面的时刻我们可不能给郁光丢面子。好歹这是他第一个正式的画展,他不在意,还有来宾呢。郁光指望这些人来买他的画,两个叫花子晃来晃去多煞风景。”
“艺术家在你们眼里就是叫花子?”
“你又没在额头上写着字:我是艺术家。人家来买画,付了钱也要个心情舒畅,我们穿得得体一些也是对人的尊重。”
“啊呀,老婆你有完没完?我不是照你说的,把最好的出客衣服都穿上了嘛。这运动西装肩膀吊得紧紧的,抬手都牵住,怎么运动?”
两人上了车,阿川过了两个加油站都没停下来,石音问道:“你不是要加油吗?等会趴在路上又是耽误时间。”阿川说:“再过去有个艾科加油站,每加仑要比这儿便宜上一毛钱。反正顺路,耽误不了几分钟的。”
再开了几个街口,阿川说的艾科油站到了,他把车拐进去,停好,打开车门出来先去收银处交钱。再回来把油嘴插进油箱。这儿临近134号高速公路,在圣塔安的边缘,属于蓝领工人的聚居区,安静而简朴,入夜之后很少有人车行驶。阿川装修房子时常去附近的家居仓库买材料,所以知道这个地区有个廉价油站。
在他对面的加油筒前停下一辆车子,却没熄火,车门一开,出来四个墨西哥年轻人,穿了一样的深色衣服,头上戴了滑雪软帽。两个走去收银处,两个就留在车旁。
过了一会,收银处那儿传来一阵争执的声浪,有人大声地呲斥,阿川向那边望去,天黑看不清楚。他心中感到些什么不对,回头望望油筒计价表,还有三块多钱就完了。正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石音的叫喊:“你要做什么?”急回头一看,刚才在车边两个墨西哥年轻人不知什么时候蹿到他们车子旁边,其中一个正从车窗里扯出石音的皮包。石音发觉了正在和他撕抢,阿川想也没想,一个虎跃扑了过去,撞在那人身上,两人都倒在地上。那人个子很壮实,一个翻身就把阿川压到底下,阿川从小会打架,乘那人再一次压下来之时,抡圆了手肘狠狠一记扫在那人下巴骨上。
只听一声闷响,然后是沉重的身体倒地的声响。阿川赶快起身,看着那家伙倒在地上打滚,另一个蹲在一边手足无措。一个念头在他脑里:赶快走,在他们同伙赶来之前赶快走。眼睛却斜见几尺之外落着石音的挎包。他犹豫一下,还是跑去捡了起来。直起腰,就见到几个人影从收银处奔来,他一步跳进车里,打着火就走,却没想到加油管还没取下,车子被拖住了。阿川猛加了一下油门,车子向前一蹿,加油管被扯下来了,车子飞速地离开加油站,只听到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叫声,那拖在车后加油管的拖曳在地的声响,汽车逆火的爆响,还有后面那批人用西班牙话大声叫骂。
开出十来个街口阿川才缓过神来,背上一身冷汗,那件绷得太紧的运动西装腋下都裂开了。他刚想说老婆你看这运动西装这么经不起运动。突然想起自从跳进车子没听见石音说过一句话,转头看去,石音头靠在车门上,好像睡着的样子。心中不禁起疑,伸手摇摇石音,竟然没反应,这下把他吓了一跳,赶紧找个光亮处停下,俯身过去查看石音,从他这边看不出什么,石音睁开眼睛朝他看了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阿川心中大骇,走出车子,绕到乘客座,才打开车门,石音就滑了出来,阿川赶紧扶住,他一眼看到石音的右背部已经被鲜血染透了。
灯光下石音背上的血迹看起来是黑色的,阿川脑中一片空白,心脏好像凝结了,反应过来先是跑去路边,向过往的车子挥手求援,但没一辆车子停下来。然后他再跑回车旁,扶起石音,想为她止血,但一时又看不到伤口在哪里。石音短暂地苏醒了一下,叫疼,说阿川我怎么了?阿川说你受伤了。石音道那赶快去医院啊。一句话提醒六神无主的阿川,他把运动西装脱下来,垫在石音的腰上,又跃进车里,飞速地拐上134高速公路,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医学院急驶而去。
凌晨被郁光牵着手带出画展时,心中一无所思,一无所想。像梦游似的,时空突然变得无限拉长,她一恍然就穿过千百年时间,月升日落,世界本是不分昨日今天明朝的,远古荒蛮,繁荣当今,就像睡眠和苏醒一样,都是一瞬间的恍神而已。在她身边这个男人是谁?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只觉得和他在一起万分安全,就是去地狱也会安全的。
男人把她引到一辆车旁,打开门,扶她坐了进去。那车座位很低,凌晨觉得就像是直接坐在地上似的。但没关系,这一切都是幻觉,今晚她不该喝那杯香槟的。但那个男人蹲了下来,伸手替她系上安全带。再把门关上,然后才坐进车里启动引擎,前面穿制服的车僮举起一只手来致意,然后快速地闪到一旁,换了个中指伸出的手势,因为突然蹿出去的保时捷差点就撞上他。
郁光根本没察觉他差点撞了人,他只有百分之十的注意力在驾车上,其余的都在凌晨身上。在车里两人很少说话,各自保持着一种出神的状态。郁光原本是想送她回家的,但车子却背道而驰,沿着十号公路,又拐上沿海的一号公路,来到圣塔莫尼卡的海边,在空寂无人的海边停了下来。
他常来这儿冲浪,熟悉这儿的每一片沙滩,每一块礁石,却从未在深夜十二点之际来过这儿。海面平静无波,与伸展出去的沙滩连成一线,偶尔有人慢跑而过,高悬在天穹上的月亮很小,亮得晃眼。月色在水面上形成一片闪跃的光斑,空气很清新,虽然是夜晚,也可以看到很远的海面,极远处有一艘大型货船,像个淡淡的影子在无声地滑行。身后的一号公路上的交通灯号时红时绿,夜归的车流疾驶而过。
凌晨静静地坐在旁边,看到郁光摇下车窗,点燃香烟。低头在包里找出一支大麻,用口水粘了粘,问郁光要打火机,郁光诧异地看着她,却没有发问,只是凑身把打着的火递到大麻烟上,凌晨低头就火,一面抓住郁光的手腕,很贪婪地深吸一口,眯起眼睛,慢慢地吐出烟雾,然后突然醒来似的,把燃着的大麻递给郁光。郁光这是第一次抽大麻,但他想都没想就接过来,学凌晨样子深吸一口,屏住气,让大麻在周身过一遍,然后才让烟雾徐徐地吐出来。两人互相传递着,轮流吸着沾了对方口水的大麻,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凌晨在抽完大麻之后短暂地迷糊了一会,郁光轻手轻脚地为她放平椅子,在微弱的天光下,凌晨的脸容显得格外苍白,像一张记忆中的工笔白描。日月如水流淌,这张脸庞却一直搁浅在他生命的某处,他曾努力忘却他俩做过一段夫妇这个事实,但记忆一次次地回来,像水蛭似的依附,搅乱他的心境。如今这张脸庞就在他尺咫之遥,倦极而眠。而他,就像被定身法定住似的,眼光一刻也不能从那张脸上移去。
他看看腕表,已过深夜二点,背后公路上的车流开始稀落。云层遮蔽了月亮,夜色转为深浓。郁光推开车门,站在防波堤上向远处眺望,海岸线的灯光散散落落地明灭闪耀,远处的海面起了雾,淡淡的,掩了过来,恍然如梦中无可寻觅的失落。
他来了美国也有好几年了,当年刚踏上这片土地时,能在有规模的画廊里开画展是每个画画人的梦想,今天,这扇门在他面前徐徐打开,门后有着无数的附加物,名声和尊敬,财富与舒适。好莱坞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赞美才能,崇尚成功,你只要跨越那扇门后,就此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多少人像鲤鱼跃龙门那样,在这道门之前撞得头破血流,还是不得其门而入,他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家伙。
然而,他并不快乐。
成功像条在水面下时隐时现的鱼儿,倏或闪现,随即而逝。你在岸上,知道有“成功”这条鱼在水里,你必须跳入水里才能捕捉得到。于是奋身一跃,到了水下却见一条鲨鱼张了血盆大口迎面而来,你闪避,你搏斗,你逃遁,你绷紧全身神经对付左一下右一下的攻击,你在最后捕获或将要捕获这条快乐的鱼儿时,你自己也近乎虚脱。如果此时有时间问问自己的话,捕捉这条成功的鱼儿究竟对人生有多大意义?
但是我们没有选择。自从踏上这块土地,我们就被一种无形的压力逼迫着,你不是抱怨在中国不能一展所长嘛?你不是觉得个人才能被强大的世俗所压迫嘛?你不是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以致不能专心画出最好的画来嘛?好,你远渡重洋,来到这块创作绝对自由的国土,你的将来在你自己手中,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具备了,应该没有再抱怨的口实了吧!那好,是驴是马牵出来遛遛,你如果在这块土地上不能成功,那你就是走遍世界也不会找到那块成功之地的。别找借口了……
如果说成功并不带来快乐也不尽然,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装上金碧辉煌的镜框,配上照明良好的灯光,被安置在一个高雅的场合,各色人等穿上正式服装赶来观看你的作品,而且为此庆祝,开派对,互相祝酒。还有看到价目表上一个个小红点,代表了有人愿意掏口袋,以五位数的支票来承认你的工作。且不管他们是否真懂得你的作品,但是他们总算是个流通的窗口,你的心血之作有一天会流向真正欣赏,懂得的人面前。你将被期待,希望你能画出更好的作品来使人惊艳,使人折服,使人珍藏。而这些都是动力,人是需要在外界回馈中取得信心和鼓励的,说到底,我们都是凡人,而凡人总是软弱的,比我们自己所想象的更为软弱,不管你头上闪耀着什么样的光环。
你低头看手掌,一恍然之间,快乐就如捧在手心里的一掬清水,从指缝间泄漏贻尽。你再也恢复不到不对所有人负责,只由自己心境带领的状态,你接过无形的担子,背负着别人的期望,你再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自己,各种潜在的需求像一张网似的罩了上来,开始还不觉得,还在沾沾自喜中飘浮,很快就觉得步履维艰,那条路越走越窄,越走越艰难了。
快乐,是另一条鱼儿,把握不定,出没无常,来了就来了,一旦离开,难觅踪影。
不但是你,郁光,你周围的人都不快乐,娜塔莎为了老公的赌瘾深受折磨,提米却抱怨老天不眷顾他的疯狂妄想,萨拉住在一幢空荡荡的衰败大房子里,卡洛琳睡在画廊的地板上,奇奇为了卖画极尽逢迎拍马之能,阿川和石音为了能有个家节约每一个铜板。而那个你最在乎的女人,为了她的快乐,你咬牙离婚成全,但是一见面你就知道她并不快乐,还在为失眠而苦。离婚不对,写作也不对,什么都不对,什么都白费了。
快乐像睡眠一样,只能从自身而来,任何外界的代替物全然没用。
郁光走回车子,发觉凌晨睁眼看着他,虚弱地说:“你送我回家吧。”
在深夜空寂无人的十号公路上,郁光把保时捷的油门踩到底,车速已达一百多英里,他却浑然不觉,脑中盘旋着一个问号:阿川,这家伙怎么会放了记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