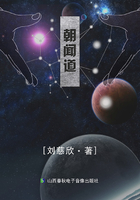凌晨早上梳头时,突然发现在浓密的黑发中有一根长长的白头发。
才二十八岁,白头发也来了太早了点。家族里应该没有早生华发的遗传,凌晨记得七十多岁的祖母还是一头乌亮的头发,梳成一髻紧紧地盘在脑后。父母也没有白头发,在经历那场变故之后,父亲变得暴躁和易怒,抽很多的烟。母亲的整个形容枯槁下去,头发变得稀薄,但也不见明显的白发。她这根白头发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一个无从回答的问题,也许就像一个循规蹈矩的家庭会出叛逆的儿子,一对乌不溜秋的夫妇会生下一个白化儿一样。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着变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
凌晨猜想这根白头发多多少少跟她的睡眠有关,从三年前起,她的睡眠就薄得像纸一样,十二点钟躺上床,半夜二点钟就醒了过来,翻来覆去就再也睡不着。眼看着晨光像水一样漫进房间,而太阳穴上的一根血管像打鼓一样跳动。再过一个小时,睡在客厅里的郁光会醒来,厨房里传来煮咖啡的味道,早起晨运的人在窗下跑过,报纸啪地扔进门廊,再下来各种城市的喧嚣声音腾起,白天强横地挤进来了。
凌晨不能忍受和别人一起分享黑夜,在结婚的第二个礼拜就让郁光抱了铺盖去客厅里睡,郁光虽然不愿意,但还是按照她的意思做了。他心疼老婆每天早上起来苍白着一张脸,与其整晚屏息凝神地躺在床上连手脚都不敢舒展,生怕惊扰了凌晨浅浅的睡眠。还不如独自睡在沙发上,至少可以睡个囫囵觉。
凌晨二十岁以前也睡得像块石头一样,就是这二、三年的事,睡眠突然变得滑不溜手,每天晚上躺下去时,凌晨都不知道今晚会是有几个钟头的睡眠呢还是一夜辗转到天亮。偶尔跟人谈起睡眠的话题,都说年轻人应该是不会有失眠的问题,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睡不着觉,但老年人也不需要太多的睡眠。
凌晨听了这话淡然一笑,人的年纪真的从她出生那时开始计算嘛?
在她十五六岁时,所住的大院来了一个异人,自称得到密宗高人的点拨开了天眼,能往前往后看人的三辈子。大院里的妯娌姑婆,大姑娘小媳妇一窝蜂地要那人看相,凌晨只是好奇张望了一下,不想就被那人叫住,说要给她算前世今生。凌晨哪信这些,更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胡诌一通,于是坚决地摇头,却被身后的七姑八婆抓住手掌,送到那个江湖术士面前。那人凝神一瞥,突然好像受到震惊似的抬首望向凌晨,又低下头去沉吟不语。旁边的人一叠声地问这个小姑娘的命如何?那人只是支吾以对。凌晨本来就不要听这些神怪之说,乘机挤出人群回家去了。
第二天上学去的路上看到那人在大院门口抽烟,见她走过就招手。凌晨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昂首走了过去。那人却跟了上来,凌晨怕被人看见,就立定脚步问他到底要做什么?那人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站定,一脸诚恳地说:“小妹妹,我要告诉你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凌晨跺脚道:“我不要听。”那人无奈,当凌晨走过他身边时突然道:
“我就告诉你三个字‘老灵魂’,你是一个非常老的灵魂来世上历劫的……”
这当然是胡话,但这句江湖术士的胡话隔了十一年又浮了出来,就如从阴暗角落里飞出的一只老蝙蝠,在一个清光弥漫的早上撞进她的思绪。人真是有灵魂的吗?在这么多年的世事经历之后,凌晨现在不敢说绝对的语句。如果真的有灵魂的话,那灵魂也就应该分老灵魂,或年轻的灵魂,沉重的灵魂或轻飘的灵魂……
也许这就是白头发的解释,凌晨掂着手中那根拔下来的头发:灵魂在某些不为人知的地方也会显出本相来的。相士说她是来世上历劫的,那十一年来几劫几历过了?
现在想起来天下所有的相士都是乌鸦嘴,好事从不兑现,坏事一说一个准。
家里是突然出事的,凌晨是在一夜之间发现家里的气氛变得像冰一样。父亲关在房间里不停地抽烟,隔着房门听到茶杯摔在地上碎裂的声音,偶尔撞上了只见他脖子上一根青筋扑扑乱跳,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以前那么有主见的母亲变得形容枯槁目光躲闪,常常一个人发怔,有时跟她说话明显地前言不搭后语,凌晨注意到母亲常常做事做到一半停下来,绞着双手,眼神望进一片虚无之中。
事情早在大院里传得纷纷扬扬,凌晨不想听也会灌进她耳朵来:在师范学院教书的母亲竟然姘上了一个比她小十来岁的英俊电工,要命的是两人在电工房里成其好事时被人撞破。学院看在母亲是优秀教师的面上准备处理那个电工,母亲却站出来说是她自己愿意的。大家都傻了眼,同事们只会摇头,嘴碎的,心里憋气的,有过节的,在背后传的话就非常不堪了:你不是党员吗,你不是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吗,你不是大家口中的贤妻良母吗,怎么一转眼就裤带掉下来了?
事情传到大院来更是一塌糊涂,婆婆妈妈们唯一可以自夸的就是裤带紧,突然有个高高在上的人在她们面前摔了个四脚朝天,怎么不使她们兴奋莫名而口舌生津,女人偏偏在这方面的想象力最为活跃,一件已经证实的事情可以引申出无数件只有怀疑但无法确定的事,这样一来所有的蛛丝马迹全都坐实了。凌晨母亲走在大院里可以感到从一扇扇窗子里射出来不屑的目光,在墙角里窃窃私语的干瘪姑嫂们见了她就闭上嘴,挤出一个暧昧的假笑。凌晨母亲虽然挺直腰背走过去,但时间一久,那种阴毒的,黄梅雨季般的潮气钻进骨髓里,再自信的肩膀也会耷拉下来。
凌晨母亲搬出大院,凌晨父女还是被流言蜚语所包围,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隔绝起来。父亲热衷于出差,身为学院图书馆馆长的他为了进一本书可以去边远的地方半个月,那是任何一个小职员都可以胜任的事。凌晨知道他是为了眼不见心不烦,这个家实在是没什么好留恋的。
父亲一走,凌晨买回一大堆方便面,关起门来谁都不见。拉上窗帘躲在床上看书,家里有三个大书橱放满了各个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大部分连邮包纸都没拆封。在阴雨绵绵的黄昏捧了一本海明威的《战地钟声》躺在被窝里,凌晨一晚上可以看完四百页的一部小说。在十九岁之前,凌晨读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托马斯·曼的作品,罗曼·罗兰的人物传记,川端康成的“四季”,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所有能找到的纳博科夫,张爱玲。
所有的书籍都是毒药,所有你咀嚼过的文字都一点一滴地浸透你的神经,所有被宣泄的情绪都被你全盘接受下来,任何不成熟的思想由于已被印成文字,所以自有一种权威,你无法向一个躲在文字后面的叙述者挑战。要么臣服,要么离开。
凌晨没有可能离开书本,在那一段恍惚的日子,书本是她唯一通向外部世界的途径。大院里的人一个个面目可憎,心思恶毒,语言闪烁。家里也只是徒有四壁,父亲这辈子可能恢复不过来了,他并不掩饰一个失意男人的颓唐,脾气暴躁,言语刻薄,这世界上唯小人与女子难养矣。他没想到女儿也是女子,女儿的年纪正处在或接受或排斥的阶段,十几岁的女孩子性情在他不经意的唠叨中逐渐垒起一道男人永远无法逾越的壁垒。
灰暗的现实中唯有书本,书本中阐述的是一个另外的世界,一个似曾相识的世界,跟我们乌七八糟的现实世界平行但又不关联的一个世界。书中当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所有的缺失都在书中升华到悲剧的境界,所有的不如意都化为诗意的惆怅和无奈。花开花落都有起转承伏,没有结果也是结果。而现实中只有一片厚重穿不透的黑暗。
大院的人们平时很少看到凌晨,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出来散下步,透透新鲜空气,在月光底下的少女脸色洁白如纸,带着一股梦游的神情。但是没人能看到她眼睛里的光芒,睿智,孤独,冷漠,桀骜不驯,像一缕暗燃的火焰,又像水一样转瞬即逝。
偶尔她会去看望母亲,母亲从大院里搬出来之后借了一间小房居住。离婚的手续僵在法院,双方都不起劲,两年多来就保持在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每次走在去母亲的住处的路上时心里总有点混合着怜悯的亲情,一进那昏暗的小房间批评的眼光就淹没了所有的同情,就如一种自己也抑制不住的生理反应。看到母亲佝偻着背脊,在不到十平方的房间里无所目的地忙来忙去。失神的眼睛空洞茫然,同时不断地说话,所言之事全是鸡毛蒜皮的琐碎。难道这就是当年凌晨记忆里的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女子,对自己的外貌和学识充满了信心,在讲台上妙语如珠,在台下也广受欢迎的优秀教师?那个在事业上野心勃勃,在人际关系上长袖善舞的聪慧女子,就为了一段不伦之恋沉陷到如此地步?
女人是脆弱的,男人摔倒还可以爬起来,女人一脚踏空换来的可能就是万劫不覆。
女人最碰不得的是感情,不管你是如何的聪明坚强,不管你是如何的刀枪不入,一踏进那片误区,很少有不是遍体鳞伤出来的。那个电工不是结婚了吗,像鸭子抖掉身上的雨水,什么事也没有,说不定还为风流往事沾沾自喜呢。可母亲,就这么一个坎,摔倒了就完全不是以前的模样了。
凌晨走在春天的大街上,牙齿咬着下嘴唇,自己对自己说:绝不,我今后一生中绝不向任何的感情低头,母亲就是最好的一个教训。
女儿在人生中第一个楷模总是生她养她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