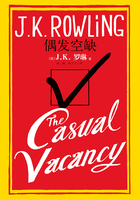杜大爷先是讲神州东边大海里的扶桑树,接着又讲上面两段历史公案,把在座诸人讲得一头雾水。
齐明刀听着听着,忽然想起秀水在董五娘的瓷魂铺鉴别青花瓷时,看到高士图和三友图时,不说那画极富国画意味,而说那画极富中国画意味。说到龙纹广口瓶时,不说国内已没有元青花龙纹广口瓶了,而是说中国已经没有元青花龙纹广口瓶了。齐明刀当时心中虽有些异样的感觉,但终究没有深思。但今日听杜大爷这么一讲,那种异样的感觉又泛上来。再看看秀水平常所用的东西,再细看看秀水稀疏的山羊胡须,齐明刀愈发觉得秀水像个日本人。
杜大爷又说话了:“人的名字,就像牌九一样,洗一遍,便重新组合一遍。譬如秀水先生的名字,不洗叫秀水,洗一遍叫明山秀水,再洗一遍叫菊池秀水,洗三遍就叫铃木秀水。”
秀水一直低着头,听杜大爷这样说,知道身份无法隐瞒下去,便抬头看杜大爷。杜大爷也在看他。那目光和身上释放的古气将秀水浓浓地包围住。
“杜大爷不愧为长安城第一高手,看古董的眼力过人,看人的眼力更是了得。我的确是日本人。”
在座诸人颇觉意外,齐明刀猛地想起小克鼎刚摆上桌面时,唐二爷和杜大爷的小声对话:器物深广,寻常绳尺难以测量。你说鼎哩还是说人哩。
董五娘似乎也想起了那天在瓷魂铺里的情形,有些急切地问:“你到底是菊池秀水,还是铃木秀水?”
秀水缓慢地摇摇头,深深叹息着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也许是菊池秀水,也许是铃木秀水,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秀水的话,又让大家堕入云雾之中。
杜大爷又开始闲雅地品茶,唐二爷古铜色的脸上泛起些许红晕,和金三爷、郑四爷、董五娘他们一起听着。
秀水在小心翼翼的述说中渐渐回到了过去。
秀水小的时候,母亲就告诉他父亲去了中国,父亲给母亲留下一个青花瓷瓶,CHINA,中国。母亲送父亲登上去中国的轮船。轮船向着太阳坠落的方向驶去。母亲抱着青花瓷瓶立在海边的岩石上,海风吹落了她头上的围巾。波涛轰鸣着,向她传递着夫妻离别的哀情。直到秀水十八岁,父亲还没有回来。母亲就像当年送父亲一样把秀水送上开往中国的轮船。告别时,秀水紧紧抱着母亲不松手。母亲的眼泪落在秀水的肩头,秀水的眼泪落在母亲干枯的头发上。自从那条围巾被海风吹落后,母亲的头发就干枯了。母亲抽泣一阵,用双手捧住秀水的脸,用无法形容的目光看着他。那目光分明在说:你的父亲在中国,你也应该在中国。几年后他才知道,当他乘坐的轮船在大海上消失的时候,母亲就跳海身亡了。母亲这是要断了他再回日本的念头。秀水当时不知道扶桑国生有三尺多长的不死草,要知道的话,秀水一定采几大把回来,覆盖在母亲身上,让母亲活转过来。可是找不到父亲,让母亲活转过来有什么用呢?秀水得寻找父亲。秀水一踏上中国国土,就觉得踏在了父亲的脚印上。
“你们问我我的父亲是菊池还是铃木,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热爱和向往中国的古董。他或者他热爱和向往中国历史文明的精神就是我的父亲。这就是我的父亲,有这样的父亲多么令人心满意足啊!”
一到中国,秀水就盲目地闯进古董江湖,连摸索带学习,渐渐地成了中国通。不,不是渐渐地成了中国通,而是渐渐地在成为中国人。每每搜集收购或者暗拍到一件古董,秀水都要跪到一棵大树或者一丛野花前,对天祈祷:“父亲啊,如果这就是你,就让这大树落下一片叶子吧!如果这就是你,就让这鲜花凋谢一瓣吧!”春风和秋风使劲吹拂,可是树叶没有落下,鲜花没有凋零。花枝和树叶在风中哗啦啦响着,像是父亲借着花枝和树叶向他絮语:“这是我,但不是我的全部,而是我小小的一部分!”秀水听清楚了,听明白了,把收到的古董运回日本,然后再去搜寻收购或者暗拍。
秀水记不清有多少古董经过他的手流到了日本。反正弄到手一样东西,他都要对着大树和鲜花祈祷,他一祈祷,风就把父亲的声音吹到树叶和花枝上来。他虽然无法完全分辨清楚那声音,但那声音却能督促他不断地去搜购新东西。他不知道到手的东西是不是父亲想要的,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父亲的组成部分。但越是不确定的东西越是对他有吸引力。他的父亲没有尽头,他做的事情也就没有尽头。天长日久,成癖上瘾了,就像吸大麻一样,吸的日久,瘾入骨髓,没法戒掉。再说,为什么要戒掉呢?他不是吸大麻,而是在寻找父亲。他只要看见父亲,看见父亲的一部分,便会不惜财力,把他买到手。然后祈祷,然后设法运回日本。
秀水说话时,一只眼镜片往外放放着很亮很亮的光芒。那光芒就像小孩在太阳底下玩反光镜一般。
“有一次,我看到一件东西,结果把一只眼珠看掉了。今日看到小克鼎,这只眼珠恐怕也要掉出来。”
在坐诸位听过秀水的身世及历史,立时便感觉出了这句话里隐藏的决心。在坐诸位看着对中国古董怀有如此深厚感情的秀水,简直不知道该恨他还是该爱他,亦或是该同情他。
但这毕竟是竞拍现场,爱、恨和同情都得暂避三舍。
唐二爷起身,十分认真地对沉思默想的杨老汉说:“杨老哥,你看这样行不?只要七方小克鼎团聚,你就是宝鼎楼和秦汉瓦罐的主人,我去四郎河边给咱养牛。”
杨老汉一边听一边愣怔地看唐二爷:“我当宝鼎楼和秦汉瓦罐的主人,你去养牛,那你老婆咋办哩?”
金三爷和郑四爷差点笑了。
唐二爷依然一本正经,侧头看妻子周玉箸:“我去养牛,你咋办?”
“我是你老婆嘛。”
杨老汉:“意思不明白嘛。”
周玉箸:“老婆就是自家男人脚上的鞋,脚走到哪里,鞋就跟到哪里。”
杨老汉神神秘秘地朝秀水转过头去:“这位先生,你到底有多少钱呢?”
秀水:“数不清,我背后有财团,还有银行。”
“天天,还有银行哩。”
“对,只要你开价,开天价我也不还价。”
“那我开呀。”
“尽管开吧。”
“无价。”
“无价?”
“对,无价。我这小克鼎无价,你虽然有银行可咋买呢?”
秀水听说杨老汉要开价,本来已经立起身,可当听到无价二字时,又一屁股跌回到椅子上,浑身的气全泄了。
看到秀水萎顿在椅子上,齐明刀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齐明刀受唐二爷之托去寻小克鼎,当然希望小克鼎团聚在宝鼎楼里。但他没有翻冯空首这道墙,冯空首忍着疼痛引来秀水参与竞拍。再者,杨老汉也要在竞拍场上看看,谁对小克鼎更有诚意。杨老汉现在看到了,唐二爷代表的长安城一方和秀水代表的日本一方都对小克鼎有诚意,而且诚意之深,深入肺腑和骨髓。杨老汉坐在这激动人心的场合,忽然明白:仅凭诚意和财力是无法解决小克鼎的归属问题的。超出诚意的更深层的东西才是裁决的标准。杨老汉本意是看谁更有诚意,没料到透过诚意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杨老汉内心本能而自然地以这更深层的东西作为裁决标准。杨老汉开出无价之价其实就是再明白不过的裁决。
齐明刀悬着的心一放下便去看冯空首。他想看看冯空首对秀水的反应。可是冯空首不见了。冯空首刚才还戴个大口罩,趔趄着两腿靠墙站着。可齐明刀看时,那儿只剩下光墙了。这个冯空首,跑到哪里去了呢?
唐二爷胸膛里紧跳的心此刻也平静下来。尽管他是继续做宝鼎楼的主人还是去四朗河边养牛这件事还悬而未决,但他古铜色的脸上已经露出些许得胜的神气。只要桌上的小克鼎不再流失,并且七兄弟团圆,那不管是做宝鼎楼主人还是去四朗河养牛都是愉快的。
唐二爷端起周玉箸面前的茶杯美美饮了一口。郑四爷惊奇万分。郑四爷一生只饮茶不饮酒。唐二爷一生只饮酒不饮茶。可唐二爷分明端起妻子面前的茶杯美美饮了一口。郑四爷正要喊一句“唐老二,你又在我的四水堂开戒了!”却见唐二爷放下茶杯,用巴掌抹一下嘴巴说:“好香的酒呦!”原来,唐二爷把茶当酒喝了。
众人看得清楚,但都笑一笑,没有说破。
唐二爷享受够了这份盼望许多年的快乐,才转而对秀水说:“秀水先生,长安城这几年,你算是白呆了。”
回忆的激动和竞拍的沮丧已经消逝,寻常的平静已经回到秀水身上。
“唐二爷所言差矣,我庆幸来到长安城。长安城使我对古董的理解更加深刻。”
“可你注定在长安城里一无所获。”
“非也,今日这场合,就使我收获大大的有。”
“我是说古董,长安城的古董,你一无所获。”
“古董仅仅是昭陵六骏和小克鼎这样具体的石刻和铜器吗?”
唐二爷扬脖哈哈大笑:“我终于把秀水先生的心里话激出来了!”
秀水也仰天大笑,笑得差点把水晶眼镜掉下来:“我不光收获到了长安城的精气神,还收获了一件凤凰虫草八棱开光青花梅瓶!”
董五娘本来梅瓶一样端坐着,听到秀水的哈哈笑声和话语,惊得嚯一下站起来,双眼恐慌地看着秀水,急切地问:“你说什么?!”
秀水一字一顿,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我不光收获到了长安城的精气神,还收获了一件凤凰虫草八棱开光青花梅瓶。”
恐慌和惊疑像云一样被风吹散了,董五娘慢慢坐回原位,重新恢复了梅瓶的端庄和沉稳:“不可能!赝品!”
一直优雅品茶的杜大爷却若有所思地搁下茶杯,用手去摸面前的青玉圭。摸青玉圭的时候,杜大爷想到了金柄印,杜大爷心里也好生奇怪:为啥秀水一提到凤凰虫草八棱开光青花梅瓶,董五娘一惊疑恐慌,自己就想到金柄印呢?
秀水大概是铁了心要试探一下长安城的人,故而尽量把话朝明里说:“这话我本来想在瓷魂铺里说,但觉着没拿实物怕说不清,所以就搁在心里了,谁知,这话茬在今儿这场合接上了。”
杜大爷淡淡地说:“接上了就说吧。”
秀水:“既然杜大爷愿意听,我就说吧。”
“说吧。”
“那可是青花里的大器,有两匝多高,瓶口折沿,脖颈上细下粗,呈八棱向瓶身通体过度。瓶身上体浑圆饱满如球,活像丰满的董五娘坐在那里。周身缠枝牡丹花草,开光犹如云朵浮空。开光里边花草稀疏,蟋蟀伏地,一对凤凰鸣叫飞翔。瓶上青花,通体湛蓝。尤其令人惊奇的是,湛蓝之中,还散布着深褐色的斑点,那斑点和董五娘脸上的雀斑形状一模一样。”
董五娘本来已恢复了梅瓶的端庄和沉稳,端坐在椅子上。可是秀水的描绘是一只有力的臂膀,猛劲推了董五娘一把,董五娘这尊梅瓶歪歪斜斜地倒在了椅背上。董五娘淋水青瓷一般细润的脸庞顷刻间变得苍黄无比,原先秀美明亮的眼睛也散失了光泽,鼻梁两侧的雀斑一下子由浅褐色暴突成深紫色。
在场诸位惊疑不解地望着董五娘,个个身不由己地沉入一种突如其来的不祥气氛之中。
不祥的预感得到证实,一种更不祥的预感也随后袭来。杜大爷握着青玉圭的手微微有些颤抖,而且颤抖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