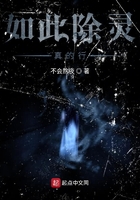三鼎之中,大克鼎的出土和辗转到潘家,至今仍是个迷。
晚清金石大学者罗振玉认为大克鼎是光绪十六年在长安西郡扶凤法门寺任村出土,经北京琉璃厂一位古董商倒手给潘祖荫。民国学者姜鸣认为这个说法不可信,因为潘祖荫正好在这一年辞世。那个时候,古董出土,绝密事件;路途运输,绝密事件;寻找买主,绝密事件,不可能一出土就转到潘祖荫手里。姜鸣一心要弄清这桩私案,跑遍北京和长安,查访踪迹,终于在北京一古董铺看到《西周克鼎金文拓片挂轴》,轴上落款为:“光绪十五年五月顺法李文田识”。
李文田落款旁右侧又有民国学者马衡题跋:“克鼎出土于宝鸡县渭水南岸”。
大克鼎先一年出土,潘祖荫后一年辞别人世。但他还是看到了它。
大盂鼎内壁铭文十九行二百九十一字。大克鼎内壁铭文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仅比大盂鼎少一个字。大克鼎铭文记载的是:克赞扬祖先师华父有谦虚的心地、宁静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能保安其君,主恭王,能辅弼王室,施恩万民,能安定边远,合恰内地。周王念其功,任命师华父孙子克为出使王命,入达下情的官职膳夫。铭文还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和赏赐内容,克跪拜叩头称颂天子美德,并铸鼎感念册封和祭祀其祖师华父。西周奴隶社会世官世禄、后世享受祖先余荫的世袭传统由此可见一斑,而且与清代潘祖荫家族及其潘祖荫这个名字竟然如此相似与对应。这恐怕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现代科技都无法解释的。
大名鼎鼎的大克鼎被大名鼎鼎的潘祖荫收藏了,可和大克鼎同时出土的七个小克鼎,其去向就很少有人知晓了。
七个小克鼎,经过了唐二爷家三代人的努力,搜索寻觅到六个,秘密珍藏在宝鼎楼里。唐二爷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第七个小克鼎,让他们团聚在宝鼎楼里。
雪花拓片也如一片枯黄的树叶,飘飞过百来年时空,经过齐明刀和陶问珠的手,放在了唐二爷客厅的红木八仙桌上。
当陶问珠听完唐二爷的叙说后,大为惊异:没想到一件古董之内,竟然有这么多参不透悟不出的神秘内容。
陶问珠觉得,自己被唐二爷死命捏着的胳膊不像刚开始时那么疼痛难忍,并且感觉到一股巨大的热流,血液般通过唐二爷的大手,涌流到她胳膊上来。那热流顺着胳膊上流,直灌她的心田。
她心潮彭湃,把融在翡翠耳坠里的人情债给忘了个光光净净。
好多天来,齐明刀都在盼望陶问珠有信息传过来。信息一传过来,他就能见到唐二爷了。就在齐明刀盼望得有些焦急的时候,腰间的电蛐蛐镝镝地叫了,齐明刀急忙按动开关,电屏幕上滚动出来的字却是:下楼提酒肉。
没有署名,也用不着署名,肯定是冯空首打的。
等的陶问珠,来的冯空首,跟的酒和肉。
齐明刀在街口接回了冯空首。冯空首买了一瓶太白酒,一瓶长安老窖,一堆肉菜,足够四、五口人吃喝。
冯空首说:“借你房子吃喝。”
齐明刀:“你房子空着嘛。”
“我借你房子,别人借我房子,就这档子事。”
“谁借你房子用哩。”
“来了就知道了。”
二人进屋摆桌支凳,冯空首把酒肉分成两份,一份留下,一份两人吃喝。
吃喝间,冯空首问齐明刀:“这几天咋啦,戴蒙眼的驴似的,老在磨道转圈圈?”
“烦。”
“烦啥哩?”
“烦烦哩。”
“你呀,想过长安城的生活,却耐不得城里人的寂寞。”
“我不是寂寞,我是着急。”
“着急得忘了咱是吃哪碗饭的。咱是啥?咱是长安城的古董商!商人嘛,男人不吆牛扶犁耕田,女人不织丝养蚕,但吃的是鸡鸭海鲜,穿的是绫罗绸缎。”
齐明刀有些诧异:“咱是古董商?”
“咱不是古董商咱是啥?这长安城里,东西两市,百家店铺,千家商场,卖瓷碗铜锅,卖布卖衣,卖菜卖粮,卖牛肉羊肉猪肉,卖花草鱼虫,卖字卖画,卖茶卖药,卖眼镜卖山货小吃,卖各式家用电器,卖戏票电影票球票,卖权卖势卖恶卖智卖乖卖巧卖色卖艺卖力卖命……咱是卖啥的?咱卖古董。卖古董不是古董商是啥?你卖古董给金三爷和郑四爷,我从中说合我就是牙人。牙人卖啥,牙人卖嘴。这长安城就是卖和买的大杂院,无论卖啥买啥,只要能高价卖出低价买进就是成功的商人。你低价买进的古董高价卖出你就是成功的古董商人。你齐明刀就是成功的古董商人你还烦躁啥哩?还着急啥哩?”
“我着我的急哩。”
“你急是因为你不晓得古董行当的卖买特点:古董行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有些人在古董行当黑摸瞎碰大半辈子,结果连个古董毛都没薅上。你呢,跟打麻将似的,手兴得很,连和带炸,一连两把,赚了好几大块,够你在长安城里山吃海喝三年,就这你还急哩,当心额头上急出犄角来。”
齐明刀觉得冯空首越扯越远,回应说:“我不是为你说的急急哩,我是为一张拓片急哩。”
“拓片?”冯空首机关枪似的嘴巴突然关闭住,一双眼睛吃惊的望住齐明刀,沉默许久之后才慢慢地说:“你翻墙了?”
翻墙,是古董行当的黑话,意思说越过中介人和中介人介绍的人直接会面做买卖。齐明刀想,陶问珠确实是冯空首介绍认识的,自已不经冯空首,直接把拓片拿给陶问珠,确实有翻墙的嫌疑。
“就算翻了,但不是做买卖。”
“那是干啥?”
“想认识唐二爷哩。”
“凭一张拓片?”
“对。”
“拓片上拓的啥?”
“古鼎。”
“古鼎?”冯空首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眶立时张大了。
“对,古鼎。”
冯空首把古鼎两个字牢牢地记在心里。
冯空首脸上不露声色,眼角却透出一丝惊异:眼前这个结识不久的稼娃朋友,咋能这么快就做出这种出人意料的事呢?
齐明刀觉得嘴里的酒菜有了异味。
恰在此时,门外有人喊冯空首,冯空首开门,齐明刀看到已经见过两次面的殷龙骨领着一个年轻女娃在门外。殷龙骨瘦麻失杆,面黄肌瘦,女娃倒是面色红润,苗条有韵,很有几分姿色。
冯空首:“你俩是先吃哩喝哩?还是先到我屋子哩?”
殷龙骨歪斜地笑笑,拧头看女娃,女娃看一眼殷龙骨,低下头笑笑,不言语。
还是冯空首善解人意,说:“那你俩就先到我房子去吧,完了再吃喝不迟。”说着过去开了门,放殷龙骨和女娃进去,拉上门,又回到齐明刀屋里。
齐明刀晓得谁为那般事情要借冯空首的房子,心里顿时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冯空首大不咧咧地坐下来,继续吃菜喝酒,说:“那罐子古钱币脱手了。”
“脱手了就领个女娃来用你房子?”
“男人要钱弄啥呀?”
“男人有钱就弄女娃?”
“是呀,你要想弄,哥也给你领一个来。”
齐明刀眼前忽然惊现出陶问珠柳丝般随风飘荡的秀发,黝黑的脸庞,毛茸茸的大眼睛,和时而闪现出来时而隐藏在发丝里的翡翠耳坠。那翡翠耳坠的晶莹绿光和自己脖领里的刀光映衬得太好了。
一想到陶问珠,齐明刀就觉着冯空首的话令人犯恶心。自己如果真能够娶到陶问珠这样的女子做媳妇,自己就绝对只守家花,不摘野花。
冯空首说:“我晓得你在心里恶心我哩。你恶心我没关系,但你没办法恶心长安城,长安城就是这生活。你也没办法恶心这生活和这社会。”
冯空首说得也许有道理,这社会这生活就摆在你面前,无论你咋样恶心它,仇视它,它都不改变。非但不改变,反而沉沉稳稳地向前挪动着。本来想啐一口的齐明刀,想到这里,咽了一口唾沫,喝了一口闷酒,不再言语。
冯空首猜透了齐明刀的心思,忽然话题一转,问起来了三百六十行的祖师爷。
“你知道裁缝业的祖师爷是谁吗?”
“轩辕皇帝呀。”
“占卜算卦业呢?”
“鬼谷子。”
“赌博业呢?”
“孙膑孙大将军。”
“商业呢?”
“白圭。”
“屠宰业呢?”
“张飞张大胡子。”
“唱戏的呢?”
“玄宗李隆基呀。”
“饮酒业呢?”
“杜康呀。”
“娼妓业呢?”
“不知道?”
绕了一周八匝,又绕到妓女身上来了!哼,我才不知道呢!
“告诉你吧,是春秋名相管仲。管相爷当年治理齐国,库中财政紧缺,于是在全国多地设置女闾三百余处,号令天下男人,尤其是外国进入齐国的男人都去女闾做嫖客,把女闾里男欢女爱的生意扇得红红火火,然后向妓女征收夜合钱。管相爷确实是位大政治家,他参透了男人女人,领悟了孔圣人“食色性也”的奥妙,放手让男人女人干男人女人爱干的事情,然后征夜合钱。夜合钱是啥?税呀。舒服你尽量舒服,但不能白舒服,得纳税。纳税干啥?充实国库啊。”
“管相爷这手绝招,传给后世,竟然变成了一种文明。历史上大凡兴盛朝代,娼妓业都非常兴隆旺盛。国运兴则娼妓兴。大唐长安城平康里、典卷以及北面一些街坊,云集色艺双全的上等妓女,专与官宦子弟和风流文士玩乐。城南一些坊巷住的多是下等妓女,狎客也多是士卒、生意人和市井闲人。西市藩坊,集中外籍妓女,扶桑国,白俄罗斯,西班牙女郎,其中最多的还是胡姬,胡姬个个生的细腰肥臀,臂腿丰满,高鼻阔口,金发碧眼,且能歌善舞,卖弄风骚。宋时又有瓦舍勾栏。
勾栏是妓女表演的戏台,瓦舍是男女互相掺合的地方,搂抱成零距离或者负距离叫瓦合,完事了拍拍屁股各自走人叫瓦解。至于青楼翠馆,则是旗帆高扬,挂牌营业。不过那些旗帆和牌匾如今已换成了帝豪和百老汇洗浴中心,洗足堂,按摩房,桑拿室,ok厅……改头换面,也蛮有时代特色。古代妓女有组织有纪律,有帮派,有擅文的苏帮,擅武的扬帮,文武皆擅的京帮。各帮妓女四面出击,抢占码头,洪水一样漫向全国各地。以三尺女儿身,经营天下事。现如今兴川帮、天水帮、江南帮和东北帮。虽然帮帮特色不同,但已经是以肉身区别,文武技艺,早已丧失殆尽,和古代的妓女比,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大大地降低了。降低成只知收费,不知纳税,更不要说充实国库了。”
冯空首越说越带劲了。
“乡下穷,城里富,山民朴,市民玩。手头有闲钱,饱食终日之时,不掏俩钱买乐子弄啥?客人到星级宾馆和高档洗浴中心,洗澡吃饭想让妓女,不,现如今叫小姐陪侍,便翻名牌呼号码,称点花牌。邀小姐到酒店陪酒叫出局。若看中那个小姐,也可付钱带走,叫下蕃。你瞧,殷龙骨领的便是天水帮下蕃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