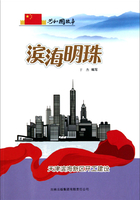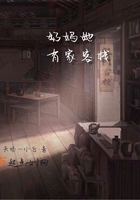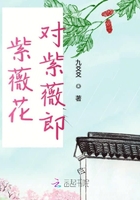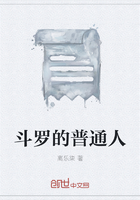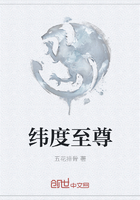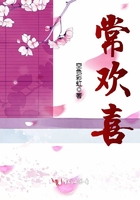——定南酸鸭的回忆
有一道菜,我心心念念了三十多年。
不光我,我的许多大学同学也一直回味着这道菜——定南酸鸭。
今年春节,托定南老同学之福,终于了了再尝酸鸭的心愿。
我的大学生活谈不上美好。更多的是囧。是精神空虚、物质匮乏的苦涩回忆。总结起来,有三大糗事。第一是情窦初开,暗恋不成。这个就不多说了,大家都差不多,鲜有成功的范例。估计有人比我更惨,暗恋n个都折戟沉沙。第二是老担心皮带会断。那个年代,没钱,用不起真皮,系的都是塑料的,易断。曾不止一次皮带裂了没钱买。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子,腰上系一根眼看着要断裂的皮带到处晃悠,情何以堪?有一次上体育课,只好腰上系着绳子上课,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第三,老担心掉鞋底。大家都只有一双鞋。为了保持尊严,那时街上有一种职业:补皮鞋、钉鞋掌。但无论你怎么小心,还是费鞋。有一次买了一双温州产的新皮鞋,没穿几天,下雨,鞋一沾水,底掉了——捡起一看,原来是纸皮糊的。
囧事一箩筐……现在同学之间互相揭老底,主要是拿谁暗恋谁开玩笑。三十年前的伤疤,成了花,成了古董,被反复细细鉴赏。哈哈,别装了,谁没有青春?谁没有回忆?
所幸,平淡中不乏美好。说起来,美好的回忆都跟吃有关。那些偶尔吃肉的日子,全成了记忆中集体的狂欢。
1983年冬,全班同学赴定南、龙南实习。我们六位同学分在定南礼亨中学——坐落在水库大坝下的美丽所在。同组的三位女生(如花似玉玫瑰般的),其中一位学习委员,一位文艺委员。我在班里年龄偏小,能力也弱,从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可不知咋的,辅导员丁老师却安排我做实习组的组长。我做这个组长,其实是徒有虚名。我好像从未组织过一次会,也从未布置过一次任务。但我干了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是主编了一份实习快报,以诗歌的形式抒发一些感受,把礼亨吹嘘了一番。结果引得其他实习组同学借机来访(当然是冲着三位美女来的),后果是由我掏钱招待吃午饭。第二件事是骑自行车带领全组同学进了几次城。进城的主要目的是下馆子。这是我第一次享用这道美食——定南酸鸭。
鸡鸭鱼肉,都是家常的食材,只是各地做法不同而已。我老家端午前后时兴仔姜炒鸭。姜要刚出的肥嫩的新姜,鸭子要当年的两斤左右的麻鸭。姜一半,鸭一半,配以生蒜、米椒,猛火爆炒出锅。佐以客家水酒,那滋味,那享受,实在无法说与人知。我到现在还记得端午时节,家乡一个叫上眭门的地方,满大街人们拎着鸭子回家的情景。
如今,定南酸鸭已入选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属赣南名菜之一。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定南酸辣白切鸭。这道菜关键有三:一是选料。与仔姜炒鸭一样,得选当年出生的两斤左右的瘦型土鸭——泥鸭。这种鸭肉质鲜、嫩,有嚼头。二是火候。火候不够,鸭子不熟;火候过了又嚼不动,得恰到好处。三是蘸料。要用当地酿的米醋,拌小米辣、蒜蓉、姜末。这是关键,据说有名的店都是自酿米醋。
酸、鲜、辣适度搭配,色、香、味完美组合,对年轻时候的我们是难以抗拒的诱惑。一元钱三两鸭,每次下馆子都点这道菜。实习一个半月,我花了七八十元钱(其中有女同学看我花钱如流水,入不敷出,借我三十元。堂弟刚参加工作,知我困难,寄我四十元。那时一个月工资不过四十元),好像有一半用在吃酸鸭了。
老同学一路领我重返礼亨。水库还在,学校已不复存在,代之以敬老院。那些教室、宿舍都已拆除,只剩一座小水泥桥;汩汩清流,只剩一汪锈迹斑驳的死水。当年,黄昏,桥下,溪边,挤满了高中少年,那几个洗碗浣衣、眼神躲闪又热切的女孩呢……
老同学周到,请定南的几个同学,还有当年我们的指导老师——罗老师作陪,中午设宴款待我们一家。为了保证我们吃到最正宗的酸鸭,老同学特意从一家叫金茂酸鸭店的打包了几份带到酒桌。不等主人谦让,我连连举箸……见我木讷,有位同学缓缓开口:醋,还是当年的醋。鸭子,已不是当年的鸭子。因为酸鸭出名了,销量大了,鸭子未必是本地的泥鸭了……其实,无需解释,我知道,什么都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自己,是岁月……
有一道菜,叫岁月。它由时光烹煮。文火慢炖,直到烂熟……
有一道菜,叫青春。它,就该在年轻时狼吞虎咽、恣意挥霍。当你老了,再好的厨师,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为我们调制、烹煮那些虽然困顿蹉跎却依然激情燃烧的岁月。
而岁月,一定是你如影随形的敌人。它,再花言巧语,永远不可能是你真心实意的朋友;它,再绚烂夺目,永远不可能是你可以反复享用的——那道菜……
(2017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