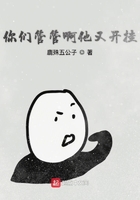少女第一次有了意识时,是在一个三足小鼎里,小鼎的上方是一颗柳树,一颗不断从三足小鼎身上抽取能量的柳树,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当小鼎的能量被抽取完毕时,自己也会在那颗树的抽取下越来越虚弱,直到意识消失。
可她丝毫不敢反抗,因为这颗树所在镇子是一个大阵,囚禁着三足小鼎的大阵,自己丝毫不怀疑,一旦从三足小鼎中脱离出去,自己将会灰飞烟灭。
更何况镇外还有一个令自己生不起丝毫反抗念头的存在。
小鼎对自己来说,既是盔甲也是囚牢,正如那颗柳树对于小鼎一样。
好在,就当自己意思微弱到快要油尽灯枯时,那棵树消失了,可小鼎也已经失去了最后一丝能量。
柳树消失,小镇的大阵发动,眼见就小鼎就要破碎,一旦小鼎破碎,自己也将不复存在。
可小鼎没碎,因为他被那个让自己生不起丝毫反抗念头的存在抓在了手里。
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她活了下来。
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带着她来找到的这个少年也活了下来。
徐来将几颗看起来最大的药材放进了背篓里,望向面前的白衣少女,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像是鼓足了勇气,缓缓开口:“既然你也已经吃饱了,我们就此别过,后悔有期。”
白衣少女也不说话,就这样盯着徐来。
徐来被看得头皮发麻,将背篓里的药材小心翼翼的放到地上,微微开口:“这下我可以走了吗?”
她看着那个清瘦少年,就是不说话。似乎在告诉徐来,来啊,继续你的表演。
徐来满脸无奈,声音有些颤抖:“你真的想吃了我?”
少女眨了眨眼睛,然后开心笑了,如一只狡猾的狐狸。
日上三杆,徐来终于返回了小镇。
擦了擦头上的汗,背着背篓的徐来连家也没回,匆匆向镇东城门跑去。
从山脚到到镇东城门,跨越大半个小镇。
小镇一样,好像又有些不一样,小镇还是那个小镇,只不过是一个人去楼空的小镇。
到了小镇东城门,徐来那张焦急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镇东城门,一个邋遢汉子正躺在高大的城墙上,嘴里叼着一根狗尾巴草,正在破口大骂,“一群王八犊子,当初挤破了脑袋想进来,现在拼了命的想出去,劳资几百年来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换作以前,劳资一刀下去将你们劈了个干净。”
徐来看到有些气急败坏的邋遢中年人,一时有些局促,就连脚步也变得扭扭捏捏起来。
从端午开始,这个守门的邋遢中年人在徐来看来好像就变了一个样。
空空如也的城门,也不知是谁惹得他如此不高兴。
将背篓放下,徐来拿出一颗采药的模样的东西,放在那个破破烂烂的桌子上,准备转身离去。
大概是年久失修,或者是寿命到了,桌子夸嚓一声,碎成了一地的木渣滓。
兴许是被声音惊扰,邋遢中年人从高高的城墙上径直跳了下来,不远不远刚好落在徐来面前。
“小王八犊子,你也想出去?”停止了口中的谩骂,邋遢中年人开口问道。
少年仰起头,盯着高出自己一个脑袋的邋遢中年人,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我。。。。我就是来看看!”背上背篓,徐来落荒而逃。
少年自然没看到,邋遢中年人袖子一挥,那张破烂桌子所变得木渣立马消失不见,一颗长着几十颗红色果实的大白萝卜正安安静静的躺着。
邋遢中年人捡起地上长着红色果实的大白萝卜,看向少年背影消失的方向,大声骂道:“暴殄天物!”
当最后一抹红色消失,邋遢中年人用袖子擦了擦嘴角,一个纵身跳上了高高的城墙,不停的吧唧着嘴。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重新躺在城墙上,嘴里哼起个来。
从镇东城门到徐来家里的途中,一辆辆马车缓缓驶出小镇,有的还对徐来打着招呼,有的脸上表情如避蛇蝎。
徐来对这一切早已见怪不怪,就连白花花的银子和黄澄澄的铜钱也有人不喜欢,如果太在意别人的态度,那就干脆不活好了。
向来好像什么都缺的少年,从不缺心态。
当少年回到家中时,脸上的表情已经满是疑惑,今天遇到的人不多,可无一例外都是准备出远门的。
邋遢守门人的话他明白了一半,这些人是要离开小镇,那种一去不回的离开。
少年晃了晃脑袋,既然想不明白就不想了,更何况自己还一堆的事儿。
站在自家围墙外的大门,徐来竟然来回踱起了步。
如同家有悍妻,不敢却又不得不回的中年男人。
少年踱步的时间没能持续太久,那扇已经饱经风霜有些发白的木门打开了。
徐来只得硬着头皮走了进去,进自己的家门,却像是一个去丈母娘家上门提亲的男子,动作扭捏,神态做作。
门口处,一位白衣少女倚着门框,看着少年,如新婚燕尔的年轻妇人在等待着劳作归来的丈夫。
进了屋,徐来更加不自在,整个房间很明显被打扫了一遍,徐来虽然很爱干净,但也只是爱干净而已,对于收拾房间显然没有这位白衣少女有天赋。
整个房间里几乎所有东西都被收拾的整整齐齐,因为漏雨还没来得及的地面也变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更夸张的是,漏雨的屋顶好像都被修缮了一遍。
进里屋一看,徐来打开自己原来的房间,自己从小睡到大的那张床上已经换好了干干净净的被褥。
就原本那间用来堆砌杂物的屋子都被收拾了出来,还搭上一张床?
嗯,勉强算是床吧,两张板凳上放着一张木板,原本另一件卧室里,徐来的东西全都被仍在了上面。
白衣少女似乎也没想到徐来会来回得这么快,一时间也有些尴尬,大概意识到自己有些喧宾夺主。
徐来也有些尴尬,大概是觉得漏雨的屋子,家徒四壁。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一个少年,一位少女都有些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