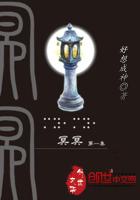我是彭喷。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杨清和了。最近有点想他。今天刚好到平满有点事,办完后路过他的公寓,我提了一袋啤酒就上门了。
敲开他的门,门后露出的是一张,深沉阴郁的脸,脸上写满了诧异和不耐。
这是清和吗?我只觉得陌生。
那一瞬间,我好像被丢在一个寂寥无人的异世界,孤独地面对着一些似人而非人的怪物。
如此孤独,似乎有一个世纪。
幸好,在那之后,清和换上笑脸:“百威还是青岛?”
“金威。”
他给我让出位置,我活动了一下似乎已经生锈的胳膊腿,挪动脚步走到那间小公寓内。
真小。不知道他一个写小说的为什么非要待在上川。把啤酒往桌上电脑边一摔,我直接坐在他的小床上。不过,他待在上川也好。我也能找着人唠嗑。
他一点也不客气,拉开一罐啤酒就喝。别看他这样,他其实不怎么能喝,一个劲说啤酒就是马尿。他喝过马尿吗?马都没有见过一条。
我一边拿起啤酒,一边看他。刚刚为什么我会生出那一系列莫名的错觉?
“看我干嘛?”
“没。”
我低头喝酒。他把啤酒放在地上,说垃圾话:“前不久你是不是分手了?现在看我都觉得眉清目秀?”
我确实分手了,那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有发朋友圈,他应该是看到了。我没应声,那不是什么好事。杨清和走到我后面,拿起扫把开始扫地。看起来房子已经很久没打理了。
“这年头。你和星星都能分。”
“分了。她家里人催婚。这个月出去相亲都四五场了。你别扫了,和我讲究什么?”
扫了也没什么用。这屋子一股臭味,一股——也不能说是臭,就是很久没通风,有一股陈腐的人味,可能是杨清和的长久以来吐出并沉淀的浊气吧。
“你打开窗通通风。”
说着,我站起身。在狭窄的房间内随意地走了两步,我看到杨清和桌上有一本很厚很显眼的书。我伸手就要把它抓过来看;忽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使我停下了动作。
黑!
无尽的手,捂住了我的眼睛!下一步,就要把我拖入无边黑暗!
这是一种令我无法不重视的强度极高的感受,一种仿若真实的感受。而事实上,我还在电脑桌前,伸手要拿那本书。
是什么这么可怕!这本书吗?
我的身体往后微缩,头发好像被什么碰到了。我转过头去......
“清和,我肚子疼。”等我清醒时,我正坐在他的床上躺着,说着不经过我大脑的话。我的思维有点卡,刚刚看见了什么?
我一回忆,我的大脑就告诉我,我什么也没看见。伴随这个信息的,还有几个扭曲的手势,仿佛语言的手势......
正常。不正常。正常。不正常。
我的大脑里,这两个概念来回碰撞,最后善罢甘休,消失不见。
清和终于停下了扫地的动作,放下扫把簸箕,拎着啤酒坐到我旁边:“你也是可怜。”
“可怜个屁!”
我当然很生气,我需要他可怜吗?
“老子又恢复自由身了,从此潇潇洒洒。忘了咱从前泡吧的岁月了吗......”
“忘了。”
“别打断我啊......”
“吧里都是我们两个聊天,聊着聊着,就有美女过来带你去睡觉。”
“你这话说的,酒水钱不都是我帮你付的?”
说话间,我喝完了一罐啤酒。这会倒是不觉得肚子痛了。
“是是,钱都是你付的。我倒是还想和你再去泡吧,你看你这个状态,能去吗?”
“当然能。”
“你不爱她了?”
“怎么可能!”
我怎么想不开呢?要来杨清和这个傻逼这,听他喋喋不休,抓住我的痛处问东问西?
也罢,不怪他,是我自己痛,痛得咬牙咧嘴。明明都过了一个月了,分手前也商量许久了......
我叹一口气,他也叹一口气。
“我这还有半瓶朗姆。来?”他问我。
不愧是朗姆小王子。“来。”
他从床底的旮瘩角扒拉出一个看上去有一升容量的玻璃罐,里面回荡着透明的液体。我忽然有点虚,今天只是顺路过来看看,喝完朗姆酒,岂不是得扶着墙回去?
“拿什么接?”他问我。
“你这没有杯子吗?以前明明有的。”
“你上一次来到底是什么时候?靠,四个月?”
“四个月里,你把那三个杯子都碎了?”
他骂骂咧咧,最后又从床下的另一个旮瘩角抓出一个小玻璃杯。杯里甚至还积了一点灰,看得我背后发寒。幸好,他给我倒酒前拿衣服帮我擦了擦。或许这也没有好多少吧。
量不多,就半杯。我一口吞了下去。这朗姆酒劲很大,之前被杨清和灌过一次,喝了一百多毫升,走路都是飘......的......
这才一口。伴随这最后一个念头,我失去了意识。后面发生的一切,我都不知道了。
彭喷绵绵软倒。
杯子磕到地上,剩余的几滴液体顺着倾角淌出。
杨清和有点心疼。这不是朗姆酒,它可比朗姆酒珍贵多了。
这是愤乐清泉。可以使人失忆。醒来后,会产生自己很快乐的错觉。
他趴到地上,摸摸索索又从床下拉出一个罐子。这就是货真价实的朗姆酒了。
还有半升的样子,清和撬开彭喷的嘴,一点点把朗姆酒全灌了进去。
“你真没用。”杨清和喃喃自语。
“每个人都应该为了爱情奋不顾身。”他转身,从书桌的柜子里面拿出《恶作剧之书》,快速地翻阅着。
最后,他停在了其中一页。
手指一行行划过诡异莫名的扭曲文字。他的左手同时在空中划出反常的轨迹,那和书上的文字意思是一样的。
【富坦语:天空是巨大的眼球,神祗将你我注视,尤其眷顾敏感的痴人。再多的灵感无法察觉困迷,再多的付出无法换来解脱。让我教你,让他教你,让每个非人教你,非人的勇气。那是你的蜜,那是人的毒。】
他的左手演奏到一半,就陷入困境。他还无法顺利地用左手表达富坦语。
他便从嘴中吐出深长鲜红的触须。触须上是细密精致的人手状花纹,其外裹着一层黏液。
触须随心舞动,咒语很快完成。
虽然彭喷闭着眼睛,而且早就晕了过去,但他还是听到了富坦语。
这是一种突破理性的语言。
杨清和还不放心。他蹲下附到彭喷耳边,重复了一遍富坦语。他发出的声音十分尖锐,介于能听见和听不见之间,会使偶然听见的人觉得如坐针毡、芒刺在背,使他们想要把手伸进自己的胃,把刚才听见的东西从那里挖出来。
即使彭喷晕着,他也表情痛苦,肢体抽搐。杨清和显然不在乎他的表情和感受,艰难而坚定地念完了咒语。
要做的事情完成了。清和把彭喷抬到床上,为他盖好被子,接着开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