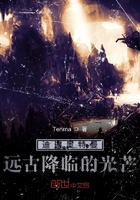“雨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下的?”
倚靠在树下的胖子目光呆滞,眼球直视着前方,再次发出令人烦躁的单调呓语。他的大脑袋上没有戴斗笠,暗金色的长发被雨淋透,睫毛上也挂着水珠。他是这四个人中最矮最胖的,说话向来萎靡不振,自从雨下以后他就变得精神恍惚,无尽与未知的恐惧是他难以接受的梦魇,睡眠是对他的最大折磨,他害怕一旦入睡,那就再也无法分清白昼与黑夜,陷入迷惘的深渊,当现实生活中的追求变得虚无缥缈,毫无意义的思考变成唯一目的。而年轻人和老人相比,更难坚守自我意志,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记忆供其在里面寻找锚点,更因为他们对于生命还有更多的期待,那种多见于年轻人,因为壮志未酬而备受折磨的心情这几天就像一条灼热的火鞭,狠狠地抽打着胖子的魂灵。
年轻的胖子,已被这些恶魔俘获,重复话语是为缓解内心世界崩塌而造成的自我迷失。
在古老的中土神话里,生时纸醉金迷、白白损耗生命的人将会被关进永夜雪山,他们将在漫长雪夜当中不断地攀登、匍匐前行,这些罪人眼里只有一望无际的白色,他们难以证明自己的真实存在,哪怕通过自伤和自戕也于事无补,被自己撕裂的伤口会快速愈合,徒手扯下自己的指甲,拔下头发也感受不到疼痛。他们能够做的只有不断地行走、寻找,周而复始,直到完全赎罪。
“闭嘴!”疯鸟又变得狂躁,脖子上暗藏血管的皮肤碰到弯刀,造成的细小伤口正渗出血液,但他完全感觉不到疼痛。
“我们都应该平静下来。”冷漠的声音再次响起,他从上方走下来,高瘦身材,胸背挺阔,身上的暗红色长袍将身体隐藏,青竹缝制的披肩挡住大部分雨水,让他的身上还保持些许干燥。红袍上的兜帽又宽又大,其深处隐约露出一双充满善意的眼神,他的脸上戴着秘银材质的面具,有些精致的暗纹被刻在在眼角和鼻翼,显得优雅而神秘。他缓缓走到疯鸟和老胡子身边,伸手将架在疯鸟脖子上的弯刀引开,然后挡在两人中间,用虔诚的语气说道:“终结生命很容易,我们很可能死在一起,被这片土地埋葬,‘平等而生,平等而亡’,最终成为这些树木的养料。然而我们都还有使命没有了结,现在自相残杀,是对生命缔造者的亵渎。”
“我见过太多你这种人,当我杀死人,制造惨剧之后,披着不同的外衣出现,滑稽的戏服。你们只想通过人们的恐惧攫取更多金币,有时候还会睡几个村妇,之后就逃之夭夭,我带来恐怖,你们则带走希望。”疯鸟将手中的剑插在腐叶当中,靠在最近的树干上,略带嘲笑地说道。“你信奉什么?奥雷利亚圣教?还是海妖?或者是仙岛传来的什么狗屁自然密教!”
“假如信奉你的神就能让老子不死在这个腐臭潮湿的鬼地方,那我情愿听你讲点他妈的教义,然后再给你的神和你磕他几万个响头。”老胡子曾极其相信海神,那是年轻时候的事,第一次杀人之后他跪在海神庙里几天几夜乞求原谅。后来他杀的人太多,海神的信仰不足以使他变得平静。他转而信奉海妖,那是一种各国都禁止的秘密邪教,它接受信徒的一切奉献,哪怕是刚落地的人头,而且有传言说身份越高贵的人头就越受海妖的青睐。但老胡子并不相信,因为从谁身上剁下的人头看起来都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最怯懦胆小的海盗也不会在杀人的时候祈祷,无论是对着海神还是海妖。只有在第二天酒醒、在妓女床上起来的时候才会想起敌人被杀死时愤怒或者恐惧的眼神,年轻人会在各种信仰中寻找慰藉,他们想被原谅,就像犯错的孩子,需要母亲温暖的手掌抚摸头发,父亲鞭打后的悉心教诲。他们也想和其他人分担罪责,好让自己下地狱之后可以少受折磨,献祭海妖就是为此。可到老胡子这个年纪,早就明白一切罪孽都会成为融入自己的血肉,无论哪路神仙都不能帮你将这些罪愆剥离身躯,你杀的人就会附着在你身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不停地提醒你,“利刃也将加诸汝身。”
“疯鸟“抽抽鼻子,仿佛被什么让人作呕的气息堵塞的鼻腔一样。这是他的习惯,每当要说话的时候就会如此,对于他来说杀人是一种活计,是一切痛苦、愉快、无奈、悲哀的根源,可以说他活着就是为了让人死亡。他看惯人死之前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表情,习惯他们语无伦次地哀求,疯鸟早就无法和人正常的交流,他是一个异类,白昼里,众人躲避他、远离他和盘旋在他身后的黑鸟。疯鸟只会跟将死之人说话,当他开口时,总要将长长的鼻腔里充满的血腥气散出去,这让他变得滑稽,但从没人嘲笑他,死人并不会笑。“老海盗,你的见识不赖。我杀过很多神棍,他们可比谁都怕死。神棍和平民的区别就是靴子里会藏有不少碎金子,而平民连靴子都没有。”
“生命是缔造者最宝贵的恩赐,死亡则违背他缔造生命的初衷,所以每个生灵都畏惧死亡,这并不可耻,反而是最虔诚的表现。在凡人堕落的过程中,缔造者逐渐失去力量,世间万物则失去永生的能力。这是一切痛苦的根源,黑鸟为了短暂的生存吃掉尸体,它们被死亡同化,最终羽毛枯萎,葬身荒野,被野兽啃食殆尽,死亡会一步步吞噬所有生灵,直到缔造者也无能为力,世间将陷入最古老的沉寂。”对于海盗和杀手的讽刺,红袍人的语调没有丝毫改变,依然将自己坚持信仰的教义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