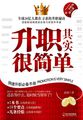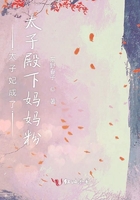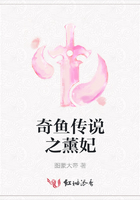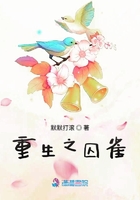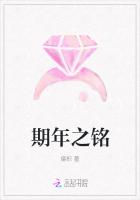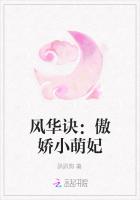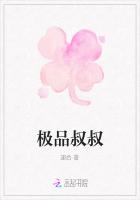来新夏(1923~年)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浙江萧山人。南开大学教授。著有《林则徐年谱》、《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
来新夏先生长期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至今年近八十,仍是天津《津图学刊》的主编。他堪称是当代图书馆学界的权威了,但很多人物辞典却将他列入历史学家类目。这并非是分类的误识,而是因为来新夏是图书馆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半个多世纪来,他研究历史,通过读书目、索引,扩大文献线索,掌握原始资料;他研究图书馆学,又常以历史古籍为载体,由是运用自如,相得益彰。
作为学者掌握目录学的基本知识,学会利用书目、索引去读书治学,这样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通过目录以寻找读书门径是一种有效的读书方法。
目录学就是读书“门径”的启迪
来新夏儿童时期是在家乡浙江萧山度过的,小小年纪就喜欢读书。可是,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常不知所措。有一次,他读《千家诗》,当读到宋朝大儒朱熹的七绝《观书有感》时,对其中的“为有源头活水来”一句很有感触。后来,在旧书摊上他偶然买到一套清人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书的首篇就写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从这位史学前辈的身上,来新夏得到了启示,目录学就是活水的源头!因此当他进入大学之后,选修了余嘉锡讲授的”目录学”课程。余嘉锡是目录学大家,他指定近人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作为课本。来新夏怀着似乎已经得到秘籍线索那样的喜悦心情,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跑遍了北平琉璃厂的书店,也未能买到该书,第一次尝到了求书之难的苦味。直到寒假回天津探亲时,他才在天津的旧书摊上搜求到《书目答问补正》两册。得书后,他急不可待地斜倚在被垛上翻读,一心想立刻找到读书之门径,翻了几页,大失所望。全书了无系统,有如一本陈年流水帐,难以阅读。
来新夏回到学校后,又登门求教余嘉锡,余嘉锡言简意赅地讲了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道理,要求来新夏多读有关的参考书,多注意字里行间,要按《书目答问补正》正文自己动手做作者与书名、书名与作者的索引。导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使来新夏大开窍门,他终于找到了读书治学的源头——目录学,也更加理解了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提到的”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藩篱”的含义。从此,《书目答问补正》也就成为来新夏的案头必备。
来新夏对《书目答问补正》情有独钟。1962年,又采取《四库全书总目》之例,遍读诸名家批注,为《书目答问》作汇补;并将清人杂书所记载与《书目答问》有关评论典籍的条目分别过录。于此,积余年辛劳,致使这本《书目答问补正》天头地脚,字里行间,蝇头小字充塞得几近水泄不通,更有夹纸粘条,补贴于上。这本书记录了来新夏读书的真功夫。
目录学知识使来新夏找到了读书治学的门径,也影响了他的前半生。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二十年,来新夏著作盈尺,且涉及文史不少领域,虽内容体例各不相同,但处处可见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如1983年出版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就是作者成功地运用目录学的一部专著。他说:“我一面检读。一面根据目录学的要求,每读一谱,便写一篇书录”,“每种年谱都是随读随写书录”。
《林则徐年谱新编》的诞生
1997年出版的《林则徐年谱新编》是来新夏校读群书的读书方法的结晶。
来新夏在40年代读大学时,曾读到过一本由魏应麒编写的《林文忠公年谱》,他觉得这本书内容不够充实。50年代初,他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读魏著,深感有拾遗补缺及订讹纠缪的必要,便采取书页签条办法,读书凡有所遇,就在魏著有关书页上标列,积之日久,一书已满,无从着笔,乃另求一本,如法炮制,一书又满,他决心重编林则徐年谱。当年,恰逢中华书局请来新夏审阅《林则徐集》,使他获得可供采集且内容丰富的第一手资料。60年代,来新夏蛰居斗室,伏首书案,历时年余,终成《林则徐年谱》初稿三十余万字。后来又反复校读群书,细加订正,清出二稿。文革之初,来新夏被遣放津郊农村,每每耕余灯下再加清正,遂成三稿。四年后又作参校订正,是为第四稿。此问共校读图书典籍一百六十八种,形成文字三十四万余。80年代,百废俱兴,1981年《林则徐年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的几年中,来新夏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新资料。他随时加以采录订正,再加上友朋的补缺正误,于是他决定增订该书。经过一年的积累,参阅书刊二百二十九种,较原谱增益六十种成文四十五万,较原编增近十万字。1985年该书出第二版增订本。来新夏说:“细读全书,犹有未尽如人意者多处,是学之无止境而我心则尚存更新之远图也。”十年后,来新夏壮心未已,在读书中每有所见,辄采登于册,又有数万字的积累,于是便又有了新编林则徐年谱的念头。他广事搜求,博采众言,终于在1997年出版了《林则徐年谱新编》,全书六十余万字,为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了重要参考书。
来新夏认为年谱是一种以丰富准确资料为基础,供人们参考与使用的著述,因此务求其详备与可靠。从《林则徐年谱》初版到《林则徐年谱新编》的诞生,来新夏几易其稿,充分体现了他精益求精的读书精神。
要把书读“薄”
来新夏读书也是“好学深思”,“博观约取”。他提倡“好学”,即在读书过程中必须全神贯注,认真阅读;还要“深思”,就是在读书过程中要积极展开思维活动。然而仅这些还不够,所以还得“博观”,要多读些书,以扩大知识面;“约取”,指善于撮取书中的精华部分。
若干年后,来新夏在《与青年朋友谈读书》中说:“要把书读‘薄’。”所谓把书读“薄”,关键是在开始读书时,先要读这本书的序或前言,然后从头到尾看一下目录,了解它的主要内容和结构。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是每一个读书人必须养成的读书习惯。
可是怎样才能把书读“薄”呢?
来新夏说的把书读“薄”,并不是指书的实体由于不加爱护而撕烂脱页,显得比未读以前薄了许多,而是指通过阅读,像海绵似地吸取书中的精华,将它储存到脑海中。这是因为无论什么书,它都有一个中心主题,然后通过文字的表述予以记录;但一本书往往又为了结构完整、篇章衔接,不可避免地会重复一些你已经掌握的知识,或是一些仅供联结呼应章节的“水分”。如果把这些重复知识和“水分”排掉,那么书就会由厚变“薄”。
来新夏还告诫青年朋友,读书,应对书中的问题进行反复琢磨咀嚼,当一个又一个问题弄明白后,就需要有总体认识,必须将全书各部分的内容连贯起来理解,经过自己重新组织整理,融会贯通,从而搞清楚什么是该书的要旨,以及各个问题之间的关联,这样才有新认识,新收获。读懂一些,读通一些,这些部分章节就不须再花费时间和精力了,这样也就会感到书本变“薄”了。
来新夏善于总结自己的读书方法。他认为正确的读书方法应该是:读书——思考——研究——运用——创新,其中的核心是思考。懒于思考,单靠死记硬背,这样读过的书,“学”到的知识是没有用的。而读书中勤于思考的另一层意思是对所读的书要有分析、鉴别,决不能盲从。来新夏反复说,要想把书读“薄”,只有“好学深思”、“博观约取”,否则便会走马看花,浮光掠影,终将如竹篮打水那样,虽然提取过大量的水,最后还是一只空篮!
黄慎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