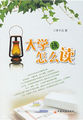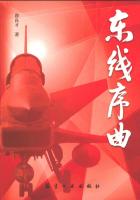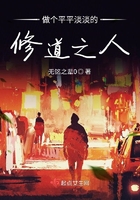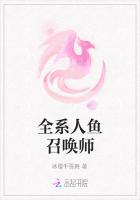沈从文(1902~1988年)作家、历史文物学家。湖南凤凰人。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著有《沈从文文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小时候只读过四年私塾,他对“四书”、“五经”并无多大兴趣,引起他爱好读书的一个原因,据称是在童年时代所接触的几部有趣的书。沈从文第一次对书发生兴趣的是五本医书,他说从中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涎液可以治愈;第二次对书发生兴趣,得到好处是读《西游记》培养了幻想。他说,使我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认为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后有了一个转变,发现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味。沈从文后来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沈从文之所以能在逆境中成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不畏艰苦、坚持读书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
从小热爱自然界
沈从文童年时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性格。
他在家乡湖南凤凰县的一家私塾读书,但是私塾里那点课文和学业使他感到读书太容易了点。别人花许多功夫才能背诵的课文,他只要临时读几遍就能琅琅上口,背得一字不漏,因此他有许多剩余精力,而千奇百怪的大千世界正好吸引了他的好奇心。于是他经常逃学。但他的逃学并非像大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把许多问题搞明白”。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自己去寻找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了,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因此只得利用白天的时间“到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闻”,到了晚上“便做出无数稀奇古怪的梦”。正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沈从文在读课本的同时,十分爱读大自然这本“大书”。尽管对少年的他来说这本大书还显得过于深奥,但他还是读得津津有味,因为“在校外所学的实在比校内课堂上多几十倍”。
儿时对大自然的热爱一直保持到成年,他三十岁时仍然觉得“社会这本大书很有益处,若把一本好书同这种好的地方尽我选一种,直到如今我还觉得不必看这本弄虚作伪、千篇一律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当去读那本色香俱全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
连夜里作梦都是翻阅《辞源》
沈从文不仅好学,而且刻苦。十五岁便离开学校到湘西靖国联军去当兵。他先后做过班长、上士司书、文件收发员、警察所的办事员、税收员等,跟随湘西军到处奔波,几乎跑遍了湖南各地。尽管他正式读书的时间少,但他能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和思考,所以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在靖国联军当兵时,第一支队一位姓文的秘书有一本《辞源》,沈从文开始对这本书不太了解,因而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后来得知这是一本“天下什么东西都写在上面,你想知道的各种问题全都写得有条有理,清楚明白”时,就对这本书十分敬畏,连夜里做梦都是常常翻阅这本“宝书”。
《辞源》让沈从文开拓了眼界,他从这本书中学到了新知识。
1922年,沈从文二十岁时作了当时靖国联军第一军统领官陈渠珍的书记官。陈渠珍自诩是曾国藩、王守仁式的军人,平常喜欢收藏文物古籍。当时陈渠珍藏有一百多幅从宋代到清朝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和古瓷,还有十多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以及一部《四部丛刊》。这些文物当时尚未整理,陈渠珍需要用书或是要抄写某书中的一些段落时,就要沈从文先做准备,因此沈从文有机会接触文物和古籍。在登记旧画时他就一幅幅仔细研究,搞清这些画的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地位;对于铜器和古瓷,则一一搞清这些器物的名称和它们的不同用途。他为了查清几十件铜器的来历,就查看《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式》等书籍,从器物上的文字及它们的形体上去辨别和考证它们的名字、用途以及所具有的价值。为了搞清这些内容,他全凭自己琢磨、思考。对于那十几箱古籍,他一本本地读下来,遇到“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
这一阶段的自学,沈从文感到收获很大,对中国历史有了基本的理解,为他后来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能买书读,比买自来水笔或镶金牙有意义多了
陈渠珍在他的靖国联军里办了报馆,沈从文又被调到报馆工作。与他同住一屋的是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有许多新书和新杂志。与他接触之后,沈从文在思想深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逐渐放弃读旧书,“向新书投降”。不看《花问集》、《曹娥传》,去看充满新思想的《新潮》、《改造》等刊物。他特别崇拜那些充满新思想的新人物,读了他们的书和文章之后,懂得了自己“应该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如何去思索,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
沈从文读书注重实质,而不是外表。对那种以新名词向人炫耀知识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外表的装饰并不能证明自己真正的实力。当时有一种嘴里镶上一颗金牙以显示自己有钱的风气,他则对朋友说:“如果年轻人染上这种风气是很可怕的”。在给一位军官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一个现代军官,单是头上有钢盔并不济事,还要同时武装脑子才够格,钢盔只能防御流弹,可并不能抵御社会中流行愚蠢有毒的观念和打算”,“军队中多有几个钱,能用来买书读,比买自来水笔或镶金牙有意义多了”。而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当他在作上士司书时,每月只有四元钱的薪水,为了练字,在五个月里就花了十七元去买字帖,他认为这是值得的,果然,后来练出了一手好字。
旁听生如饥似渴地读书
二十一岁那年,沈从文离开了家乡湘西,也离开了军队,来到北京,他非常希望能到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上学,但因种种原因而无缘成为一名正式学生。幸好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思想开放,对来学校的旁听生不加限制,使沈从文有了旁听的机会,于是选修了许多课程,如饥似渴地读书,从书中汲取了大量知识。
在北京大学旁听时他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艰苦,但他仍然咬紧牙关坚持不懈,并把这当成是对自己的磨炼。他后来回忆道:“当时住在潮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冬天零下几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次是起码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的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御力和适应力。”沈从文认为,困难和挫折都是一种考验,只有不怕失败,坚持到底的人才能获得成功。他就是在这种坚持和等待中不断创作,投稿,退稿,再创作,再投稿的。当然,他也曾有过动摇。有一次“差点儿为了果腹而想卖身当兵,但就在要按手印时,突然清醒了,意识到自己现在除了理想之外已一无所有,如果再把理想卖了,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这时,乡下人固有的倔强性格又使他回到了住处,在“窄而霉小斋”继续他的追求。
当他坚持几年之后,终于出现了转机,他的才华被郁达夫发现,在郁达夫的帮助下,稿子陆续被刊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既有了生活来源,也有了社会影响,后来成为我国自“五四”以来第一位职业作家。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做文章呢,不要怕失败。做一切事皆不要怕失败。譬如走路,跌到了,当然得即刻爬起来再走。”
李金琳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