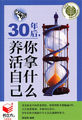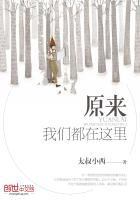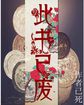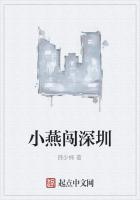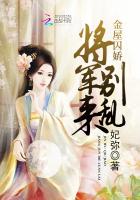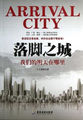钱穆(1895~1990年)史学家。江苏无锡人。50年代初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著有《国史大纲》、《国学概论》、《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
20世纪中国的通儒钱穆是以自学成名的大学者。他由乡村小学教员,走上大学教席。他的一生只是读书、写书、教书、藏书,但留下的读书和治学经验,却是一笔文化遗产。
自学十年,乡教十年
钱穆自小就喜爱学习,记忆力特强,朗读三遍即能背诵。当他还不能读“五经”全文时,就与长兄时时把玩祖父所遗手抄“五经”。当父亲为长兄讲述各种书时,他经常在枕上窃听,常兴奋得睡不着觉。家庭浓郁的文化气氛,培育了他读书求知的欲望。
钱穆七岁人私塾、读古文,每天读生字二十至七八十,都能强记不忘;九岁因老师生病失学,在家每天读书。他很爱读古典小说,其中最爱读的就是《三国演义》。熟能生巧,巧能生华,以致能通篇背诵而一字不爽,并揣摩人物个性、身份作表演。他是20世纪一百年中,也许是《三国演义》问世以来,中华神州唯一能背诵这部六十五万字巨著的学人。
一年后,钱穆进私立果育学校。在此四年间,他又接触了新学。教师曾说他“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因为作文优秀,曾获奖《修学篇》等两本书。书中选编的西欧自修成名数十人的苦学事例,对钱穆很有影响。钱穆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朝的韩愈和北宋的欧阳修,以及桐城派古文。在常州府中学堂学习期间,他还师从国文教师学昆曲、习生角,演奏也颇称职。这亦使他不断强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中学是钱穆的最高学历,但由于家学渊源与所遇良师特别多,因此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培养了好学不厌的精神。他十八岁就开始了边读书边教书的教读生涯。乡教工作既繁且碎,他却见缝插针,利用时间读书。吃饭看书,上厕所看书。家乡无锡炎夏虐蚊成灾,为防叮咬,仿效父亲纳双足人瓮夜读。乘船往返学校与家之间,常坐船头读书。晨读经学,夜读史书,午间读闲杂书,授课之余,则阅读报章杂志,有条不紊,颇见规律。他说“虽居穷乡,未尝一日废学。”正所谓是“既无师友指点,亦不知所谓为学之门与方法,故其初在冥索中努力而尤见艰苦。”
钱穆爱好读书,更善于从中汲取新知识新道理。
当年他就读常州府中学堂时,曾一度染上了抽烟的习惯。后教学的课文中有《戒烟》一篇,暗想自己抽烟,何以教诲学生?于是决心戒烟,以后数十年里再也不抽烟。过去读书随心顺意,读了《曾文正公家书》,受到“教人读书必自首至尾通读全文”的启发,此后读书每行必读,几十年如一日。又如读一本卫生书,说人之所以不长寿,大多是由于忽略了健康教育。想到祖父、父亲及不少亲戚长辈都难长寿,即引为警示,并且痛下决心,力求日常生活规律化,作息、散步都有一定时间,至老不衰。在讲授《论语》课时,正好读了《马氏文通》、《文通论字法》,即仿其例论句法,写成《(论语)文解》一书,这是钱穆的第一部著作。再如读《墨子》,开卷就觉得有错误,愈读愈难,就逐条列出错误,加以改正,成《读墨阖解》一稿。但考虑到《墨子》乃名著,传世已久,此类错误应当早就有学人指出,试翻《辞源》,知道有孙诒让《(墨子)闲诂》一书,急忙设法找来读,果然发现自己所指出的有错之处,《闲诂》都早已经指出,并有详确证据。孙诒让读书精博,令他叹为观止。认识到自己孤陋幼稚,从此更力求精进。
1922年秋,钱穆在厦门集美学校高中部与师范部毕业班任国文教师。开课首讲《曹操述志令》,此文千百年来都未曾引起文人的重视,而他却认为:此文显示了汉末建安时代古今文体一大变,言之凿凿。学生听后,大为佩服。
要能读常见书,而又从常见书中见人之所未见
钱穆本乃一介书生、读书种子,常自勉而又勉励学生:课程可以毕业,学问不易毕业。他确实做到了孔子所说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先后在各大学任教授或兼课,以炽热的情感和令人折服的评议,把听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每当下课,同学们陪着他边走边请教。在这种时候,他解答疑难,还教人以读书治学的方法,这比课堂听讲,得到的益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对学生说:“有些书,像《史记》、《通鉴》,要反复读,读熟,一两遍是不行的。……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学无止境呀!应该着力的,一是立志,二是用功。学者贵自得师,只要能立志、能用功,何患乎无师。我就没有什么师承呀!”
钱穆于读书之道,真可以说是深知个中三昧。他针对学生读书贪多求速,不求甚解,反复要求他们要注意从从容容地读书,要有耐心,要细心体味,不能只顾翻书,只为查找需要的文句而读书。又谆谆教导学生:根基要扎实,要能读常见书,而又从常见书中见人之所未见。他不赞成读书急功近利,认为读书多了,知识积累多了,自然而然会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时就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受,写成文章,也就必然能言之有物,发前人所未发。他还告诫学生说:想要速成,想要走捷径,是做学问的大忌,应当认识到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应当懂得“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登高望远,登泰山而小天下。钱穆谈论读书常以登山作比喻。他常说,读书有如游山一般,要能专心致志,心无二用,自然能从中感受到大乐趣。还说:读书如登山,拾级而上,每登临一个山峰,俯视山下,必有不同,登至顶峰,然后方能领略一个全新的境界,方能“一览众山小”。读书越多,思考的问题越多,就能触类旁通,进入不同的思想境界,不至沾沾自喜于一隅之得。1950年他在香港新亚书院,有次课后,一位学生向钱穆请教如何做好笔记,他回答说:“做这种笔记的工夫,是一种训练。但是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而见解有不同时,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步的研究。”这其实也是他多年来读书的一种方法。
纸上得来终觉浅,方知此事要躬行。钱穆的读书经验,是他七十五年教读生涯智慧的结晶,学生得其教诲,一生受用不尽。
梁晋晔同济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