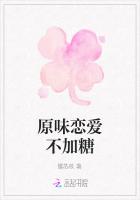张恨水(1895~1967年)作家。安徽潜山人。曾任南京人报社社长,重庆、北平《新民报》副刊主编。建国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著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
张恨水著作等身,他虽是报人,却以通俗小说名家而誉满华人世界。他是中国写小说最多的作家之一。
长期以来,张恨水保持每天五千字的写作速度,他著作盈百,计三千万字,很大程度是靠坚持读书,时时“充电”,打下深厚的文化基础。因为频繁地读书、写作,常恨时间不够用,因而写第一部小说即取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取笔名为“恨水”,久而久之,他的本名张心远却很少有人知道了。
读小说正文,也读批注和书评
正如20世纪早期的许多学者作家,张恨水也经历过私塾时期。早年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也读过《左传》、《论语》等典籍。据称,他儿童时代读书速度很快,半年就读了十三部。读这些书多不求甚解,但因背得很熟,却也为日后写作应用带来了方便。50年代后,张恨水虽多次患病,但当子女要他背《古文观止》时,仍能按指定背出其中任何一篇。
张恨水少年时候热衷于读中国平话小说。
1905年,年方十岁的张恨水随父由南昌赴新城(黎川),在拖船上偶尔翻到一本旧书,就极有兴致地读了起来。这是他读的第一部小说《五代残唐演义》,也有说是《薛仁贵征东》,虽然它们都属三四流作品,但起伏的故事情节还是能吸引人的,从此他就迷上了小说。
对他少年时代很有影响的一部书是《三国演义》。
这部书开始是在塾师桌上偷看到的,越看越有味,其故事日后常使他浮想联翩。六十年代初周瘦鹃为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题字“明明者月”,女儿不明其意,张恨水就指出此出自曹操的诗,“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后来张明明大学毕业在四川劳动锻炼,四川在古代曾是三国蜀汉所在地,张恨水在给女儿的信中,对绵竹、绵阳、梓潼和剑阁等处的古迹,联系《三国演义》一一作了介绍。
少年张恨水几乎读遍了明清平话小说。他曾在两个月里读完了《西游记》、《封神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十余部小说;后来又通读《红楼梦》,因为对《红楼梦》感兴趣,若干年后还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情有独钟,与几位老报人整天讨论、考证。
张恨水读平话小说相当认真,常人只读正文,他不但读正文,也读批注和每回前后诸家书评,由此懂得了许多作文之法。
熟读平话小说,对书中若干情节和角色印象尤深,致使张恨水在十三岁就写过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是给弟妹读的,其中情节和人物,都是模仿他以往读过的平话小说。
少年时代熟读的平话小说,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日后的创作。
《木偶奇遇记》故事开头好
但对张恨水日后写作产生直接影响的却是林纾翻译的欧美文学名著。张恨水读林译小说始于1909年在南昌大同小学期间。当时的小学校长是维新派人物,教书常嘲笑那些捧读孔孟经典的学生。当时张恨水于新学知识是一穷二白,常成为嘲笑对象。为此,他订了一份上海《小说月报》,并认真阅读所载的林译小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西洋文学,通过比较分析,从中找到中国平话小说所缺乏的细腻的心理和时空描写,日后他将这种西方文学的写作技巧,应用于自己的创作。所以张恨水的章回小说虽源于传统小说,但刻划细腻,人物形象逼真,呼之即出,就是得益于林译小说。
为了从原著中直接汲取文化精华,张恨水也很重视学英语。他自学英语三十年。
20世纪20年代,张恨水为补习英语,曾在商务印书馆英文补习学校上课,后因感到进度缓慢,打算自聘教师每天教读,因家人反对,而自己也力不从心,便打消此念,但仍坚持自学。据女儿张明明说,张恨水为学英语,每天早晨高声朗读,音调响亮。
依靠坚持不懈的自学,张恨水取得了不错的英文成绩。他曾在重庆《新民报》发表以歌行体古诗形式所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商籁体);在市郊南温泉草房居住时,就以意大利科罗狄童话《木偶奇遇记》英译本为自学蓝本,并向子女们口译;先念句英语,又译为中文,中间还常插以诙谐的语言。他很喜欢这部为儿童写作的世界名著,对子女们说,这个故事开头好。通常西方故事开头,总是一个皇帝或皇后,然而这里却是一块木头,这就是动人之笔。
张恨水通过向子女口译精读了全本《木偶奇遇记》。
晚年打算读完《四部备要》二千册
张恨水出名后,应酬频繁,然写作不断。据说20年代在北京时,一天要同时为六家报纸写六部连载的长篇小说,其中就有《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有时报社派人前来催稿,他即凭几而作,文不加点,一气呵成。
多年的超负荷写作,促使他必须不断充实知识。因此他规定每天都须阅读一个多钟头的新书,雷打不动。据他儿子回忆:父亲终日手不释卷,连在重庆躲警报时,都要带本书去读。在他书桌上经常堆积很多书;其中也包括与文学相关的诗律词谱、历史传记和画论字帖,书房四壁是书柜,有条不紊分门别类排列着大大小小的书籍;对这些书,他几乎都能说出每本的内容。
张恨水是有计划地读书的,他读书与写作内容有关。开始写作《梁山伯和祝英台》时,即以半年时间,集中阅读了三十多种文献书籍。因为作品文化背景定位在晋代,因此他对书中要描写的晋代各阶层的衣着、用具等都作了缜密、细致的考证。
张恨水是位严肃的作家,他也非常注意自己的文学修养。早在1928年他在《世界日报·明珠》版连载《金粉世家》时,就将自己积累多年的写作经验,列为《作小说须知》十条:一、研究社会,了解周围人物的环境;二、养成细心观察习惯,不要闭门造车,要出去走走;三、学会绘画摄影技术;四、学一种外国语;五、读古诗;六、有一般文学知识;七、注意戏曲艺术;八、掌握科学技术;九、研究最喜爱的动物;十、熟读中外文学名著五十种。这十点都间接或直接牵涉到读书与创作的关系。
60年代前期的张恨水,已如秉烛夜行之老人,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仍是离不开读书。他想在暮年读完二千余册的《四部备要》和太平天国史料,还打算阅读、研究巴尔扎克、契诃夫和马克·吐温等作家及其作品。读书伴随了他的一生。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