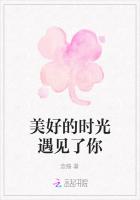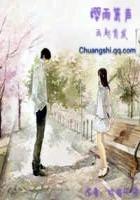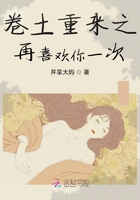刘海粟(1892~1994年)美术家,美术教育家,江苏常州人。著有《齐鲁谈艺录》、《存天阁谈艺录》和《欧游随笔》。
刘海粟是我国现代绘画的先驱者,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六岁进家塾识字读书,八岁开始学画,十七岁就创办上海美专,并提倡人体模特和人体画展。他以“不怀庆赏爵禄,不顾非誉巧拙”自励,努力发扬传统画学,创新立说,为弘扬中华文化,沟通中西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做出了贡献。
大画家必然把读书作为提高自己专业修养的途径,在他长达三分之二世纪以上的艺术生涯中,绘画千幅,著书立说,留下了一笔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绘画想出色,必须有学问”
刘海粟童年得益于母亲洪淑宜的教育。洪淑宜是清代大学者、人口学家洪亮吉的后代,她是儿子的启蒙老师,教他读书识字,给他讲古人勤奋学习的故事。其中刘海粟印象最深的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诗仙李白的才华,杜甫的在离乱中饥寒交迫仍不废苦读。母亲还向刘海粟介绍洪亮吉的好友黄景仁(仲则),黄景仁是乾隆年间的大诗人,虽只活了三十五岁,却留下了两千多首诗词,还有不少散文骈文。母亲的故事给刘海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后他多次通读黄景仁的《两当轩全集》。80年代初,当黄景仁的后裔黄葆树为常州筹建黄仲则纪念馆前来求取墨宝时,他欣然书写“两当轩”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并打趣地说,一个字可值一千元哩!还与黄葆树闲谈了黄景仁诗词中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等佳句。
刘海粟早慧,他比一般同龄人似乎更早意识到读书的重要和宝贵,及至开始学画,族里长辈给他送来《南田诗抄》、《南田画跋》、《爱石山房刻》等书,对他鼓励有加,刘海粟当时虽看不懂这些古书,但却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绘画想出色,必须有学问”。
刘家是江苏常州大族,书香门第,自然藏书不少,父亲的书房,成为刘海粟寻找快乐的天地。儿时的勤奋苦读,使他后来得益匪浅。
刘海粟少年得志,艺术作品阔厚雄奇,深得康有为的赏识,并收他为弟子,在书法上给予指点。每次刘海粟到来时,康有为都叫人磨好了墨,刘海粟一到,就予以示范,并让他广读各家各派碑铭,自己悟出道理,还要他读《历史画论》。刘海粟通过那段时间的研习,颇有心得,并悟出一个道理:临碑不读书,至多得古人皮毛,字匠而已。习字,得转折、停顿、收缩之法不难;而健筋骨,血肉丰满,有个性则甚难,惟有书外求之。刘海粟苦下功夫,在勤练书法的同时,博览群书,先写《石门颂》,再写《石门铭》,力求风骨棱劲;继而苦练《灵庙碑阴》及魏碑中最俊秀之《六十人造像》,得苍古沉雄之趣,并深研《历史画论》、《书镜》及各家各派之名著,扩大知识面,把胸中诗书融入笔下龙蛇,后来终于做到气高志洁,心有巨眼,下笔自然超拔。
要求临摹十幅古典名画
1921年,二十九岁的刘海粟两次赴海外考察,他的东瀛之行时日不长,却收获累累。在日本,他重逢了画家张善子及日本画界著名画家小室翠云、关东画派领袖桥本关雪、收藏家工农大臣山本悌二郎,并应邀去他们的别墅作客,观赏了他们收藏的世界级画家罗丹、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的原作和从我国流失的古代艺术珍品。天外有天,这次考察使他大开眼界,终生难忘。画家观画犹如学者读书,日后刘海粟常常以此为题和艺术界友人交流对古今绘画艺术的认识,并称鉴赏名画,亦所谓读经验之书也。刘海粟还应邀到东京《朝日新闻》作《石涛和后期印象派》的讲演,他所论证的在二百多年前石涛就发现塞尚所探索的绘画奥秘,被小室翠云誉为“20世纪东方最伟大的画论”。
1929年,刘海粟在巴黎连日参观了博物馆、教堂、宫殿、画廊、展览会等,过去他在书本上向往之杰作,现在得以直接观摩,并往卢浮宫临摹前代名作,拜访巴黎艺术巨匠马蒂斯,还见过毕加索、凡·达利、特郎等大画家,同野兽派画家们交流用原色作画的经验,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画的线条。
刘海粟在日本留学,并不局限于艺术创作领域。1934年4月的一天,卢浮宫前面的外国作家博物馆,举办日本绘画展览会,刘海粟偕数友人前去参观。画展中有许多日本第一流的画家作品,他们的画虽然有一定水平,但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同行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画展是日本式的布置,富丽堂皇,装裱精致。日本绘画展览会开幕后,震动了巴黎,艺术界认为日本绘画达到了世界艺术高峰。刘海粟与留法同学听了,无不难过,想到中国只因政府腐败,不注意对外宣传,致使欧洲各国不了解中国现代艺术的高超水平,遂与高鲁、汪亚尘、方君璧、张弦等画家筹备旅法中华艺术协会,积极宣传中国艺术及文化。自从旅法中华艺术协会组织起来以后,刘海粟的学习、工作都更忙了,每天上午六时到九时去卢浮宫临画,下午在格郎休米亚画院选修人体和速写,晚间还要给《申报》写《欧游随笔》,并且还要每天抽出时间与协会会员交换意见。这就需要“充电补血”,要大量读书,以提高艺术修养。“一副西洋画是一副画,一副中国画则是一首诗,自然只是供给它以素材而已;不要以为这些花草木石……是中国画极盛时代的艺术家随便高兴造作出来的,正是相反,需要长年的苦工磨练,学习和观察……因为中国思想更重哲理,不能容纳没有心灵的物质……”
刘海粟在海外游学时,把临摹画作为提高自己绘画技巧的重要手段,他向巴黎市美术馆管理局写了申请书,并递交中国大使馆的保证书,要求临摹十幅古典名画。在取得了摹写证后,除了星期日因美术馆闭馆休息以外,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他都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可是在临画过程中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曾经多次看到过这些画的印刷品,似乎很熟悉,但一旦临摹起来,几乎都要经过认真思索才能画下每一笔,而且这仅是形似,难以做到神似,因为每一幅画都凝聚着画家特殊的思想感情。书山有路勤为径,几乎每一个夜晚,他都和挚友傅雷同坐灯前,翻阅艺术史论文,有关画家的日记、书信以及传记,以便在临摹画作时加以体验。工夫在画外,随着刘海粟全方位修养的提高,绘画的境界也大大提高,他因此更加体会到阅读的重要性,在画画之余,把很多精力都投入了阅读。
海外的观摩,使刘海粟绘艺大进。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告诫青年人说,艺术家的成功要靠自己努力,“倘若能够到国外去看看尤其好;美术馆、图书馆收藏的丰饶,更可供给你无穷无尽的探索。”
绘画如行路,从无止境
刘海粟艺术的一生,也是游历的一生。青年时期,他几度游学欧洲,在考察东西方绘画的基础之上,综览东西方绘画发展的潮流,取精用宏,融会中西。他曾十上黄山,每次都有新鲜感,还常在登山途中临风朗读《徐霞客游记》。刘海粟登黄山,留下的速写、素描、油画、国画,大则丈二巨副,小则册页,如果汇集起来,可足有一大厚册。他常喜欢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说明绘画如行路从无止境。1929年,他在瑞士,为瑞士和莱梦湖的天光水色,峰峦映美神往,由此联想起欧洲许多画家如米勒、哥罗等以及中国古代画家如王维、荆浩、李成等人都是得江山之助而成为一代画宗的。所谓“黄子久(公望)每日看富春江,领略江山钓滩之概,探虞山知朝幕之变幻,四时阴霁之气韵。倪迂(云林)浪迹五湖,而成其幽澹疏萧之趣。”刘海粟赞同董其昌所说:“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而欲成画祖,得乎?”由此而提出,气韵不可学,生而知之,自然天授,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勉强学之耳。
针对当时艺坛有人堕落,浮浅虚伪,或一味复古和崇洋,正如鲁迅与章衣萍等人所批评的:“有些留学生到日本去留学,到了日本以后,就关起门来炖牛肉吃,在日本住了几年,连日本话也不会说,更不用是看日本书了。”刘海粟提出每个有志学艺的青年,“只有君子求诸己的一法,大家拿出勇气多读书作画,多跑山川,先将根底做好,自然就能自由发展你的天才,读书要走路,才能读好书;走路要读书,才能走好路。”刘海粟自绘画以来,将这个朴素的道理贯彻了八九十年,以致有一次,英国远东大臣达夫古柏向他提问:“中国的水墨画实在太高深了,请问作为中国画家,如何才能取得艺术上的高深修养呢?”刘海粟回答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孙金滟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