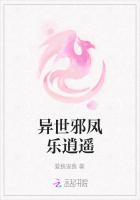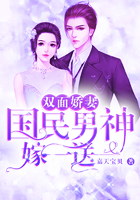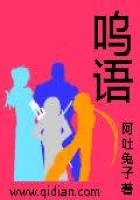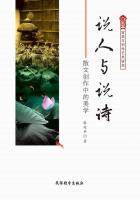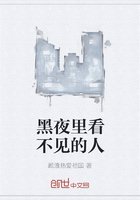谢六逸(1898~1945年)新闻学家、作家。贵州贵阳人。留日。创办复旦大学新闻系,任主任。主编《立报》。著有《新闻学概论》、《中国小说研究》。
谢六逸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20年代中期,新闻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的时候,他就在上海复旦大学创建了新闻专业,成为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谢六逸的知识面还涉及到日本文学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和创作,他的读书领域是很广泛的。
读书在乎季节的变化
谢六逸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学问很好,所以小时候没有进过私塾,完全由他的父母教。他对书籍从小就有一种癖好。在家乡时,由高小到中学,从没因为读书的事使父母生气。十三岁时,就常常跑到父亲的藏书楼上去翻书,从早晨到天晚,只下楼吃两顿饭。小小的年纪看《绿野仙踪》、《飞驼子传》,书中的谚语很多,弄得莫名其妙,但仍看得津津有味。中学毕业后,公费到日本留学。在留学时期,他说有两个地方我永远不能忘记,一是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二是东京郊外的吉祥寺,就是在这两处地方他读了好多书。他视读书为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可一日缺少的。
谢六逸在长期的读书生涯里,养成了一种与常人不同的读书习惯,他在《读书的经验》一文中说道:“我看书不怕喧嚣,孩子在身边吵闹也可以看下去,有几次我看书时,太太在我的旁边对我说话,我完全没有听见,因此尝受非难云。”“我读书有时作Notes,有时用铅笔在书上乱涂线条,有时从头到尾没有作什么记号。”
谢六逸读书在乎季节的变化,他说:“夏天和秋天是我读书能力增进的季节,春天也还可以,我最憎恨冬天,我最痛恨的,就是‘围炉读书’躺在沙发上读书等等调儿。我的信条是多读,深思,慎作。”
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读书
谢六逸教了二十六七年的书,尽心尽责,他对学生们很和气,用心指导他们。每当新学期开始,首先要和学生谈的是: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读书?该用什么方法读书?“这些问题要触动我们的脑筋,要引起我们的思考”;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们:“人生的黄金时代是青春,俗话说的好:‘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禄爵,何处买青春’,西哲拉凯尔也说,‘常保青春,为人生无上幸福,欲享此种幸福,当死于青春之中。’古往今来骚人墨客,对于青年,无不加以最高的赞颂。因为青年有沸腾的热血,有进取的勇气,有坚忍的毅力,有耐劳的体魄。正因为青春的可贵,我们得利用青年时期的智力体力,充分发挥我们的求知欲望。试想一想,我们不读书,我们将感到空虚,将感到生命的无所寄托,我们青年的力量更不易表现出来,此时我们放弃了读书的机会又将何以自慰呢!为求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绵延,我们不能不埋头研究。每值太平盛世,学术易于发达,历史上不乏其例。即所谓艺术之花,常开放于和平的园囿。”
“一切事物必有它的变化发展的法则,只有问答辩难始可明白它的意义。愈问答辩难而真理愈明。”谢六逸针对青年读书不主动提出问题的缺点,语重心长地教诲学生们:“我们发问辩难以解决人生宇宙的许多疑问符号,解决之后,此一问题可储积起来,作为我自己的营养料。我们后一代的人必须从前一代接受其优秀部分的遗产,化作我们新的血肉,然后我们才能成就新的发展。”
谢六逸在他的作品《茶话集》中也讲到了读书的方法,他说:“关于读书,我是主‘立读’或‘行读’的。”还形象地描绘着,“日本商店里的小伙计,骑在脚踏车上面,一只手驾驭着车柄,一只手拿着口琴吹奏着《嘉尔曼》中的小曲,这样的‘吹口琴的艺术’,移用为‘读书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读书的趣味。还有在散学归来的中途,站立在书店的杂志摊旁边,‘揩油’翻阅儿童杂志的日本小学生,才是真正懂得‘读书的艺术’的人。”
谢六逸主张读书面要广,认为只读国内名家的作品是不够的,还得多读在世界已有定评的各国作家的作品。他说,我们欣赏一部伟大的作品时,就无异和作者伟大的人格、丰富的阅历相亲近。不单在艺术方面获得益处,同时对于如何观察人生社会,如何思维,也能得惠不少。读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最好是先读一两个作家的全集(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全集》、《易卜生全集》等)。读时尤贵一字一句的慢慢地吟味,寻绎它的佳胜处。
他说:“在青年时代,我们的生活体验是有一定的范围的,故不能不借助于书籍,用于观察或吸收现实,把我们从小范围的生活圈子里面解放出来,认识真正的人生社会。要做到这一步,就得从储积知识着手。”
写作:劝用“卡片制”
谢六逸是新闻学家,编过好几份报纸的副刊,并且编得相当精彩。在那么小的一方篇幅里,他竟编得十分活泼,常有好文章给读者。据说,他在上海办报时,每年元旦,就要收购当天出版的报纸刊物,多多益善,一一认真阅读。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尽心,他说,元旦这天的报刊,都是呕尽心血组稿和编排的,为给读者一个新面目,现在能够集中在一起阅读,这真是事半功倍的好机会。当然,好的文章不仅来自于他成功的读书,还来自于勤奋练笔,正如他在《茶话集》里所写的“我们要有柴霍甫、德富苏峰的毅力与决心,才配称‘写作’。我们应该十分地忍耐与审慎,必须要写坏了十几册的笔记簿,将几百张的稿纸,写了又撕,撕了又重写,始可发表一篇作品。”
谢六逸和青年们谈写作方法:“我劝诸君用‘卡片制’。让我们买了若干厚纸片放在抽斗里,把我们每天的见闻感想,都写在卡片上。凡是五官所感触的,直觉所想像的,都得写上卡片。每天不论写完几张,随手把它放在抽斗里。日积月累之后,所积的卡片应该不少。在星期六的晚上,把卡片慢慢地整理,真有一种乐趣。如果计划写巨大的长篇,用这个方法搜集资料,也是颇适用的。我在上海教了五年的书,一向就用‘卡片制’搜集教材,并记录我自己的研究与意见。不过,卡片制只是写作的准备,材料准备好了,还得写在有格的稿纸上。在整理卡片时,应该舍弃的陈旧资料,便随时舍弃;有新颖的资料,便时时加以补充,自问能幸免于‘留声机器’的讥评。这个方法用来练习写作,在搜集、整理诸点上,是有效的。”
黄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