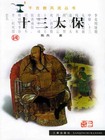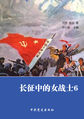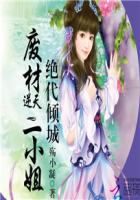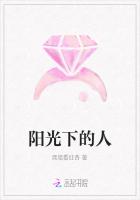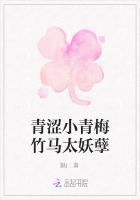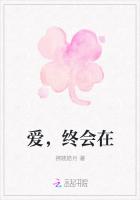在那样的家庭里,蔡妈妈是不做菜的,蔡康永也从来没有吃过妈妈做的菜。说到这里,要插一下嘴。在上海,贵族的大小姐是不做菜的,却“说”得一口好菜。蔡妈妈不会做菜,只会“说”菜,因为所有的菜,她都是“听来的”。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这一原则,蔡妈妈是严格遵守的。
言归正传,虽然蔡家逐渐没落,但是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台湾的蔡家依旧排场不减。小蔡康永随手抓起的食物不是鲍鱼就是鱼翅,家中天天衣香鬓影,夜夜笙歌。这日子,好像生活在一个不需要钱的世界似的,因而蔡同学一直对钱没什么概念。
蔡康永在自己的《痛快日记》一书中说:“这样的场面,偶尔看一次,当然很有趣,可是如果经常看、看多了,就自然而然,懂得‘无常’是什么了。我就是这样懂得‘无常’的。”
显然,他成长的家庭跟一般孩子的家庭很不一样。这个家庭终究逃脱不掉上海没落贵族的影子。这一点,从蔡妈妈的一日活动就看得出来。蔡妈妈每天睡到中午12点,穿着毛毛边的亮片高跟拖鞋、好莱坞电影里女明星穿的丝质晨袍,在家里晃了一下,起床后不吃东西,就出门弄头发,弄到下午两三点回家,等朋友到家里打麻将。
有一次,蔡康永和王家卫聊天。王家卫说,他对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所知和迷恋,来自于在夜总会工作的父亲。蔡康永回了一句让他差点跌倒的话:“你戏里头的旗袍,好像跟我母亲的还不是一个路数。我母亲的旗袍,领子竖得比张曼玉更高。”可见,蔡小孩的家庭还是蛮“上海”的。
蔡父蔡母几近半百,早已不是二十几岁生子时的那种状态了,对小康永就像对宠物似的,过得去就OK了。有一次,蔡妈妈跟小康永开玩笑,叫他离家出走,可怜的小康永只好一边哭一边回房间收拾行李,搞笑的是因为从小就有专门照顾他的保姆,所以他连抽屉都没有亲自打开过一次。生平第一次亲手打开抽屉,看到一件绣着二条龙的小背心,觉得这个很好看,就拿出来包了包,带着这一件衣服到客厅跟妈妈道别。妈妈还说,好呀好呀,走吧。小康永只好一边哭一边拿着只装了一件衣服的小包包开门要走,还好碰到刚下班回家的蔡爸爸,头正好撞到爸爸的皮带扣,看到回家的爸爸,哭着说要离家出走。结果,宠爱康永到不行的爸爸把妈妈狠狠地骂了一顿。
别的孩子有父母陪着学打球、学游泳啊,他却只有应酬啊、礼物啊等等这些东西,而且他的父母更像是他的爷爷奶奶。蔡康永说,没落家庭的孩子有一种难得的轻松,没有什么光宗耀祖的压力,因为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从前。
蔡康永曾说,他的童年很苍白,甚至等于没有童年,因为看的都是浮华的东西,孩童应该经历的乐趣他统统缺失。“家人对我的好,是那种客套的好。我沉默,甚至从来不和母亲谈心事,但是从小便懂得投其所好。我只是一个玩具,供他们拿出去炫耀。”2010年8月他接受《申江服务导报》专访时这样说。
小康永家里,客人永远比亲人多,访客可以用川流不息来形容。虽然都面带微笑,却冷淡到极点。而且大自己半百的爸爸总是无法忘却在上海种种的好,所以在一些认知上,不可避免地给小康永泼“冷水”。在家中,吃一条黄鱼,蔡爸爸都会念叨半天,说不及上海的黄鱼好。小康永当然不能体会爸爸的感情,但是在他眼中,那些值得赞赏的美好事物,到了父母眼中却是次等替代品,这种心理巨大的落差可想而知。
有一次,小康永和蔡爸爸被邀请去吃大饭店的自助大餐。小康永陪着爸爸排进队伍,拿了只瓷盘递给爸爸。蔡爸爸却叹了一口气说,“上海人不吃自助餐”。小康永很好奇,就接着问爸爸原因。蔡爸爸一本正经地讲:“端着盘子排队才有得吃,只有乞丐才这么落魄。” “噌”的一下子,小康永背脊一冷,好像看见大雪纷纷无情飘下的场景了。
一个事事惊奇的小孩子,一天到晚总有人来泼冷水,久而久之,不养成冷眼旁观的个性都难。所以,小康永过早地、不合时宜地就领悟到了一种“过眼云烟”的沧桑。难怪熟知他的张小燕要说他外表年轻、灵魂古老了。
蔡康永的好友,主持人汪用和也曾说:“他的冷和距离感,来自他的聪明,而他的聪明在于看透、看清楚了人与事。但他没有因此放弃生活,做事也一定做到最好,以至于他的冷和距离就变成一种美感和优点。”
还好,除却川流不息的访客,喋喋不休的麻将声,世界上还有一种陪伴孩子走过孤寂岁月的发明——玩具。儿时的那只握着一口铁皮锅子煎着铁皮荷包蛋的铁皮小猪,构成了他童年里零星的温暖回忆。他还心血来潮想为那只小猪设计出格公仔来着,他说那铁皮小猪“好像一只神经病小猪,锅子里有煎不完的蛋”。
你猜,他说这句话时,开心吗?如果可以选择,他会选择怎样的童年?
因为家庭地位在那儿摆着呢,所以蔡康永上学的地方也马虎不得。
能让蔡同学待的学校,那不是一般的学校——台北市知名私立贵族学校“再兴”,他在那里度过了从幼稚园到高中的14年学生生涯(幼稚园2年,小学、中学各6年);能和蔡小康做同学的,那也绝不是一般的人——身边的同学大多出身名门,有辜家、蒋家后代,有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医院院长等人的孩子,不是高官就是台湾地区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皆是政界要人和上流社会的小孩。名牌跑车和阿玛尼,清一色的名门权贵家长和老师,让蔡同学以为世界全都是由这群人组成的。蔡同学真可谓是“含着金汤匙出生,裹着金棉袄混世”。
小学一年级的蔡同学,连“考试”是干什么用的都搞不清楚的,非常无知。稀里糊涂考了第一名,自个儿却还不知道。不过,他这个第一名却是非常“实惠”。
话说,这天蔡同学跟往常一样回到家里,正好碰上妈妈的麻将盛会。按照妈妈的指示,规规矩矩给每位阿姨伯母打招呼问好,之后他正准备一溜烟跑掉时,妈妈又叫住了他:“考试第几名啊?”看似无心的一问,其实也就是想向那些姨母炫耀一下。蔡同学这时不知道“第一名”为何物,就直接把考试成绩单交给了妈妈。蔡妈妈一看,满脸喜色,惊呼:“第一名啊!”蔡同学的众位姨母,也都齐声欢呼,好像麻将间“清一色”的场景。这时,蔡同学才明白,原来“第一名”的威力可以和“清一色”的威力相媲美。众位姨母也很自觉,纷纷给他发红包。从此,蔡同学对“一”建立起了良好的印象。
九岁那年,蔡康永演出京剧《四郎探母》,饰演杨四郎,获得无数掌声,剧照登上台湾地区《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头版。当时《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王惕吾和余纪中是父母社交的好友,家中的常客,蔡家儿子登台演出,捧场那是必需的。不然,那么多掌声从哪来的?小康永的“应酬”也不是白去的。看来“多个朋友多条路”,这句俗话果然说得不虚。
在这出《四郎探母》的演员表中,你会看到史上最怪异的一幕:演杨四郎的有两位,“候补杨四郎”则有八位,而杨四郎的外国妻子铁镜公主一名,候补铁镜公主也有八名。这不像是一张京剧演员表,更像是自杀特攻队的队员名单,仿佛每五分钟就会阵亡一名,需要马上替补,非常悲壮!其实这张演员表,就是那张交错复杂的社交网,名单上的孩子,父母都不是好惹的!
蔡同学之所以去唱京剧,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家里“无架可打”,穿上戏服画个花脸就可以名正言顺打架去了,他当然乐意了。他是谁啊,家中的小王子呀,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了,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去招惹他。为了打架,去唱京剧,也算是蔡同学的独创。
其实,他可以唱京剧,是在七岁那年,用“第一名”跟蔡妈妈换过来的。话说,年幼的蔡康永经常会被蔡爸爸带着去看一些表演。那些表演,总是杂七杂八的,有中国人变魔术,也有外国人走钢丝。有一个晚上,去看一个酒店夜总会的表演,台上竟然出现了京剧表演的“孙悟空棒打金钱豹”。小康永被深深吸引了,原来还有一种表演叫京剧,原来在京剧里,可以拿着金光闪闪的棍子降妖除魔哈!这之后,小康永就对京剧“念念不忘”。
终于有一天,“深思熟虑”之后,小康永向蔡妈妈提出演京剧的要求了。蔡妈妈答应了,前提是小康永考试要考第一名,然后就让他“演京剧,打架的”。果然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小康永顺顺利利地拿到了第一名。蔡妈妈也真的去找剧团衣箱师傅借来戏服,为小康永拍了一套“京剧打架写真集”。
小康永估计非常过瘾,因为给他拍了中国野史上最爱打架、最会打架的三个家伙:三国故事的马超、水浒里的拼命三郎石秀、专克匪类的侠客黄天霸。这次只是摆拍,到了小康永九岁的时候才“真枪实干”,在学校里真正开始学了京剧,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四郎探母》那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