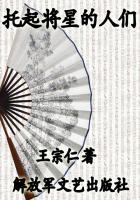到了那个像小码头一样热闹的庙南波时,我竟有点小紧张,此处仿佛一道关口。像往常一样,这儿或站着、或坐着、或蹲着一些山民,年老的,年轻的,还有几个嬉闹着的孩童,他们或者闲来无事,或者多少有些小事,聚到了这里,拉呱儿,下棋,打牌,玩耍,做针线活,望天儿,顺便看看过往的人,见我这么一身打扮走过来,认不认识的都跟我打招呼,我不知拿什么话回应,只是冲他们微微一笑,点了点头,算是致意了。
那个小卖部的王老虎嗓门最为响亮:哎,作家,今天穿得这么利索,这么整齐啊!你这又是干什么去的?
这是眼下我最不想被问到的问题,我当然不愿将真情告白,但是人家问得那么认真,你就不能再回避了。我笑了笑,很有些含糊地答道,我到下边去,随便转悠会儿。
我看你又是去采风,去体验生活的吧?那王老虎咧开一张镶了金牙的大嘴,和善地笑着,不依不饶地追问道。这个显得很可爱的老家伙时常上城进货,偶尔弄本破烂小说之类的翻翻,他知道也会使用这种显得很有点文化的词儿。
呵呵。我只好再次朝王老虎们微笑着,脚步非但未作停留,反倒是加快了步伐,一副仓皇逃离的样子。实话说,眼下我不想,不必,也不敢道出实情,一是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二是怕引起误会,若是你说要走回商城去,他们肯定以为你这个城里来的作家犯神经病了,善良的山民有可能纷纷上前拦住你,甚至动手拉你回来。在这些敦厚纯朴的山民面前,你没什么好张扬的,反而是有些心虚了。眼下,你所能做的,只是赶快逃离众人的视线。不过我能够感觉到,一群目光还在后头追赶我。
过了一关又一关,路口也是一个关口。这里停泊着几辆颜色不一的破车,车主是石柱兄弟的哥们儿,他们守候在此,随时准备把山上的人拉到山下去,再把山下的人拉到山上来。看到我匆匆走来,当然以为我是要乘车下山的,就乱招呼我,问我要到哪儿去,说车马上就开,请我稍等一会儿(通常他们是要等车挤满了人才开的),其中一位似乎跟石柱的关系更铁一些,可能是他考虑到了作家的时间更宝贵,宁愿现在就走,只拉我一个人下山。
我微笑着谢绝了石柱兄弟的哥们儿,只得又撒了个谎说,我不坐车,不坐车啦,我只是到下边随便走走。
说是随便走走的,你就不能走得太快了。不然,似乎就对不住那几位诚心想拉你的兄弟,至少在走出他们的视线之前,你得做出那种溜达的样子来。于是,我就强压着步伐,压抑着急迫的心情,把那一小段时间和道路晃悠了过去。
拐过了一道弯,浓郁的树木,高耸而连绵的石壁,像一面巨型的墙遮住了我,回头望一眼,哪还有车和人的影子?现在好啦,就像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行进到了开阔地,我禁不住甩开了胳膊,迈开了大步,甚至扯开嗓门唱了起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高声唱着,还高举了几下手臂,像是在宣誓,或者是发誓,有点像个就要奔赴沙场的战士的样子了。
一二一,一二一,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样子,意识到了自己这样子有些夸张,但并不觉得多么可笑。是啊,接下来的漫漫长路,对于你这平淡无奇的人生来说,不就像一场活生生的战斗吗?而且你不可能速战速决,它是一场持久战呢,艰苦卓绝是少不了的。现在,我就是一个出征了的战士,当然得有一个战士的姿态,当然是要斗志昂扬的。不如此,不如此想,不如此做,你有把握走完下面那遥远的路途吗?哦,我知道,我也能够想象得出,艰难险阻和辉煌的胜利都在前方等着我呢。
朋友啊,我看你还是不必这样吧,不必这样庄严,不必这样严肃,一切都没那么严重。别刚一开始就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别搞得太像那么回事(如同别把小说写得太像小说,别将生活弄得太像生活了一样),别太虚张声势了。那样不好,会把自己搞得很累,弄得自己很紧张的。不妨把心态放得平和些,再平和些。你不就是走个路吗?不就是走一趟远路吗?不就是要走回商城去吗?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走就走嘛,一步一步地走就是了,一直走下去就是了。
就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