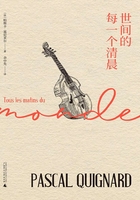终究是要行走的,在城市或者乡村。
年纪一点点大了之后,脚步渐渐就缓下来,对世界的敬畏与向往也越来越淡,终于有一天,心一松,把自己宠好的念头就狠狠生出。父母已经老去,子女尚未长成,所以只能以日益凋零的体温苟且宠住自己。为什么不呢?对着阳光笑一笑,然后心平气和地把羽毛缓缓梳理。年轻时,骄傲是我理想的一部分——骄傲地仰望骄傲地蔑视。一滴水都可以不屑一片汪洋,一片叶也可以承载整个春天呀。
人的内心波动是会渗透于外的,凝聚点可能是容貌也可能是那一身裹住躯体的衣服。
我曾经放肆追逐过各色服装,而且以稀奇别致为上。在庞杂物流中与某件蓦然邂逅,肩宽袖长腰围竟还那么契合,就有一种命定的感觉涌上来,如果又是腰包中的银子所接受的,就更是一种前世之缘了。世界那么大个体这么小,历史那么长生命这么短,爱的人爱的事以及爱的某种机遇与某个境界,谁能随心所欲轻易获得?能够瞬间在握的服装,便抚慰了这份无奈。它们轰隆隆轮番登场,带着我单薄动荡的身体箭一般刺穿生活——只是试图刺穿罢了,那一份喧闹和躁动,反而搅起更多的尘土,终究把自己先累倒了,然后归于平淡。
一切都渐渐地淡。这是一个过程,一个退缩与自省的过程。肯定还有俗事,俗事萦绕纠缠久久不息,连俗欲都不时涌起。只是我已经愿意找寻后退半步的秘笈与捷径。欲望是一种与硫酸类似的东西,有呛鼻的恶臭,会透彻地腐蚀。当站在伸到半空的阳台上,俯看街头的喧哗再仰望天际的悠远时,会知道,心灵最大的愉悦是来自最深的静谧。
“短篇王”,这个叫法很霸气,多少让我生出不安。但能够加入这套丛书,我还是高兴的,因为之前,我还没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子。当然,没有的好东西太多了,不要不切实际地流口水是人生一条很好的座右铭。但既然它像雨一样自然而然从天而降了,又何妨伸手捧住,俯身嗅一嗅?那上面有着大自然的气息。
“刻意”是个令人生厌的词语,刻意的拒绝与刻意的迎合应该同等摒弃。那首歌唱得好:“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做到很难,但可以努力。
我女儿在成长过程中,两耳堵满刀光剑影的人间丑态,是我屡屡从滔滔不绝的报纸电视以及道听途说的新闻中,捡出一堆负面的喂给她。不是要让她内心阴暗起来,而是为了防御。她这个年纪,丰衣足食,终日沉浸在夸张惊咋花里胡哨的动漫故事里,双脚始终没有踩到现实的地面。如果太平有序,还可以有风和日丽的日子。可是世界如此不尽如人意,人心如此复杂难测,无边的天真与单纯,就恰如手无寸铁地站在乌黑森严的枪口下了。即使五脏六腑,也需要有一片软弱的肚皮去保护啊。所以得把真相和盘托出,然后指望她开始锻造筋骨,并竭力自塑丰盈妖娆的心灵世界——一个庇护所而已,可以将自己的灵魂安顿进去,否则失望就来临了,虚无、落寞、沮丧也会陆续到来。
我的庇护所便是小说。
每看到有人扬言要把文学当成什么武器时,我的心总不禁陡然一紧,随后又释然了。无论他们所说的是自欺欺人,还是为了打造一副强大的盔甲,这个世界反正是需要一些志向宏大的人,那么硬朗地宣告出来,至少鼓舞了自己,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我却只有卑微的理念,觉得一部小说不过是某种精神疼痛或焦虑或躁动或渴求的隐秘的图,经线纬线的走向,都藤蔓一样沉默。在键盘上敲击着一个个汉字时,我成了他或者她。他们附体而来,让我凭借这些与我生活迥异的场景与素不相识人物,表达了,释放了。
释放不一定让人愉快,有时因为那么血淋淋地逼近了一下,就如一星烛光闪现之后,黑反而更浓更墨地降临了。这时内心就开始新一轮的起伏,于是另一篇小说可能就因此隐约显出了端倪。
其实一篇小说写作的时候我常夜不能寐,某一瞬间甚至满眼盈泪,然而在划过句号之后,涌动的潮常迅速退去,仿佛演出完毕,谢幕就不可抗拒了。等到它们挤进某本杂志变成铅字公之于众,有时就连再看几眼的力气都丧失殆尽。把这一组短篇小说收拢时,我甚至发现个别篇目不知去向了,样刊或原稿当初都没有被珍视,它们已经永远消失在废品站和电脑病毒后的空白中了。这样不好,以后得改一改。只要用心,给自己当好秘书并不是太难的事,难的反而是留不住跟在句号之后那一份退却的激情。为什么?我不知道。两年前当我心虚地把这个现象对一个编辑说出时,遭受到她语重心长的批判。我在电话这一头语塞,一时也不免后悔。哪怕装一装城府,也未必实话实说呀。人家会因此发现你是肤浅的,是胸无气象的,是缺乏文学气质的。
可是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写作着和丢弃着。那些意造出来的故事,我相信无论被如何冷落,它们都依旧在日升月落中径自把生活情节顽强地延续下去,而那些被我起了名字、赋予社会关系的一个个人物,他们也始终脚步匆匆地行走在一条特别的小路上,这条路蜿蜒于我内心,我的笑与哭、悲与喜、疼与痛,都与他们相关,都切切实实地来自他们躯体的某一角落。他们将同我一起祈祷树常青、花常艳,祈祷鸟健康地飞,水洁净地流。
祈祷给生命以自由和安宁,盎然如水草。
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