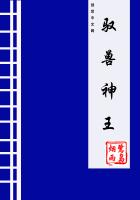人不但无法选择家庭出身,更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但无论这两点对人多么不利,人仍有选择自己人性坐标的可能,哪怕选择余地很小很小。于是,后人会从史性文化中发现,即使在寒冬般的时代,竟也有人性的温暖存在,而那,正是社会终究要进步的希望。
夕阳如血。
列车奔驰在秋季的松嫩平原。夕阳悬在车头前方,似乎在勾引列车吻到它。而对于列车,那是不可能的,尽管看起来车头与夕阳的距离近在咫尺;这情形使人联想到“夸父追日”的神话。车头气急败坏地喷吐浓烟,混沌了天地。而于那混沌之中,夕阳将车身映成平原上一道长长的剪影。
夕阳无可奈何地沉落……
列车亢奋地追逐……
迷雾渐散。一缕青烟,从一只斑驳了红色铁锈的灰铁皮烟囱里冒出。这只旧烟囱属于一栋被漆成果绿色的小房子。亮晶晶的铁轨从这小房子前铺过。那是只有北大荒才有的窄轨铁路,将林区丰产的木材一车车运到原野以外的地方。仓库整齐地排列在小房子后边,小房子旁竖着一块牌子,上写“白桦林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竖——一九六九年。”
已是傍晚时分,天空中大朵大朵的乌云逐渐堆积成团,从远处茂密的白桦林那方压过来。
杨秉奎的手在一盘残棋上缓缓移动,他在小房子里跟自己下棋。窗上贴着红纸剪的“忠”字和“公”字,除了一张没刷油漆的单人木床,还有桌子、椅子、箱子、柜子,都没刷油漆,木质已被岁月涂得黑亮。床上挂着蚊帐;炉子上的水壶吱吱作响,突突地冒出水汽;一条大狼狗懒洋洋地卧在炉旁。
杨秉奎五十多岁了,一脸该刮未刮的黑胡茬,一身旧铁路服,脚上是双“解放”鞋。
桌上的电话骤然响了。杨秉奎抓起听筒:“对,是我,‘养病亏’站长……放心,我知道……哎,你说话客气点嘛……我不管你是谁,给老子记着!”
他“啪”地放下电话,从墙上摘下铁路信号灯,把与铁路服配套的蓝帽子按在头上,开门出去,大狼狗溜溜地跟着。
天已快黑。
杨秉奎仰脸看天,雨点落在他脸上。
“早不下晚不下,非赶这个时候下。老天爷,你他妈成心找人别扭啊!”杨秉奎扭动着布满胡茬的嘴,喃喃地咕哝着。天仿佛就是要跟杨秉奎找别扭似的,霎时间雷声大作,暴雨倾盆。
“老伴儿,都说谁也惹不起老天爷,看来此话真不假呢!”“老伴儿”就是那条大狼狗。杨秉奎无奈地退回小房子,将雨衣从墙上取了下来。
闪电劈开雷雨交加的黑夜,瞬间照亮站在铁轨中间的杨秉奎。他左右摆动着手中的信号灯。一列封闭的货车缓缓驶来,车灯橘黄色的光透过密集的雨点,照在杨秉奎身上。
司机探出身喊道:“老站长,对不起啊,让您在雨中为我举信号灯了!”
杨秉奎:“甭客气,应该的。再说也不是你对不起我,是老天爷对不起我。”
列车停稳,一节节车厢的门被依次打开,有人从上面跳下来。顿时,哨声此起彼伏。
一个粗声大嗓的人喊:“全体下车!整队集合!各带队注意,哪一车厢少了一个,军纪处分!”
可是知青们却没有应声从车厢里跳下来,而是犹豫地聚在车门口,谁也不愿意先行一步。一名女知青用上海话抱怨,意思是这么大的雨,淋湿了我衣服和行李怎么办?也没有个站台,也没人准备好雨衣和伞。
张平原连长分开聚集在一起的知青们,指着那名女知青问一名男知青:“她嘟囔什么?”
那男知青也是上海人,绰号“小黄浦”,他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将女知青的话向他解说了一遍。
张连长:“那也不许赖在车上!”
他跳下车,指着“小黄浦”命令:“你,给我下来!”
这时,团里的曲干事走了过来,把手拢在嘴边,冲车厢大声喊:“男知青先下,接一下女知青,不要让女知青们摔伤了!各领队注意,要保证安全,保证安全!”
刚才已经跳了下来的“小黄浦”张着双手要接女知青,却被一个体态圆墩墩的女知青给压了个屁股着地。
曲干事赶紧上前扶起他们,关心地问:“摔伤哪儿没有?”
报数声在滂沱大雨中此起彼落,像是溅落到金属上弹起的雨点。闪电的光耀下,大雨冲刷着知青们一张张年轻的脸。他们浑身都已经湿透了。有些知青眼泪和淋脸的雨水汇流而下,如此这般地来到北大荒是他们万没想到的。
杨秉奎打开仓库的大门,冲着知青们大喊道:“都到仓库里来躲躲雨!”
刚才还整齐列着的队伍一下子散乱开来,大家涌进仓库。张连长望着知青们奔向仓库的背影,束手无策地自语:“这老爷子,真添乱!”
“不许往那跑,列队!”张连长拦住一些知青,被拦住的知青不情愿地向仓库的方向张望着,张连长生气地吼道:“都聋了吗?我再说一遍,列队!”
被拦下来的知青敢怒不敢言,怨恨地瞪着张连长,不情愿地站成队形。
“都没见过下雨吗!”张连长吼声如雷。
无人接言。
“回答我!”
一名女知青小声说:“见过……”
曲干事走来,在张连长耳边低语:“老张,我看是不是暂时……”
张连长看也不看他一眼,恼火地说:“你别管!”
曲干事欲言又止,只好退到一边,习惯性地从兜里掏出一支已经被雨淋湿的烟,刚举到唇边,又想起了什么,将烟揣回兜里。
张连长脸板得像块湿木头:“下雨只不过是下雨,下再大的雨也还是下雨,不是下刀子!你们不是那些插队知青!他们一插队,不想当农民那也是农民了!你们叫兵团战士!是战士就得有点战士的样子!没有口令擅自行动,不是好战士!跑到仓库去的,都要受处分!”
曲干事又说:“老张,还是听我的……”
“不听你的!这时候非听我的不可!”张连长打断他的话,继续训,“我们这个团的团长,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当年跟随团长转业到北大荒的,号称三个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九十五的党团员!百分之九十五的正副班长!百分之九十五的五好战士!这是我们团的政治血统,这个政治血统必须永远保持下去,保持住了就等于保持住了我们团的光荣!所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家庭有严重历史问题的,我一个也没从城市里往一团接!哭鼻子抹眼泪也不要!写血书也不要!你们已经成为一团的战士!你们也应该感到光荣!感到自豪!挨点淋就不要纪律了?不是都发誓要炼一颗红心吗?那就给我从现在炼起!”
张连长的训话还没有结束就被打断了,一个知青惊慌地跑过来:“带队,那边打起来了。”
“谁跟谁打起来了?”
“北京的和哈尔滨的,啊不!是哈尔滨的和北京的、上海的打罗圈架!”
张连长和曲干事连忙向事发地赶去。
在列车的尾部,几十名知青打成一团,有女知青在尖叫:“别打了!”
“呯!”
一声枪响使打架的知青都停止了。杨秉奎冲到打架的知青中间,扯开嗓子喊:“谁再打我崩了他!都到仓库避雨去!”
张连长和曲干事赶过来的时候,知青们早已悻悻地散开了。
张连长看着四散离去的知青们说道:“就这么完了?”
“不完还怎么着!”杨秉奎甩下一句话,也转身走开了。
仓库的一摞麻袋上横七竖八地摊着些湿透了的衣服,男知青们把身上能脱下来的衣服都脱下来拧干。上海知青徐进步连裤衩也脱下来拧,被一穗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的干苞米击中面门。
“谁?谁他妈打我?!”他鼻子被打出了血,眼镜片上也开了朵蜘蛛网似的花。
哈尔滨女知青孙曼玲双手叉腰,操着地道的东北腔指着他:“你要不要脸啊!当我们女知青不存在啊!”
孙曼玲背后那些浑身淋得湿漉漉的女知青都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徐进步恰与孙曼玲面对面,赶紧用湿裤衩捂住下身,红着脸嘟囔:“哎哟妈呀,直勾勾地看着我,是我不要脸还是她不要脸啊!”
孙曼玲听到了,生气地发动女知青:“姐妹们,他出言不逊,打他!”
一时间,苞米、葵花盘长了翅膀似的飞向徐进步,徐进步顾上顾不了下,狼狈地蹿到了几个箩筐后面。无辜挨打的男知青们也跟着东躲西藏。
“你们就这么糟蹋我留的良种?”拎着枪的杨秉奎大喊一声,闹成一团的知青们顿时安静了。
知青赵天亮赔罪道:“对不起老爷子,刚才发生了一点小摩擦,您千万别生气,我们保证归放原处。”说着,将地上的谷物一样一样拾起,其他知青也纷纷帮他。
“以这几个箩筐为界,今晚,筐那边是女知青的地盘,筐这边是男知青的地盘。都听明白没有?”杨秉奎看着一边收拾地上的谷物一边点头的知青们,扬手示意了一下赵天亮:“你过来一下。”
赵天亮放下手里的东西,走到杨秉奎近前。
杨秉奎问:“你叫什么名字?”
“赵天亮。”
杨秉奎点点头:“我授权你,今晚要是有哪个男知青胆敢犯女知青的界,就把他拖出去,让他喂蚊子。”
哈尔滨知青孙敬文插嘴道:“下雨天蚊子不叮人。”
杨秉奎摇摇头:“这雨不会下一整夜。雨后的蚊子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当万。不相信的就让他领教领教北大荒的蚊子,哼!”
赵天亮有些迟疑:“可我一个人,势单力薄,恐怕做不好你交代的事,授权也白授权。”
“那就挑一个助手吧。谁愿意?”
孙敬文油腔滑调地凑上来:“我!我!谁也甭争,就是我了!我可爱干把人拖出去喂蚊子的事了!”
杨秉奎问赵天亮:“还有问题吗?”
赵天亮摇头。
杨秉奎一转身走了。
孙敬文学着样板戏里刁德一的样子拖腔拉调地唱:“这个老头——不寻常……”
赵天亮碰了碰孙敬文,问:“哪儿的,叫什么?”
“哈尔滨的,孙敬文。以后你叫我‘小地包’就行。”
“我是北京的。”赵天亮指了指正由孙曼玲指挥着,在仓库里拉草绳子的女知青们,“你认为她们想干什么?”
孙敬文抓了抓脑袋:“猜不准。搭衣服吧?”
孙曼玲们却往草绳上搭草帘子和麻袋,搭成了一道“隔墙”。
赵天亮轻轻地嗤了一声:“多此一举。”
孙敬文拍拍他肩膀:“别多说了啊,她可是我老姐。”
阳光从仓库上方的一排长方形窗户里照了进来,驱散了仓库里的阴暗。
赵天亮醒了,他身上盖着麻袋,仰面躺在草帘子上——仓库里所有的知青,都是这么睡了一夜。赵天亮把头向左扭去,只见徐进步、孙敬文以及周边的几个男知青全都趴着,双手托腮,跷着脚丫子,兴致高涨地向草帘子对面张望;他右边的王凯、沈力、杨一凡三名北京知青也同样,一心一意地向对面伸着脑袋观看什么。
赵天亮对他们的专注有些奇怪,一翻身也朝对面看去——对面的草帘子和麻袋下端暴露着一双双女知青们的裸腿和光脚丫,她们的腿呈现着各种各样的姿态,有的在走动,有的跳芭蕾舞似的翘着脚尖,有的将一只裸臂搭在草帘子上,单腿着地“金鸡独立”着。一副乳罩掉在地上,一只修长的手臂垂下,把它捡起。
沈力在往小本上画速写。
“你们……”“下流”“可耻”之类的话还没说出来,赵天亮的嘴被孙敬文捂住了。一只麻袋从天而降,蒙住了赵天亮的头。
徐进步轻声地鼓励道:“对!还没看够呐!别让他出声……”说着,便扑在了赵天亮的身上。
沈力:“你们可别闷死他。”
孙敬文:“闭上你的臭嘴,别得着便宜卖乖。”
女知青那边忽然发出尖叫声,一阵骚乱。
王凯眼尖:“黄鼠狼!”
“钻咱们这儿了!那!那那儿!”杨一凡指着嚷嚷。
黄鼠狼窜到了男知青这边,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黄鼠狼身上,没有人再搭理赵天亮,他这才从麻袋底下钻出来,大大地喘了几口气。还没等他定下神来,哨声从仓库外传了进来。
杨秉奎走进仓库,仓库已经没人了,麻袋乱扔一地,柳条筐也倒在地上,草帘子却还在草绳上耷拉着。
杨秉奎边收拾地上的狼藉,边嘟囔着:“这些孩子……”
一阵隐约的哭声从草帘子另一边传来。
“谁还在那儿?”
哭声呜呜依旧。
杨秉奎提高声音:“我过去了啊!”说着,便扯下一条麻袋,走到“隔墙”那边,见上海女知青周萍缩在一个角落,双手捂脸,继续哭着。
“哭什么?谁给你气受了?”杨秉奎走上前去问道。
周萍摇头。
杨秉奎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更温和些:“挨淋了,就受不了啦?”
周萍还是摇头。
杨秉奎有点生气,火气一顶,把刚才的温和顶走了:“那你哭什么!没听见吹哨子呀?别人都集合了!”
周萍绝望地说:“他们不要我!”说完,放声大哭。
杨秉奎蹲了下来:“谁们不要你?”
周萍:“带队们,因为我父亲是资本家……可我写了三次血书……”
杨秉奎注意到周萍右手的食指包扎着,皱眉问:“手指怎么了?写血书刺破的?”
周萍抽抽搭搭地说:“不是刺破的,是咬破的。别人说,写血书一定得自己咬破自己的手指……”
“教条嘛。所以你就咬破三次?”
周萍痴痴地点头。
“发炎了?”
“嗯。”
“这还能不发炎?说说,你父亲是民族式的,还是买办式的?”
周萍用手抹了抹眼泪:“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档案里写的是民族资本家。”
杨秉奎郑重地点了点头:“要是民族资本家,倒还有点儿商量了。政治上的事,我是懂些的——可既然他们不要你,你怎么还是来到这儿了呢?”
“我从上海偷偷混上了知青专列……”
杨秉奎吃惊道:“上海?那得经过北京、哈尔滨、北安,一地一点名,你就能一路混过来了?”
周萍点了点头。
杨秉奎被感动了:“姑娘,北大荒其实是个很有人情味儿的地方。冲你这一份诚心诚意,我帮你。起来,跟着我。我一定会帮你到底!”
周萍顺从地起身,跟随杨秉奎走出仓库。
张连长瞪着眼前整齐地列成队的知青们,训道:“你看你们,啊,麻袋扔得哪哪都是!那可都是新的!今后你们要记住,在北大荒,麻袋也是宝贵的东西!”
徐进步眨眨眼睛,强词夺理:“北大荒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从没听说过还有麻袋!”
张连长瞪着徐进步:“现在你不听说了?都记住没有?”
知青们回答:“记住了!”
赵天亮不服地说:“我有意见!”
张连长:“给你半分钟,说!”
“天有不测风云,这是常识。既然是常识,就应该为我们的到来考虑得周到些,提前做好防雨措施。”
张连长反问:“也就是说,应提前准备好足够用的雨衣、雨伞、雨靴,最好再搭好十几顶临时帐篷?”
“按理应该那样。”赵天亮一板一眼地回答。
“你出列。”
赵天亮向前跨了一步。张连长走到他身边,上下打量他,仿佛在研究一样稀罕的物件。
“叫什么名字?”
“北京知青赵天亮,‘赵子龙’的‘赵’!”
张连长哼了一声:“赵子龙是条龙,冲你刚才说的话,我看你像一条虫!雨衣、雨伞、雨靴、帐篷,想得倒美!在北大荒,在目前,想到了也白想,因为那是做不到的。天有不测风云,在北大荒的意思那就是,老天爷给人气受,是常事儿,人得受着!你的想法是歪理,我讲的才是正理,北大荒的理!”
赵天亮说:“我对你动不动就训我们也有意见!”
张连长:“还有意见以后再提,给你的半分钟过了!第一排听我口令,向前一步——走!向右——转!你们都跟着他,把麻袋收集到仓库去!”
赵天亮低声对徐进步嘟囔:“半分钟里,我说的没他说的多!”
徐进步瞟了一眼张连长的背影,说道:“这就叫,官不大,僚不小。”
张连长猛地回头,瞪着他俩:“说什么呢?”
徐进步赶紧朝赵天亮一指:“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说完,便朝一条麻袋跑去了。
赵天亮转头望着徐进步,生气地说:“这不是陷害我嘛!”
杨秉奎和周萍一前一后朝这边走过来。张连长看到他们,想转身走开。
杨秉奎:“张连长,站住。”
张连长站住了,掏出烟和打火机。
“我跟你说话,你不许吸烟。”杨秉奎将张连长手里的烟夺了过去,叼自己嘴上,又指了指张连长手中的打火机。张连长只得按着打火机,伸到杨秉奎嘴边,同时狠狠瞪了周萍一眼。
杨秉奎缓缓吐出一口烟,对张连长说:“旁边说几句话。”
张连长只好跟着杨秉奎踱向一旁。
杨秉奎:“你不拿好眼色瞪人家姑娘干什么?”
张连长:“我没瞪她。”
杨秉奎:“瞪了就是瞪了,事实那否认得了吗?我觉得人家姑娘挺不容易。归在你们连了。”
张连长:“老爷子,她是硬跟来的。我没那么大权力呀。”
“她的情况我了解过了,我的话你照办就是了,算给我个面子。”
“不是我不给您面子,可她父亲是资本家,不符合咱们兵团的成分要求。”张连长一本正经地说。
“民族资本家!”杨秉奎正色纠正。
“资本家就是资本家,那还有什么区别?”张连长铁面无私地说。在他眼里,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资本家,都是反动派。
杨秉奎:“资本家和资本家,当然有区别!我看你政治水平不怎么样!”
周萍紧张地盯着他俩,列着队的知青们则用同情的眼神看着周萍。
张连长有些为难:“老爷子,您的批评我虚心接受,可这件事,我真的……”
“说来说去,我看你是成心不想给我面子!”杨秉奎有点生气,转身对周萍说,“咱不跟他瞎耽误工夫了,我给你找个更好的连队!”
卡车和马车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有的知青方阵已经上了车,没有上车的知青方阵正准备上车。周萍急得又快哭了。
曲干事走过来,对杨秉奎“啪”地敬了一个军礼:“站长同志,我们团长嘱咐我一定替他向您问好!我马上要坐卡车回团部去了,您有什么要捎给团长的话没有?”
杨秉奎:“小曲,你来得正好!这上海的女学生,我劝张连长收到他的连,张大连长不给我面子。你看怎么办吧。”
曲干事早就认识周萍了,揣着明白装糊涂:“张连长,这你就不对了。你怎么能连站长同志的面子都不给呢?”
张连长有些急了:“哎,曲干事,话不能这么说啊!她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同情归同情,感动归感动,事情归事情,不是连你都没权力……”
曲干事摆了摆手:“得了得了,别说那么多了,什么权力不权力的,我代表团长作决定,她就归在你们连了!”
张连长还想争辩,曲干事把他扯到一旁,低声说:“我不是装好人,明摆着,只能先收在你们连了!这老爷子要不高兴起来,团长也会不高兴,师长也会不高兴,这点事儿你都不懂?”
曲干事跟张连长说完,又笑着对杨秉奎说:“老站长,张连长同意了,您放心吧。”
杨秉奎转头对周萍说:“听到了吧,你也放心吧。”
周萍抹抹眼泪,破涕为笑。
杨秉奎走到张连长跟前,严肃地说:“以后不许你叫我老爷子,我有那么老吗?我还打算找个伴儿呐!都像你那么叫,我不只有找老太婆了?你给我记住!”
仓库里,赵天亮把麻袋一条条码好,刚要喘口气擦擦汗,见徐进步和几名知青抱着麻袋也走了进来。徐进步刚放下麻袋,被赵天亮一把揪住了衣领。
赵天亮恨恨地:“刚才明明是你说的话,为什么往我身上赖?!”
徐进步挣扎道:“侬这等样不来赛不来赛,阿拉上海泥胆子小的赖,阿拉视侬的胆子大的赖……侬不是虫,阿拉是虫,好□?”
赵天亮狠狠将他推开:“哼,我胆子大,就该什么不利的事都往我身上推吗?”
徐进步还没来得及把狡辩的话说出口,仓库外传来一片“乌拉”之声。他们一齐跑到仓库门口,朝七连那边看去,只见队形已经散乱开了,女知青们围成一团,男知青们往空中抛帽子。
孙敬文:“准是那名混来的女生混成功了,大家为她高兴。功夫不负铁了心的人啊!”
张连长带着知青们走在山脚下的公路上。而所谓公路,其实只不过是包括拖拉机在内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车辆压出来的一条土路。
张连长不知把哪个知青的行李扛在肩头,手拎网兜。尽管如此,他的步速还是比知青们快许多。徐进步、王凯和孙敬文拖着各自的大包小包走在最后边。徐进步的军绿色大书包背在身后。王凯尽量让自己的步速跟他保持一致,边走边从徐进步背包的缝隙里掏糖,边掏边往自己兜里揣,徐进步浑然不觉。
冷不丁地冒出来一个声音:“人不能太贪,差不多就行了。”
徐进步猛然转身,见是孙敬文,问:“你说什么?”
孙敬文看一眼王凯,对徐进步说:“没说你,自言自语呢。”
徐进步往前边看了看,说:“咱们三个不能走在最后,让女知青笑话!”说着,便加快了脚步。
王凯拍拍孙敬文的肩:“哈尔滨的,没出卖我,够义气!”
孙敬文伸出一只手:“我够义气,你也得够意思吧!”
王凯从兜里掏出块糖,剥去糖纸,塞在孙敬文嘴里:“我低血糖。”
孙敬文嚼着糖:“酒心儿的——我也低血糖!”说完,便紧跑几步,也追上徐进步,从背包里往外掏糖。
张连长把肩膀上的行李往地上一撂,站在路边等知青们的大队伍跟上来。
徐进步跑了过来:“连长,允许提个问题吗?”
张连长点点头:“可以。”
徐进步:“就没有一条好走点儿的路了吗?哪怕一条要多走几里的路。”
“我带你们走的正是最好走的路,起码在这一带是这样。这里本没路,拖拉机一过,路就出现了。”说完,便又扛起行李往前走。
徐进步回头看赵天亮一眼,说:“他这最后一句怎么听着像谁说过的话?”
“套用鲁迅的话。”赵天亮马上说出了出处。
徐进步一拍脑袋:“啊,想起来了,‘世上本无路’那一句,难怪听着有印象。可就他,八成没读过鲁迅的什么书吧?”
“你怎么知道我没读过鲁迅的书!”张连长回过头,瞪着他厉问。
徐进步被他瞪得一哆嗦,赶紧摆手道:“不是我说的,是他!我从不背后说领导的怪话。”他又企图往赵天亮身上赖,赖人仿佛也有惯性。
赵天亮一晃拳头:“我揍你!”
“你犯不着揍他。这一次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是他说的!”张连长给了他个公道,接着,又大声说,“都站住吧,原地休息休息!”
知青们如逢大赦,把行李当成坐椅就地坐下。
张连长掏出烟来,点上。
赵天亮:“连长,我有问题。”
张连长咂吧着烟:“提。”
“在小火车站那儿,别的知青都有卡车送、马车接,为什么单单我们,非得自己带着行李走这么远的路?”
“就是,起码也该来辆马车接接我们吧!”王凯揉着脚踝附和。
杨一凡也插嘴道:“难道你们连队连一辆马车都没有吗?”
“重说一遍,谁们连队?”张连长眼睛一瞪。
杨一凡忙不迭地纠正道:“说错了,说错了,咱们连队……”
上海女知青薛艳:“我们的箱子到哪儿去了?不会丢了吧?”
上海女知青谢菲:“要是丢了,我连手纸都没得用了!”
哈尔滨女知青高洁跟林丽咬耳朵:“但愿别和上海女知青分在一起,事儿多!”
孙曼玲听到了她们的话,摇着头冲她俩使眼色。
张连长弹了下烟灰,慢条斯理地:“第一,你们的箱子绝对不会丢。一路上,团里派了专人负责,估计不久就会用卡车送到连队……”
徐进步:“不久是多久?”
“最晚半个月吧。”
知青们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你。
张连长继续说:“第二,用卡车送的知青,他们的连队比我们七连更远。用马车接的,他们的连队比我们近些。我们七连距离小火车站不远不近……”
赵天亮:“多少里?”
“三十七公里。”
“三十七公里?!”
知青们全都愣住了。
张连长安慰道:“不要急嘛,我也很内疚啊!实际情况是,连里是派了爬犁来接我们的,但接连下了几天雨,路被水淹了,爬犁只能在半道迎我们了。我们呢,再走过塔头甸,就能与连队的爬犁会合了。”
高洁有些纳闷:“又不是冬天,怎么用爬犁接我们?”
张连长刚想给她解释,一直在默默点名的孙曼玲突然向他发作起来:“带队的,你干什么吃的!少了一个人!”
张连长赶紧起身清点人数。
“还点什么呀你,我点两遍了!”孙曼玲凶巴巴地打断他,“少了那个上海的小可怜儿周萍。这下不知她又哭成什么样儿了——你还吸烟!”
张连长这才把手中的烟扔到地上踩灭:“刚才走在后边的举手。”
一旁几名正在休息闲聊的知青怯怯地举起手。
张连长瞪着眼睛:“混账!走在最后的人掉队了,你们都不报告!”
王凯委屈地说:“我们也没注意到啊!”
“还顶嘴!你应该注意到!”
正说着,一个瘦小的人影一摇三晃地从远处走来。
赵天亮向远处一指:“看,她来了!我去接接她!”
张连长伸手拦住赵天亮:“别去接,让她锻炼锻炼!”
赵天亮冷冷地看了张连长一眼,拨开拦住他的胳膊向周萍跑去。
满面泪痕的周萍,双手各拎一只皮鞋,赤着脚一瘸一拐地走着。
赵天亮迎上去:“脚打泡了?”
周萍无力地点点头,鼻子一酸,眼泪又噙满了眼眶。
赵天亮转过身背向她,蹲了下去:“背你。”
“我不用你背。”周萍倔强地说着,绕过他,蹒跚着朝前走。
赵天亮站起来,跑到她前边,又蹲下去。
周萍站住了:“我说了,我不用你背。”
“你也不能白让我蹲两次啊,让大家都等你太久,不好吧。”赵天亮劝着。
“我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周萍哭了,将两只鞋掷在地上。
赵天亮默默捡起鞋,拎着,第三次蹲在她跟前:“我可第三次为你蹲下了,我从没这么求人让我背过。”
赵天亮背着周萍从远处走来。
张连长看着赵天亮放下周萍,大声训斥:“不许哭!我就受不了你们动不动哭鼻子抹泪的!是你自己死乞白赖跟来的!”
“你混蛋!”赵天亮瞪着张连长。
“你!”
赵天亮将手中的两只鞋一前一后地扔向张连长,被张连长躲了过去。紧接着赵天亮向张连长扑过去,被张连长一下子甩出老远。
王凯和杨一凡将赵天亮扶了起来。赵天亮向后一甩胳膊,把二人甩开,接着又向张连长扑去,却被沈力一把拽住了胳膊:“干什么你!”
赵天亮挣扎着:“你别管!我早就忍着他了!”
孙曼玲伸开双臂,拦在赵天亮跟前:“你不累是不是!”
张连长:“别拦他!谁也别拦他!我看他想怎么样!路上我是你们带队,到了连队我是你们连长!想跟连长打架,反教了!”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赵天亮推到一旁,把他和张连长隔离开来。
周萍捡起自己的鞋,一边抽搭着眼泪,一边穿鞋:“连长,都是我不好,我一步不落就是了。”
孙曼玲对张连长说:“连长,大家早上没吃饭,又走了这么久,都累叽歪了,您既然是连长,有火也应该压着点,不能跟我们战士一般见识。”
张连长发狠地说:“都起来!谁也别装草鸡,继续往前走!”说着,他走到周萍跟前,将周萍拽起来,扛麻袋似的,扛在肩上。
大家跳跃着,经过一片闪着水光的塔头甸。
还趴在张连长背上的周萍不好意思地小声说:“连长,求求你,让我自己走吧。”
张连长:“你脚上磨出了这么多泡,自己怎么走?这塔头甸子里的水,是各种细菌的大本营。五八年,我们那批转业兵来的时候,一个战友脚上的泡也破了,可他偏要强……结果得了败血症,死啦。我不能忽视那种教训,尽管我背的是资本家的女儿。”
周萍小声说:“如果我能以兵团战士的身份死,就是死了也值。”
“别废话!资本家女儿的命,那也是一条人命。”
赵天亮趟着水走在张连长旁边。周萍扭头看赵天亮,泪汪汪的眼睛带着询问:我该怎么办啊?
张连长停在塔头上喘着气,流着汗。
赵天亮有点不好意思:“连长,刚才是我不好,让我背她一会儿吧。”
徐进步站在一个塔头上,一点也不知道身后背包里一长截手纸垂下来了。上海女知青谢菲站在另一个塔头上,用上海话朝他喊:“你把你那尾巴卷起来行不行,拖那么长尾巴,演大老鼠啊!”
徐进步将书包移到身前,往书包里塞手纸,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伸手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来一看,发现糖只剩几颗了。他快要哭出来,忘记自己是在塔头上,一跺脚,失足滑下了塔头。
“我的画夹!谁帮我捡!”北京知青沈力看着自己的画夹被水流漂走。
上海女知青薛艳弯腰想帮他捡起,却被另一个塔头上的张连长喝止:“不许捡!大家注意,这里水深!也许水下还有沼泽坑,都小心点,过了这一片就安全了。”
远处,有人用长树枝挑着红背心在向他们摇摆。
知青们终于坐上了三辆拖拉机牵引的爬犁。暖日当头,疲惫的青年们互相靠着打起盹来。
徐进步和孙敬文闭着眼睛说话。
徐进步:“咱们之中有扒手。”
孙敬文:“不会吧,连长不是说了嘛,能来的都是大大的良民。”
王凯:“哎,孙敬文,‘小地包’不就是地面上隆起的一个小土包包吗?你这个绰号太低级了吧。还是咱们上海来的这位兄弟的绰号有文化——‘小黄浦’!让人联想到黄浦江、黄埔军校,再加一个小字,受尊敬,又招人疼。起绰号也要起得高级。”
孙敬文:“好歹我的绰号是别人送给我的,我不接受都没办法。而他的绰号是自己送给自己的,见人就推销,别人想不接受都难!”
“小弟,说话别带刺儿!”孙曼玲教诲弟弟,转脸又对徐进步说,“‘地包’是我们哈尔滨市的一个区,我家住那区。”
孙敬文:“哈尔滨的贫民区!”
一名叫吴敏的哈尔滨女知青道:“哈尔滨没有贫民区,不许污蔑社会主义。”
孙敬文也猛地睁开了眼睛,瞪着吴敏,较真地:“你敢说没有?!”
孙曼玲打断他:“小弟!不许再抬些不三不四的杠!”
周萍坐在赵天亮身旁,悄悄地往他手里塞东西,他低头一看,是两块糖纸亮晶晶的糖。
周萍:“谢谢你背我。只有两块了,酒心巧克力。”
徐进步将眼睛睁开一条缝,刚好看到了那两块糖,他皱了皱眉头,觉得有点纳闷。
爬犁颠颠簸簸地行驶着,目之所及尽是莽原荒野山廓水支。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悠悠的号子声:
兄弟们使把劲儿哟!
嘿哟!
咱们就往前悠呀!
嗨哟!
谁要是藏点劲儿哟!
嘿哟!
他也就不能够呀!
嗨哟!
……
知青们睁开眼睛,寻找声音的来处。
灌木丛遮掩的河湾那儿,拐出一些人来。几名老战士和两名知青样子的青年——他俩一个叫张靖严,一个叫齐勇。他们二人一组,用显然是临时砍下的树段当作杠子,用柳条和野草编成的绳子,抬着一只大柴油桶。桶在河水中半沉半浮,河水没过了他们的腰。
大家看呆了。
张连长从爬犁上站起来,一摆手,两辆爬犁停了。河里的老战士也停止了前进,为首的机务排尹排长问张连长:“连长,你怎么才把这些知青接回来呀?”
张连长:“路上不顺。你们怎么回事啊?”
尹排长叹了口气:“我们更不顺,拖拉机陷住了,只好顺河往下抬。眼瞅要麦秋了,机械没油喝那还行!这样抬才抬得动,要不咋办啊。”
另一名老战士:“连长,有烟没有啊?”
“有!有!”张连长连声应和着,跳下爬犁,趟着水大步走向河边。
一名老战士连忙阻止他:“别下河,扔给我们就行!”
张连长却已举着烟和打火机下了河,走到老战士们跟前,将烟一一送到他们唇边,并替他们点燃。
张靖严和齐勇抬最后一杠。齐勇:“还有我俩呢!”
张连长:“没了!有也不能给你俩知青吸!小齐,你上去,我来!”
齐勇一指张靖严:“我顶得住,你还是替他吧!”
张靖严:“你顶得住我就顶不住了?我是班长,连长当然得替你!”
话音刚落,起绳子作用的柳条突然断了,桶猛地往下一沉。三人仰倒河中,扑腾起片片水花。
在岸上的赵天亮看到这一幕,迅速解开自己的行李,拿着行李绳飞快地跑到河边,不管不顾地下了河,抬起最后一杠。
一双手在往顶棚糊一张报纸,却怎么也糊不上。
这是一间有着对面炕的知青宿舍。尽管是对面炕,但每铺炕仅能睡五六个人而已。
糊报纸的是黄伟,傅正双手高举糨糊盒。他俩也是哈尔滨知青。他们与齐勇、魏明都是老高三,并且都是同学。而张靖严是和他们同校的老高三,在校时就入党了。
傅正:“临时宿舍,别太认真,差不多就行。”
黄伟:“那也得糊上去啊!”
只听“砰”的一声,宿舍门被撞开了,孙敬文、赵天亮等新来的知青,扛着行李从外面闯了进来。但听“嘭通”一声,黄伟被他们的突然闯入吓了一跳,从椅子上跌了下来,倒在地上,糨糊盆扣在炕上,糨糊溅得四处都是。
傅正抹去脸上的糨糊,拉起黄伟,呆望着一炕狼藉。
孙敬文连忙道歉。
傅正缓过神来,摆摆手:“没什么,小事一桩!”
黄伟眼睛到处寻摸擦糨糊的东西,看了一圈也没找到,便脱下上衣去擦炕上的糨糊。
“我去打盆水。”孙敬文从网兜里取出脸盆往外边走,不料与正要进宿舍的齐勇撞了个头碰头。孙敬文又连声道歉,可是这次换来的不是原谅,而是狠狠的一记耳光。
“凭什么打人?!”赵天亮几步跨过来,护在孙敬文身前,瞪着齐勇。其他几个知青也跨过来,站在赵天亮左右。
王凯指斥齐勇:“‘小地包’又不是故意的!”
杨一凡:“欺负我们新来的?!”
“我去打水,我去打水。”徐进步从地上捡起盆,溜了出去。
黄伟一把将齐勇扯开:“你发什么神经?!”
齐勇一掌推开赵天亮,横着膀子撞开新来的知青们,扬长而去。
赵天亮瞪着齐勇的背影说道:“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完了!这可是我们新知青来到连队的第一天,我一定要代表新知青向连里抗议这件事!”
大家也七嘴八舌地附和着。
“对,不能就这么完了!”
“打人者必须公开道歉!”
“只道歉不行,连里必须给他处分!”
黄伟语气和缓地说:“你们当然有抗议的权利,不过呢,这会儿先认识一下行不?我叫黄伟,哈尔滨知青,老高二,他叫傅正,也是我们哈尔滨那嘎哒的,和我一样,老高二。”说完,向赵天亮伸出一只手。
赵天亮没握黄伟伸过来的手,也没说话,他朝炕上望一眼,也脱下上衣去擦起来。
傅正轻笑道:“还挺有性格,我喜欢有性格的人。”
黄伟走到两眼发直的孙敬文跟前,拍拍他肩膀:“放心,我们都是见证人,会替你主持公道的。你喜欢睡有窗那边还是没窗那边?”说罢,拎起了孙敬文的行李。
孙敬文夺过行李:“不用你管!”
一阵哨音打断屋里的争执。
“连长叫放下行李就集合。”孙曼玲探进头来通知,发现她弟弟脸上挂着眼泪,便走进来,问:“小弟,谁欺负你了?”
黄伟赔笑着说:“刚才发生了点不愉快,不过已经过去了。”
孙敬文气鼓鼓地:“没过去!”
徐进步端着盆水进来了,见赵天亮还在擦炕上的糨糊,赶紧声明道:“我可不睡这儿。”
赵天亮:“是糨糊,又不是别的东西。”
徐进步:“糨糊扣炕上了,那能擦干净吗?还不进到席缝里啦?以后还不招苍蝇?”
赵天亮默默将自己的行李和网兜摆到擦过的炕面儿上,又替徐进步将行李和网兜摆在自己腾出来的地方,问:“这样行了吧?”
徐进步没再吭声。
“快去集合吧!”傅正向窗外看了看,催促大家。大家搁下手里还没整理完的行李,皆匆匆而去。
黄伟想对孙敬文说什么,傅正悄悄扯了他一下,对他使眼色,意思是,没事,他姐哄哄他就好了。黄伟没再说什么,跟着傅正离去。
孙曼玲用手绢替弟弟擦眼泪:“告诉姐,刚才究竟怎么回事儿?究竟谁欺负你了?”
“姐,咱俩要求调到别的连队去吧!”孙敬文推开姐姐的手,冲出了宿舍。
一队拖拉机开了过来。张连长的口令声被拖拉机声盖住。拖拉机总共十二台,每两台一纵列,由新到旧纵向列开。不过,即使是旧拖拉机,也擦洗得干干净净。拖拉机的纵列后,是八挂大车一字排开,套在车上的马匹精神抖擞,佩戴红花、铃铛。
大车后边是两排老战士。其实他们年纪并不老,平均年龄也就三十二三岁。尹排长站在第一排老战士排头,响亮地喊了一句“敬礼”。于是,新来的知青们脸上挂着庄重,接受了老战士们齐刷刷的敬礼。
韩指导员走过来,亲切地说:“大家请稍息吧。我叫韩经泰,是咱们七连的指导员。我是江苏人,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
徐进步突然冒出了一句:“海军学院的,到北大荒来干什么?”
韩指导员轻轻一笑:“我听到你们中有人感到奇怪了。关于我的经历,以后再告诉你们。”他用手指着后面的拖拉机和大车说道,“在咱们兵团,一般连队只有七八台拖拉机,可咱们七连却有十二台!不久后,师里还要奖给我们一台,七十五马力的,因为我们是最早在这里开垦、播种、收获的连队。拖拉机是咱们的宝贵财富,人更是。你们来了,我们七连更加人强马壮了。也许你们中有谁还想问——明明一个常见的农村嘛,为什么非叫‘连队’呢?这个‘农村’和普通的农村有不同吗?有,那就是军号声!它意味着连队在下达命令——小李,吹一遍!”
年龄最小的哈尔滨知青——只有十五岁的李鸣演示起了各种军号:“起床号”“午休号”“集合号”“熄灯号”。新来的知青们以后就要在这些长长短短的号声中作息操练,蹉跎自己年轻的岁月。而北大荒的每个黎明、日出、黄昏、日落和夜晚,也就要如同这些号声一般,萦绕在每个知青茫然的青春记忆里。
迎接新知青的联欢会在天色擦黑的时候开始了。篝火燃起处,传来手风琴和二胡的声音,有人唱样板戏,笑声使北大荒的原野显得更加空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