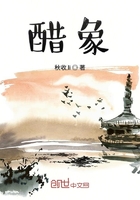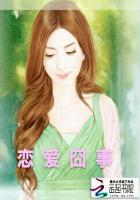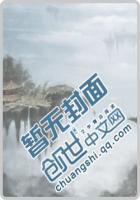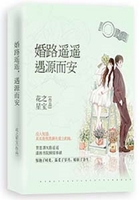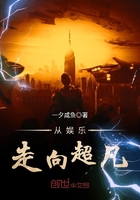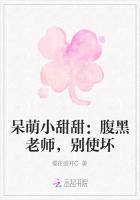半个多世纪,他的欢乐,他的欲望,他的旺盛的生命力,都给了无名河。剩下的只有一份淡淡的忧伤。
人这一辈子是太短了。
沙丘上,梅子依然坐在那里。她已经织完了又一件小毛衣,难得地闲着。在她膝旁,卧着一头雪白的小山羊。小山羊用它毛茸茸的濡湿的唇,轻轻地蹭着她的腿。梅子低下头,用她纤弱柔软的手指梳理着小山羊身上的毛。一下,一下……
最先从沼泽中隆起的那块沙滩,独臂汉子叫它蚂蚱滩。蚂蚱滩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庵棚。庵棚被狂风一次次连根拔起,抛向空中。一次次被暴雨冰雹打碎,散在地上。但都没有把独臂汉子赶走。恶劣的天气和肆虐的蚊虫日夜折磨他,弄得浑身肿胀,血脓斑斑。但他不走。
独臂汉子不走。
他对着狂风暴雨野狼似的愤怒地长嚎:
“我——不——走!”
“我——不——走!!”
“我——不——走!!!”
…………
他不走。他要夺回这片本来属于人的土地!
他没有伴。只他一个人住在这里。住在这无边的沼泽中。他长发如草,满脸胡须。衣服已经烂成碎片,随风而去。他干脆裸着全身。又丑又脏的生殖器吊在大腿间,晃来晃去。日月昭昭,高天朗朗,他一点也不觉得害羞。这里一切都已回归原始。他失去了从文明社会带来的那块遮羞布,风雨雷电酷暑严寒却为他再造了一张鳞甲一样的皮。没有什么道德能约束他,没有什么人来指责他。他就是道德,他就是法律,他就是这茫茫沼泽的国王。
饿了,吞吃蚂蚱。渴了,暴饮冷水。困了,就地一躺。醒了,就去干活。每天凌晨,他便早早地离开庵棚,赶上老牛。老牛拉着拖车。拖车上放一弯木犁。慢慢从一条泥泞的路上走。每天傍晚,他又赶上老牛。老牛拉着拖车。拖车上放一弯木犁。慢慢从这条泥泞的路上往回返。
他沉默着。一年一年地沉默着。
飘泊多年之后,他是回到这里来的第一个土著。他在塌陷的眼窝里,深藏着无法确定的怨恨和无法确定的恋情。折磨他的,不是狂风暴雨,不是蚊虫泥淖。那实在算不得什么。任何恶劣的环境都不能和那场毁灭性的劫难相比。真正折磨他的,只是无尽的回忆。当年波涛汹涌的大河,在大河中驾船捕鱼的冒险生涯,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乡亲,日夜在他脑海中出现。可这一切都像梦一样消失了。黄河走了,把一切都带走了,连同他的一条左臂。
但他在等待。等待一些熟悉的面孔重新出现。那是一种十分渺茫而执着的等待。他相信,还会有人像他一样在那场劫难中侥幸活下来,哪怕极少极少。活着就会回来。不死就得活下去!
老日升的杂货店,生意并不景气。虽然它是鱼王庄惟一的商业。两间土坯房。里间铺一张床,床上堆一卷破棉絮。当门亮处就是杂货店了。迎门垒一道二尺高的柜台。柜台上放一杆断了杆的盘子秤。柜台里头的砖上有一坛醋、半缸黑乎乎的盐,当门临墙的土坯货架上有火柴、烟卷和一些针头线脑。
所有这些东西都蒙着一层沙灰。
鱼王庄年轻力壮的都出外要饭了,寻常连个动静也没有,像个死村。不大有人买东西。他便整日在门口劈柴。
“嘭——!嘭——!嘭——!……”
这声音满村都能听到。
这声音已经响了几十年了。
日升是小名。喊了一辈子仍叫日升。日升老了,人们便喊他老日升。晚辈的尊一声日升爷。据说,他是在日头升起时生下的。但一生的运气并未蒸蒸日上。他苦了一辈子,连个女人也没娶上。日升从十八岁在河滩里当纤夫,干到六十岁。四十二年。一九四七年解放,河滩里修了一条沙石路。行人客商方便了许多,却从此断了日升的生计。无奈,回鱼王庄开了个杂货店。虽说生意不好,他也没大花销。开店后,主要靠劈柴赚钱。
他劈柴极有窍门。先把树疙瘩搬到空地上,背着手绕一圈,翻弄一下。看准哪里是旋,哪里是茬。然后操起家伙,如庖丁解牛,一层层一爿爿把柴片剥落下来。一圈人围着看。有蹲,有站。抽着烟。看他劈柴,是一种享受。鱼王庄没什么好看的,就看老日升劈柴。
老日升七十岁的时候,雄风尚存,能抡一把锋利的锛,扬起来,“哇”的一声,关键地方,只这一锛,就开了。再难解的树疙瘩,他都能解得开。他叫“解”,不叫“劈”。解和劈不一样。解需窍门,劈用蛮力。
现在,他抡不动锛了,改用一把短柄斧子和两根钢钎。八十多岁的人,抡不动锛了。坐在一个方凳上,慢慢劈。旋口处最硬,十斧八斧才能开一道缝:“嘭——嘭——!嘭——!……”旋口终于开了。往下,顺着木丝就好解了。“嘭”一斧,开一道缝,插进一根钢钎,取下斧子。“嘭!”又一斧,缝隙延伸,插进第二根钢钎,取下斧子“嘭!”再一斧,第一根钎松动掉落了,拾起插到前头。如此循环挪动。劈开一个树疙瘩要两天。而过去,他一天能解五个树疙瘩。他喘得厉害。
屋后的空地上,堆一座小山样的树疙瘩,好像永远也劈不完。垛上的树疙瘩,已经长出木耳。木耳干了,生一层黑锈。看了叫人发愁。但老日升极有耐性。现在,已经不大有人看他劈柴了。倒是有几只麻雀老落在周围,从劈开的木片中找虫子吃,也不害怕。老日升也不轰赶。发现一条虫子,还专意捏来丢给它们。麻雀便来抢。虫子吃完了,就歪头瞅着他。一蹦一蹦的。
老日升一天到晚坐在树疙瘩旁边,劈柴不止。外头什么事也不打听。也不和人说话。累了,便坐在凳子上喘口气,呼噜呼噜的。拎起一只断嘴茶壶抿一口,接着又劈。
“日升爷,买盐。”轻盈盈走来一个姑娘。
“日升,打醋!”踢里趿拉过来一条汉子。
“老日升!买盒洋火!”走来一个自己聋也以为别人都聋的老头子,弓着背在那里叫。
老日升比他还聋。他耳目不灵。理也不理,只专心劈柴:
“嘭——!”
“嘭——!”
“嘭——!”……
长了,便不再有人喊。他的杂货店永远敞着门。买东西都是自己拿,自己付钱。老日升头也不扭。他仿佛已经入定。斧起斧落,铿然有声,像老和尚敲木鱼。
鱼王庄东头,有一横一竖两口草屋。横的是堂屋,两间。竖的是东屋,也是两间。堂屋里住着女主人。东屋里住着男主人。夫妻俩不住一屋,更不睡在一起。
女主人是个疯子。男主人是老扁。
女主人起了床,披头散发。正要梳头,忽然想撒尿。便探出头,往东屋看一眼,没人注意。伸手从门旁拎进一只土陶尿罐,飞身进屋,又反身把门闩死。这才往下褪裤子。把个白白的屁股按在土陶尿罐上,立刻哗哗大响。一边尿,一边从门缝里往外瞅。忽然院子里一声响动,她立刻停止尿尿,猛然提上裤子站起。再听,动静没了。褪下裤子又尿,哗哗大响。她警觉得很。尿尿停停,停停尿尿。三四次才尿完。她长舒一口气,提上裤子,又伸手往裆里掏了几把,放在鼻子上嗅嗅。满屋臊气刺鼻。她把裤带拴得很紧。长长一根布带,扎一圈又一圈,打上死结。这才开门,把土陶尿罐提出去,满满当当一家伙,放在门口,也不泼了。接着回屋梳头,对一面镜子,边梳边唱,咿咿呀呀的极快活。女人不丑。瓜子脸,大眼睛。腰身也苗条。浑身透着秀气。只是眼神游移,不时左瞅右瞅,防止有人扑上来。
东屋烟雾腾腾,熏得人睁不开眼。老扁打灭灶火,饭已做好。他先盛了一碗,上头放一双筷,弯腰出门。走到堂屋门口,喊一声:“柳!吃饭喽。”女人叫柳。却并不进屋,只立在门口。好一阵,女人才说:“我正梳头呢!”老扁便端个碗,站在门口立等。女人慢慢梳好头,又洗了脸,这才站起,走到门口,很凶的样子,冲老扁叫:“你往后退三步!”老扁端着碗退了三步,闪开门。柳哧溜钻出屋,站到远远的地方,命令:“放屋去吧!”老扁乖乖地进了屋,把碗放在一张方桌上。走出屋。女人看老扁出了门,才蹑手蹑脚回到屋里。刚坐下要吃饭,忽见老扁又转回来,腾地站起,惊慌的样子:“你要干啥!我不给你睡!”一边紧紧护住胸脯,“我不给你睡!”
老扁一边走来,一边说:“我没说和你睡。我给你倒尿。”
“你说瞎话!我不给你睡!”
“我没说和你睡。我给你倒尿。”
老扁端上那只土陶尿罐,走了。那女人才又坐下吃饭。
老扁为她倒了尿,又把尿罐放回原处。回东屋洗手吃饭。吃完饭,把锅碗洗涮干净。这才拍拍身上,坐在灶前吸了一根烟。吸得很深很慢,徐徐吐出一口浓烟。
老扁迈着仙鹤样的长腿,慢慢离开家,往老日升那里走去。他是这里的常客。
他爱默默地看老日升劈柴。蹲在旁边,吸一根烟。他不吸烟袋。从二十岁开始吸洋烟。还是当维持会长时学的。从此再没丢下。买不起烟卷,就把老烟叶搓碎了,用纸卷,卷得和洋烟一样。突然飞来一爿柴。他捡起扔回堆上。仍然老样子蹲着,眯眯地看。
这时候,他的诙谐、豁达全没有了。老日升每一斧子都像劈他心上。但他还是要看。看着看着,他会大汗淋漓,脸色苍白,像犯心绞痛。
老日升也不理他,只管一下一下地劈柴。
“嘭——!嘭——!嘭——!……”不紧不慢。
这声音满村都能听到。
这声音已经响了几十年了。
老扁终于离开老日升,转到别处去了。抱着心口窝。
鱼王庄没有一点活气。
他算了算,立冬已过,出外讨饭的人,该陆续回来了。这是规矩。鱼王庄人不论讨饭到了哪里,每年冬春都要回来栽树。有的跑到大西北,有的跑到关外,在当地干了临时工。立冬一过,也必定回来。嫁出去的闺女,也不叫自回。闷着头栽几棵树,然后该去哪去哪。想去哪去哪。
栽树!栽树!栽树!栽树!栽树!栽树!栽树!……
栽树已经成为惯性的机械运动。栽树就是一切。
鱼王庄人对栽树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齐心。栽树这两个字已潜入他们的血脉,每一颗细胞都是由栽树两个字组成的。尽管不少人对栽树已经失去信心,但一到栽树季节,还是像候鸟一样回来了。
一年冬天,一个因要饭远嫁黑龙江的姑娘,立冬刚过,就跟丈夫要了钱往家赶。三千里火车。二百里汽车,汽车到县城已是后晌。她急急忙忙往家赶。时逢大雪纷飞,道路难辨。一路不知跌了多少跤。上百里路赶到鱼王庄,天已黎明。她在冰天雪野跑了一夜,实在走不动了,爬着进了村。身后拖着一道长长的雪沟,一个早起的老汉,突然在雪窝里发现了她。姑娘已冻得半僵。老汉弯腰抱起,急急地问:“妮!恁远的路,你咋回来啦……那小子不要你啦?”姑娘摇摇头:“我……回来……栽树。”
老汉哭了。消息传开,全鱼王庄的人都哭了。
栽树,是鱼王庄一辈辈的传统,一辈辈的事业。
鱼王庄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树木成林,等待风沙的消失。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代一代人编织着同一个梦。一个多世纪以来,鱼王庄人一直在梦幻中生活,在梦幻中繁衍生息。树木栽上被毁掉,毁掉又栽上。不知多少次了。时间在过程中悄然流逝,一辈辈的人在过程中悄然倒下。奇迹一直没有出现。而风沙却像永远的梦魇伴着他们的日子。
老扁在一棵三人合抱的苦楝树旁边,站住了。他轻轻地摇摇头。真快。多少年过去,他仍记得儿时的歌。
风沙不把人情留,
打罢麦穗打谷头,
哥嫂逃荒郓城去,
爹娘吊死在梁头……
三岁那年,爹娘就吊死在这棵苦楝树上。他还依稀记得,四条赤裸的干瘦的脚杆,双双在空中晃荡。哥嫂郓城一去不归。
那时,鱼王庄人多爱去郓城逃荒,却不知什么道理。是郓城盛产五谷,还是因为郓城出过一个“及时雨”宋江,郓城人也便从此乐善好施?老扁说不清。
他没有去要过饭。日本人在时,大伙公推他当维持会长;国民党在时,他当村长;解放后,他当村支书。他没有机会出去。可他真想出去。在外头,一人混一张嘴,再怎么难也混得住。在家呆着,却像个住持僧,什么事都得管。年轻力壮的走了。剩下的妇孺残疾,他必须养活。他不忍心丢下他们。
鱼王庄的地不少。如果按人平均,居全县之首。但河滩上只长茅草,不长庄稼。茅草根都扎在三尺以下,庄稼行吗?每年只能种一季高粱。庄子穷,没有本钱,地里稀稀拉拉。秋天一场连一场雨,高粱都泡在水里。成群的麻雀飞来,遍地哄抢。他和几个老人每人提一杆火枪,蹬着水,这里放一枪:“轰——!”那里放一枪:“轰——!”到处轰赶。最后多少收一点。他把仅有的这点粮分给每家的老人孩子。再厚着脸皮要点救济。日子就这么过。
哪个老人病了,他要去端屎端尿,煎汤熬药。多亏梅子做他的帮手。否则连口气也喘不过来。
他感谢梅子。一直对她怀着深深的歉疚。
她已经等他多少年了。
梅山洞出洋归来,在城里娶了个女人。后来生下梅子,几年后就病死了。父女俩相依为命。梅山洞没有再娶。小时候。梅子常跟着父亲外出,老扁赶上马车,四乡行医。没事时,老扁就领着梅子玩耍,在大街小巷里串。他比梅子大十几岁。梅山洞让梅子喊他哥哥。他似乎成了这个小家庭的一员。但梅山洞不知道,老扁已在暗中走上了另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