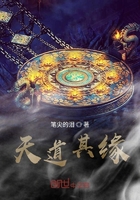我不知该做什么,泪水很自然地淌落,冰冰一身的油彩浸落在我的身上,混合着汗水和泪水,肆无忌惮地在我身上流淌。透过车窗看着飘满绿色的广州,我们像是一对连理的虬枝,彼此缠绕,已不能再分开。小雨滴落在车窗,淌下时像是泪道,为我们营造了一种未经设计的感动。
1996年,我从北方逃离,踏上前往南方的道路,目的地是广州,全国美容美发大赛的现场。
我再一次坐上绿皮火车,只是当时已不同过往,心情和人早就换了个模样。相同的是,我又踏上一段漫长的路程,绿皮火车车厢里依然设备简陋,环境污浊。这是一次从中国西北跨越东南的横穿,逃离束缚奔向自由的快乐心情跟着车轮一起奔跑,我看向窗外,发现竟连景色都变得更生动,更美丽。
旅途中的奇妙,在于它的随机,我无可预知将要发生什么,所以冒险才显得更加刺激。我原本为获得自我肯定和荣誉而来到广州,却遭遇了一份意料之外的初恋。
在一个身体还略带僵硬的早晨,在我仍困倦着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火车抵达广州。双脚踏上陌生城市的瞬间,那种出发时的兴奋与期待突然被迷茫代替,我只剩混沌,毫无方向感。好在我仍年轻,所以无惧,心中总是充满对未知的好奇和对实现自我的向往。至少在这里,我获得了自由。少许的迷茫,应该会在与陌生城市结缘的过程中慢慢消失。
广州和我曾居住的边陲小城景致完全不同,这里的街道热闹非凡,放眼望去街边全是生意兴隆的门店,街道上色彩斑斓。那些在西北地区很难见到的郁郁葱葱的绿色,也把城市点缀得更加生动,沁人心脾。这里的树不像西北地区的那样单一,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叶子还能有如此多的形状,而绿色也能透出不一样的深浅和感觉,每一种都各有气质,随着微风飘荡在这个暖湿的城市里。
经过广州荔湾区的荔湾湖公园,我看到一汪静谧的湖水,湖面如镜,两岸百年的荔枝古树倒映在湖面上,仿佛水下还有另一个世界。在百年古树下,年轻的我渺小又不值一提,但它们对我这个外来者的友善和包容,却透过沧桑的树皮,渗入我的心底,让我不再紧张,而是学会去享受这里的一切。
我喜欢这座南方都市中自由的味道,也许它来源于我的内心,而非这座城市本身。此时此刻,因为我的叛逆,家中老人已和我断绝了关系,也许这就是想要获得自由而必须承受的代价。
在四位老人看来,我应该尽职尽责做一个安分的孩子,每天按时上班下班,按时回家吃饭,在他们认为能够安心度日的工厂里就这么度过一生。可我,却无法接受他们为我设定的人生曲线,在背起行囊迈出家门之前,我的心,其实就已经远去。
背负因为叛逆而离家的压力,四位老人愤怒的目光几乎灼伤我的后背,但我也同样无法妥协。我承认自己给他们造成过伤害,从离开的那天起,我就无法停止告诫自己必须努力,用行动证明自己选择的路是正确的,希望终有一天换得他们的谅解,也解开我的心结。
在这次全国大赛中,结果无非只有得奖或不得奖两种。面对这样一半一半的可能,我也会恐惧,但决不能会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倒下去。
年轻的我纠缠于“不被认可”和“自我认可”的疑问中,等待着一个答案。这条冒险的路上,开始起步就困难重重,磕磕绊绊。那时我会想,也许年轻就意味着要因为不断尝试而备受磨难,然后在摸索中成长。还是要有信仰,这样才能认准方向,而这个信仰越坚定,前面的路才会越明朗。
任何人的成长都要靠经历来维持,我又怎么可能是个特例呢?寻找的路,正是经历的路,实现梦想原本就是积累的终点。一路上,我无怨无悔。
我报名参加了两个比赛项目,一是“晚宴发型”,二是“梦幻彩妆”。晚宴发型的项目里,模特身着华服,造型师当场为她们设计发型;梦幻彩妆的项目更为复杂,需要以模特全身作为造型载体进行创作,从脸部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节都会涉及。模特们将会穿上肉色的文胸和底裤,让造型师用油彩以身体为画布,在上面进行创作。
组委会安排给我一个名叫冰冰的模特。冰冰是广州人,是当时广州小姐选美比赛的获奖选手。初次见她,我有点害羞,面对这种大胆的比赛形式,当时我这个来自边陲小城的毛头小子还无法完全适应。我脑子里不敢有半点混乱,只能专心于创作。冰冰露出那如剥开的荔枝般光润水嫩的肌肤,让我硬是舍不得用油彩遮挡住她浑然天成的美丽。
大赛组委会规定赛前要完成身上油彩创作的部分,比赛时只制作脸部妆容。所以比赛当天,大家都起得很早,开始做准备。
清晨五点,冰冰来到酒店,两个鼻孔塞着纸巾,说话鼻音十足,和她姣好的面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看出冰冰病得不轻,就算提出休息的要求也完全不过分。
我心里惦记着冰冰的病情,希望能尽早完成创作,让她也多些时间休息。于是我开始专注地将油彩按照自己在脑中涂改过多遍的创意,一点一点在她身上铺陈开。油彩在冰冰的肌肤上落下,洇开,停顿,然后转变方向……我沉浸在创作的快感中,偶尔会留意笔下这位“病美人”。
为保证油彩的完整,绘画的整个过程中冰冰都必须站立着,包括完成以后也不能松懈,要一直等到比赛结束。回想起自己在来广州的火车上站得小腿肚子淤青,我就能完全理解冰冰的痛苦。在比赛的过程中,冰冰站在台上,腿好像受伤那样微微颤抖,外加她当时又有病在身,难免让我产生心疼的感觉。
我对冰冰特别照顾,陪她聊天,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她喝水,这种源于合作的亲密关系,让刚开始的那种疏离感渐渐散去。这似乎不是简单的友谊,而是并肩作战似的心灵沟通,虽然有些胆怯,但我还是能感到我与她之间因为彼此理解而获得的那份默契。
真正在赛场上的时间并不长,脸部妆容需要在半小时内完成,我仅仅用了20分钟就结束创作。一来,我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项目;二来,我实在不忍继续看到冰冰忍受痛苦的表情。热闹的台后人来人往,大家有说有笑,只有冰冰脸色苍白,伴随着一阵阵的咳嗽声。工作人员看到冰冰的样子也于心不忍,索性叫冰冰在结果出来之前回家休息。工作人员一边说,一边用手拍拍冰冰,但冰冰僵硬的身体好像一片薄纸似的,突然滑倒在地。我越过众人冲向冰冰,一把抱起她,边往外跑边喊人叫车,整个楼梯走道里充斥着人们的喊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
去医院的路上,我不知该做什么,泪水很自然地淌落,冰冰一身的油彩浸落在我的身上,混合着汗水和泪水,肆无忌惮地在我身上流淌。透过车窗看着飘满绿色的广州,我们像是一对连理的虬枝,彼此缠绕,已不能再分开。小雨滴落在车窗,淌下时像是泪道,为我们营造了一种未经设计的感动。
在医生为冰冰挂上吊瓶以后,我小心地替她擦去身上的油彩。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一些颜料凝固在皮肤上,难以擦去。我耐心地为她慢慢清理,逐渐还原她皮肤本来的颜色。
吊瓶里的液体逐渐输入冰冰体内,她开始慢慢恢复精神,气色也好了许多。在送她回酒店的路上,我买了最能诠释我俩缘分的荔枝。回到酒店以后,冰冰躺在浴缸里泡着热水澡,我就蹲在她的身边,把剥开的荔枝一颗一颗送到她嘴边。水雾弥漫中,我能看清冰冰疲倦的脸,正在冲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