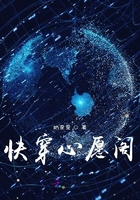张小年和张和坐在他们公司的休息间,张小年喝着咖啡,张和虽然表情轻松,但总感觉有一丝游离。
张小年:想不到吧?我也觉得不可能,我甚至没有打李茂,我连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梦都不知道。关键是这梦的感觉太他妈真实了。我有的时候甚至不知道现在是现实还是梦里。
张和:也有可能是梦,你可能也没有见我,而现实里的我已经死了。
张小年听到脸色一变,嗔怒地看了张和一眼。
张和:开玩笑嘛,这么严肃干什么。
张小年不想深说这个事情,转而说道:总之我就觉得很奇怪,赵大哥现在都已经出院开始工作了,而在梦里我感觉那事故像是刚发生的一样。
说完张小年又揉搓了一下手指。
张和:梦是会模糊掉时间概念的,而且在现实中你不会相信,不过去做的事情,在梦中你又觉得理所当然,梦也会模糊掉是非观念。
张和注意到了张小年的动作:你手怎么了?
张小年:噢,好像是手指上扎了一根刺,1个月了,好像特别小,看也看不见。
说完把手递到张和面前。
张和看了眼张小年的手指:一般这么长时间应该早就好了,你等下去我们实验室,给你做个检查。
张小年:这点小事不用这么麻烦吧。
张和不解释也不言明:你就是太容易忽略危险和隐患了。走吧。
张和走近张小年,拍了拍他的肩膀,而后向前走了。凑近张小年才发现张和因睡眠不足而显露出的憔悴面容。看样子他还是没有走出来啊。
何也是一家科技公司,主营业务是微型芯片,现在正在研究可植入人体的芯片,所以也有一些生物科技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在地下二层。张和与张小年一同走进一间实验室,实验室的人看到张和进来都点头向他示意。
张和:小林,麻烦你帮我弟弟做一下检测,看一下他手指里有什么东西。
说着指了指张小年的左手。接着有一个年轻人走过来。
小林:好的,您就是我们老板的弟弟吧,请跟我来。
小林将张小年引到一个仪器面前。
小林:请把手放在这个上面,有问题的是左手手指是吧?
张小年点点头,而后面向张和。
张小年:你们不是搞芯片的吗?怎么感觉像是搞医学的一样?
张和:这是我们芯片植入的实验室。
探测器滴地响了一声,小林看向显示面板。
小林:老板,小年哥,手指里的确有一部分非人体组织,直径只有十微米,正常光线下肉眼不可见。
小林的脸上透出了一丝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一样的兴奋的神情。
张小年:可能就是一个小刺吧,看都看了,能帮我取出来吗?
小林:当然可以取出来,不过这个应该不是刺。
说完小林看向了张和,张和的视线现在却不知道飘向了哪里。
张小年:怎么,难不成是你们研究的芯片?
张和:取出来看看再说。
而后张和便要向外走,张小年本想叫住他,不过总感觉张和的情绪在听到这个不是刺之后就不太对,好像是在生气?而后张小年转向小林。
张小年:怎么感觉你有一点开心呢?
小林:噢小年哥,也没有了。
张小年:你叫我小年就行了,诶对了,来给我说说你觉得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小林看了一眼电脑中的各项数据,又转向张小年。
小林:我们检测到这东西在向外传输数据,但是数据好像加密了。
张小年略显惊讶。
张小年:你是说,这个是…
小林:微型芯片,我们公司一直在研发的内容,不过如果这个真的是芯片的话,它的技术可领先我们太多了。如果以它为样本进行研究的话,一定可以大大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张小年听到这里之后就陷入了思考,只看到小林的嘴巴一张一合的,但根本没有听他后面的话。如果这如小林所说真的是微型芯片的话,还有这么高的技术,那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植入自己的体内?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员工了,身上还有什么值得别人注意的地方吗?
小林在一旁还在独自感慨:这要是在以往,老板一定比谁都兴奋,可是今天,根本就没有看到兴奋的影子...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是逃避更好一点。小年哥,还请你多劝劝老板呀。小年哥?
张小年还在想事情,被小林这一叫,回过神来:哦,好的,必须的。
从和也出来,张小年还去了一趟动物收容所,他还是放心不下交个易竟单独接田野和跳跳。他大步进入了收容所,后面跟着一同过来的易竟。偏暗的收容所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光,值班的一位身材高大的管理员,他抬头看了一下,易竟连忙走上前去。
易竟:这位大哥你好,我们接到荣所长的通知,来领自家狗狗回去的。
管理员:姓名,电话,号码牌。
易竟递过去一个名片和一个牌子,管理员在他的一个小本本上核对后,将易竟和张小年引了进去。他们走过长长的通道,通道的两旁是一排一排的笼子,每个笼子里有一到两只狗。张小年原本以为会比较吵,没有想到出奇得安静,这些狗看上去没有欢快感,或恐惧感与紧张感,各个懒洋洋的。
张小年:这些狗狗怎么看上去没什么精神?
管理员:太舒服了,所以没有精神。
明显骗人的鬼话,这话中还带着戏谑,让人不爽。
易竟给了张小年一个眼色,示意不要问了。而后他们在一个笼子前停下了。里面的跳跳和田野看到了主人,都跑过来摇着尾巴。
张小年:田野,跳跳,走,回家了。
易竟在前面开车,张小年在后座抱着田野与跳跳,一遍遍摸着它们的头。
易竟:可能要缓一个星期才能活泼起来,收容所为了好管理,给狗狗们喂了催眠一类的药物。
张小年没有接易竟的话:田野呀田野,你叫田野,可是却不能去田野。跳跳呀跳跳,你叫跳跳,可是现在都没有力气去跳了,呵呵。
易竟:小年.....
张小年把头望向车窗外,飞驰而过的路灯一下一下地打着他的眼睛。他自出生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他没有经历过怎样的变革,他不知道之前的世界是怎样的,电影中看以前的世界,总是不缺乏快乐的人。但他知道自己不快乐,人心淡漠,金钱至上,至于致力于尽可能维持公平而制定的各种规则法律,也被许多人钻了空子用于谋私。熟悉规则的公平窃贼,比鲁莽的规则破坏者可怕多了。可张小年没有见过快乐的人,即使是那些得利者。要不然这个城市的自杀率不会这么高,心理诊所不会开得到处都是。一批又一批的人们离开家乡的田野,一股脑地涌入这一个个钢铁森林,而后从高架上,从桥上跳下去,在浴缸里在卧室里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行为让他想到了旅鼠,走那么远的路,就是为了最后跳下去吗?他想不明白,一切人们想不明白的事情,就归结于宿命,仿佛只要带上宿命,一切不合理就变得合理,做一切奇怪的事情也就心安理得了。
他们的车仍然穿梭在这个不用睡觉的城市里,街道两旁的高楼林立,写字楼的灯、霓虹灯、广告牌都发着光闪烁着,车流人流一切都在规律地运转着,这个城市看上去井然有序。
张小年:这个城市病了。
易竟从后视镜中看向张小年,张小年像是在自言自语一样。
张小年:这个城市没有快乐的人,这里到处是心理诊所,但是可能连心理医生都有病,这里也没有快乐的狗狗。这里的灯在晚上也亮得晃眼,但是这光照不到谁的心里去。科技发达了,我们能轻易地联系到任何人,可我们没有想要去联系的人了。这里除了高楼之外没有好的风景了,这里除了纪录片里看不到各种各样的动物了,这里只剩人们自己了。
易竟:你怎么了?可别吓我啊,田野被扣起来是我不对,你不是打算再讹我精神损失费吧?你哥那么有钱,你有啥事儿可找他要啊。
张小年:我哥?他也不好,也不知道该说是科技害了他还是他对科技的热爱与信任害了他。
易竟:哎,要不我还是给你找个心理医生吧,我看你手机里推送的这个万医生就蛮好。
易竟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从副驾驶座上拿起张小年的手机,手机正好给他推送了心理咨询的广告,医生名叫万均。
张小年:把我手机拿来。
易竟:这可是你自己放在前座的啊,你不会真的抑郁了吧?要不它怎么给你推这个?
张小年:屁,这只能说明在大数据的天下,还是有算法算不对的事情。
汪,田野也配合着叫了一声。
易竟:呦,田田,你在帮谁?平时白给你喂那么多好吃的了。
张小年:给你说了别喂它其他的东西,只为狗粮,到时候吃坏肚子了。
伴着这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车子向城市深处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