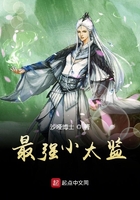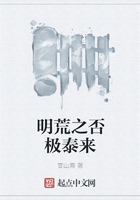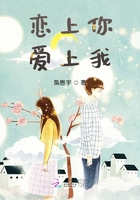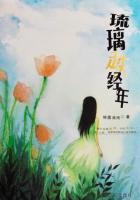大汉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夏!
数月以来,豫州仅仅下了两场小雨,对干渴已久的中原大地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旱灾已成定局,庄家大部分枯死。眼见夏收已经变成奢望,秋收也可能只是幻想。
无数百姓站在田间地头欲哭无泪,命运的魔爪已经悄然的伸向了他们。
可当权者仍然醉生梦死,地方豪强不顾百姓死活仍旧横征暴敛,那些所谓的名士依然时常聚会,指着枯死的田地吟诗作赋,表达一下悲痛之情,然后喝的酩酊大醉,等待着下一次的表演。
十几年来不死不活的太平道仿佛一夜之间兴盛起来。作为首领的张角开始自称‘大贤良师’,命令徒子徒孙游走四方,传播教义,施以小恩,蛊惑民心。
…………
与豫州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宁城县。
用一些老农的话来讲就是该下雨的时候下雨,该放晴的时候便是艳阳高照。在他们的记忆中,宁县从未有过如此风调雨顺的年景。
人们都说这是托了曾大人的福。仙门弟子来宁城做县令,老天爷都得给面子。
传言这种东西一但传播开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在家躺尸的曾麒莫名其妙的被捧上了神坛,他在宁城百姓心中的威望被无限拔高。
人们祈祷曾大人永远不要离开宁县。
叨念曾麒的不仅有宁县百姓,远在荆州南阳郡,一个魁梧的中年汉子匆匆的推开了家门。
“夫人,可准备妥当?”
“嗯!值钱之物皆已变卖。只是那曾幼麟真能妙手回春,救我叙儿性命?”
“曾幼麟乃仙门弟子,商队之人言之,其曾让一位发热垂死之人一夜之间变得生龙活虎。此事有百余人得见,岂能有假?况且……”
男子没有说完,但意思妻子却心知肚明。曾幼麟是他们夫妇唯一的希望了。
这时,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扶着一个病怏怏的男孩走了出来。
男孩仅仅十来岁,却身形消瘦,面色蜡黄。每走几步便会气喘吁吁,咳声不断。好似古稀老人一般,即将油尽灯枯。
“走吧!我已向太守大人辞去都尉一职,我等尽快起程。”说着抱起男孩,快步走向停在门口的马车。
“汉生,汉生!张机来也!”
哒哒的马蹄声自街口传来,一个身穿道袍,负背药箱的中年男子疾驰而来。
“仲景兄?昨日已然辞行,兄不必再送。还是早早起程赴任,以免延误时日,遭张叔父责怪。”
“哈哈!汉生素知张机为人。自小笃信道学,志在悬壶济世。至于官场,只叹今生无缘矣!”
“张叔父那里如何交代?”
“我已留书一封,言明志不在官场。自此云游天下,寻医访道。顺便护送汉生去往北地宁城。我虽治不好侄儿,但一路护持、稳定病情,总还能起到一点作用。”
“这……如此多谢仲景兄之恩情。”
“哪里的话!顺道罢了!起程吧!”
一行人出了南阳,直奔北方而去。
无独有偶!
陈留郡与东郡的交界处,一个壮汉推着车正在官道上狂奔。车上坐着一老一少两位妇人。
“儿啊!此地已是东郡地界,休息片刻吧!”老妇人开口言道。
“好!”壮汉缓缓减速,不过却未停下了。
“呜呜!”老妇人突然呜咽起来。
“阿娘,是儿不孝,害的阿娘背井离乡。”
“呜呜!为娘所哭者,非因背井离乡,乃因老妇人无用拖累我儿矣!”
“阿娘不需如此,东郡距此已然不远。孩儿有一好友,在东郡太守麾下任屯长,此去投奔他,定无忧矣!”
“我儿一身本领,何故寄人篱下?”
“阿娘说的有理。凭儿一身本领,也定能让阿娘与夫人生活无忧。”
“阿娘,前方路口有一酒肆,咱们歇歇脚如何?”
“我儿做主就是!”
酒肆不大,却占据两郡要道,过往的行脚商人络绎不绝。此时已经极近客满。
三人在角落里最后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要了一些吃食和清水。边吃边听周围的食客们议论。
“李兄,你行商南北,最近可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豫州大旱算不算?”
“这算什么?豫州大旱人尽皆知。况且兖州南部不也同样遭受波及了吗?”
“呵呵!要说大事还真有。听说数月前草原胡人之间发生了战事,鲜卑人吃了大亏,赔给了乌桓人十数万头牛羊和马匹。”
“好!真是一报还一报,大快人心。”
“好什么好?鲜卑人损失惨重,估计今年还得犯边。”
“真的?”
“这还有假?宁县县令曾幼麟,你知道吧!”
“当然!仙门弟子,曾经一人一骑纵横草原,这天下谁人不知?”
“一个月前曾大人发布召令,请天下游侠齐聚宁城,共同抵御胡人,守卫国门。”
“游侠?他们除了为祸乡里,还能有什么用?”
“呵呵!此侠非彼侠。”
“何解?”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好!此诗可是曾大人所作?”
“不错!诗名《侠客行》。曾大人所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唉!恨周某手无缚鸡之力,恨不能与天下侠士共襄盛举。恨、恨、恨!”
“呵呵!周兄不必如此!为国杀敌,我等无能为力。不过有一件事我想周兄定然感兴趣。”
“哦?何事?”
“最近曾大人在宁城县衙旁起了一座藏书楼。楼中有藏书万卷,可供学子免费阅读、誊抄。若家中有竹简孤本,也可到藏书楼换取心仪之书籍。”
“呵呵!李兄欺我矣!一座书楼何以藏万卷经书。”
“知道你不信,请看!”
李姓商人从怀中小心翼翼的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后一本崭新的书籍出现在两人眼前。正面印有《论语》两个大字。
“这、这……”周姓男子同样小心翼翼的掀开书籍,一股墨香扑面而来。
“这竟是论语全册?”
“嘿嘿!这是李某用家中藏书,托甄氏商队换回来的。”
“咳咳!李兄慢饮,周某尚有要是,先行一步了。”
周姓男子匆匆离去,角落里的一家三口也收回了目光。
“阿娘!儿想去宁县!”